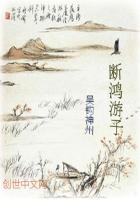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所以珍惜才是最大的真理。
想起来,那段日子应该是阿K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了。
梦想破碎,失业,居无定所,女友提出分手,被在一起十年的朋友骗走所剩无几的存款,你可以想象到的种种遭遇,他一个不差。
阿K觉得一定是老天在玩他,没有第二种可能。
2009年的夏天,阿K大学毕业一年,刚满24岁。
6月初的杭州潮湿蒸郁,正赶上梅雨季节,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阿K习惯性地睡到晌午,外面天还是阴沉沉的,好像人的脸色。他起来坐在床脚,把打火机点着,迟疑片刻后,眯着眼用力吸了一口烟,很快烟就着了。
阿K清楚地记得,点着打火机的一瞬间,微弱的火光就在眼前晃啊晃,但他好像什么都看不见。
他笑了笑,掐掉烟头后穿上背心和短裤,趿拉着拖鞋下楼去了。
老海请阿K下馆子,一大早就在楼下等着了:“你可算出来了,打你十几个电话都不接,急死个人。”
“你怎么一副比我妈还婆婆妈妈的样子!”
“少啰唆了,就在体育场路宝善桥过去一点儿,走两步就到了。”
老海走在前面,撑一把黑色的伞,伞不大,但是可以把他肥大的身子罩住。没走两步他就顿住了,然后往回走:“你说你出来也不拿把伞,让我说你什么好。”
老海把伞移向阿K,雨打湿了老海的左半边身体。
“饿了吧,八宝象肚好吃得很,猪肚里灌了鸡肉,咱哥俩再来几瓶白的,今儿我请客,吃个痛快!”
阿K没有接他的话。
阿K又点着一根烟,用力吸一口火光就起来了,在雨天里吞云吐雾的,他感觉自己就要飞起来成仙人了。老海像个孩子一样用手乱扑腾,把烟都打散,还一边嘟囔着:“抽烟对你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啊。”
阿K是一个重度烟瘾患者,在女朋友的控制下还每天两盒都不够。嗯,他承认自己压力大——24岁,未婚,住在租了三年的公寓里,离租房合约到期还有五个月,在一家知名的外企工作,老板是一个苛刻的老外,每天都要他把领带打正,西装熨得平整舒展。
阿K每个月倒是有一万元的收入,这在外人看来很富裕,不过大部分钱都寄给家里了。五千块汇到妈妈的卡上,两千块交房租,余下的三千块是生活费,养着拜金女朋友,还有一条狗。
女朋友名叫百合,是阿K的大学同学,现在是个模特。每逢车展或者服装秀,她就花枝招展地出去。很多时候阿K加班后回到家,还要照顾喝得烂醉的她。
当阿K看到她脖子上有吻痕的时候,恨不得一巴掌把她打醒。
然后就是舍不得、怜惜,帮她换洗衣服,打热水,用湿毛巾给她敷额头。
再然后就是一个人坐阳台上抽烟,一根一根的,留下百合在屋里哇哇地吐。
他嫌弃百合,百合嫌弃他。百合说阿K每天只知道工作,衣服除了西装还是西装,连一身这个年纪该穿的像样的运动服都没有。很多次百合带阿K出去参加她朋友的局,他除了能帮她喝酒,干不了其他的。有一次阿K在饭店厕所里吐的时候听见里面的哥们儿说:“百合眼瞎了啊,跟这么个男的,要钱没钱,要长相没长相。”
“百合也不是什么好姑娘,你以为她干净啊!”
“哈哈哈。”
阿K醉得连爬起来冲过去给他们两拳的力气都没有。
百合跟阿K去逛街,她试的那些衣服都太贵,阿K不喜欢,就直接把衣服从百合身上扒下来还给售货员。百合气得直掉眼泪,说再这样下去整个杭州的商场都不能去了,脸丢得到处都是。
他们价值观不同,阿K无法接受在他的世界里一件衣服几千块钱,而百合说她是模特,有些场合需要穿。阿K又开始发疯,说:“那些场合不是不需要穿衣服吗?”
后来他们分手了,阿K很后悔,给她留了这么个显而易见的把柄。
阿K出生在农村,他是看着全家人眼泪汪汪地靠着杀一头猪过年或者结婚长大的。百合说他不会心疼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寄回老家养猪了。
百合还说他连自己的女朋友都养不活。
可是阿K觉得日子挺好的,他有个小梦想,希望做到公司市场部的主管,然后推广自己的新产品,拿个年度销售奖。阿K的那条狗不金贵,他吃的它都能吃,从来没生过病,就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阿K有一间不大的房,每天早晨都起来给他爱的人煮牛奶,然后把前一天买的面包加热好。当阿K急匆匆穿好衣服出门时,百合还跟孩子一样在床上赖着。
他就觉得真好。
阿K爱吃路边的早点,比面包好,不光因为便宜,还因为他觉得面包没有人情味。
同事都开玩笑说他是男佣,阿K回应他们,没关系,两个人在一起,开心最重要。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式了。
2009年夏天,全城都被笼罩在燥热中,霓虹灯,日出,匆匆的行人和拥挤的人行道,还有耸入云霄的写字楼。《快乐女声》在电视里、地铁上、商场的大屏幕上播着。曾轶可唱歌时总像是很冷,让人听起来有些心疼。街上有刘惜君的粉丝团,发着大大小小的宣传单,希望大家支持她们的偶像。她们穿着统一的衣服,脸上还化着浓妆。
如果是以前,阿K一定会匆匆穿过人群,面无表情地对这些人说抱歉,然后拒绝掉传单,拎着西服走进耸入云霄的写字楼。不过那天阿K恰巧因为一个方案与老板吵得不可开交,转天老板就开了他。
“他认为我是个自以为是的蠢货。”
房子也快到期了,阿K为了躲房东不得不到处借宿,去大狗家住一晚,再去小强家借住一宿。
不过最坏的事情是他被在一起十年的朋友骗走了所剩无几的存款,阿K恨他恨到不想再提他的名字。
几个星期前百合又约阿K了,他接到电话时兴奋得说不出话,像个没出息的孩子一样。百合说她很难过,想让他陪她走走。见面后他才知道百合被一个开连锁酒店的老板踢了,像皮球一样,滚得很远很远。
那天晚上他们喝了很多酒,百合依然骂阿K是废物,养不活自己的女朋友,反而要逼女朋友出去赚外快。阿K笑嘻嘻地说:“你也是傻,牛的话你赚个男人回来,到头来还不是被人家当皮球踢。”
然后他们都哭着笑了起来。
百合和阿K曾经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她是校花,他是全校成绩最好的男生,本科毕业就接到四家上市公司的工作邀请,大家都叫他们“人生赢家”。
那时候他们每天一起泡图书馆,她看美容杂志,他算线性代数,傍晚天边有云的时候就在校园里走一走,晚霞落下来像轻薄的衣服。他们常去学校里最有名的一条小吃街,下雨了阿K就脱下衣服披在百合身上,等跑到宿舍,百合帮他擦身子,然后把淋湿的衣服洗干净。
阿K的那几个混混儿室友见了百合就调戏,两眼放光。每每这时候阿K都会一边打一边骂地把他们赶走,然后锁上门和百合亲热一会儿。
百合洗干净的衣服总有百合香气。
百合问起阿K有没有当上主管,他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没有告诉百合自己被开除的事情,而是借着醉醺醺的那股劲儿,说当初发誓是到年底前实现的,这还有好几个月呢。然后百合又大笑起来,她笑起来没有遮拦,美得真像百合。
阿K问她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她说找个好人家嫁了,当家庭主妇。
两人都没再说话,只是喝酒。
阿K是靠百合搀着走出去的,他喝得太醉了。百合说阿K还是老样子,只要有她在就会喝多。
“嗯,可能是帮你挡酒挡习惯了吧。”
阿K已经没什么知觉了,整个人横着躺在百合的车后面,吐得满车都是。
百合送阿K回家,说这次轮到她帮他换洗衣服、打热水、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阿K开玩笑说:“你不怕我把你当皮球踢啊?”百合爽朗地笑起来,说自己倒是有点儿想回以前那个球门了。
路上阿K一直大声嚷嚷,唱他一喝酒就爱唱的歌。后来百合接了个电话,迷迷糊糊中有人堵住了阿K的嘴,然后就是一阵巨大的撞击声,他头晕得厉害。
是老板的电话,说介绍个活儿给百合,事成后给她五十万。百合骂着脏话,但是阿K唱歌声音太大,对方根本听不清。百合转过头伸手捂住阿K的嘴,然后对着电话连说了好几个“滚”。
百合恨死他们了,也恨死自己了。
一句“你不得好死,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之后再转过头,车子已经偏离方向好远了,一下子撞到一辆小轿车上。
火光漫天。
百合当场死了。
阿K被送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再醒来时,阿K就是这副模样了:身上插满粗粗细细的输液管,整个人被纱布包着,戴着氧气罩,只有眼睛可以动。身旁的仪器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嗯,他是植物人了,终生植物人。
被撞的人是老海,他的身体可以活动,但是大脑受伤严重,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他那天开车去接好几年没见的发小,不过现在他都不记得了。
老海就认为阿K是他发小,老海的家里人怎么劝他都不听。老海总来阿K的病房看他,给他带红烧肉,看着他只能输那些营养液却不能张嘴吃东西,老海就哭,急得直跺脚。
阿K还有一个完好无损的大脑。他知道百合和他出了车祸,知道如果没有这场车祸或许他们就可以重归于好,也知道他们对不起陌生的老海,他想道歉,但是开不了口。
老海每天傻兮兮地穿着病号服来阿K的房间拔他的输液管,被护士发现带走时急得眼泪哗哗地流,这些阿K都知道。他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弥补,也不知道还能这样痛苦地坚持多久。
阿K闭眼的时候,两股热热的液体顺着眼角不听使唤地淌下来。
老海没有带阿K去吃八宝象肚,阿K也没有再抽过烟,那些都是阿K的想象,想象老海一直觉得自己亏欠他,愧对他,对他好,还打伞来为他挡雨。
其实阿K还有很多想象,他想象百合在他醒来前做好早饭,她洗完的衣服整齐地挂在阳台上,风一吹就全部飘起来,那是有百合香气的。
他好像一闭眼就能闻见百合香味。
我就是老海的那个发小,他小学一年级就跟我在一起玩了,我们总是去彼此家玩,我记得每次他那个不会做饭的爸爸都会买一大桌子东西招待我。2009年那天,我从外地读书回来,老海高兴得不得了,说要给我接风,特地开了他爸刚买的车。
那天我在车站等了好久好久,好像有一辈子那么长。
老海从小就不顾一切地吃吃喝喝,胖得像一片海一样,所以我们都叫他老海。他说人要学会珍惜,别跟他爸妈似的,为了一点儿小事就吵架离婚,搞得跟仇人一样,没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所以珍惜才是最大的真理。那些你不珍惜的,老天自有另外的安排。
老海还说,人生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不然要是有一天被车撞死得多冤。
BGM_《水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