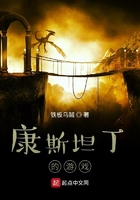PART 1 抢走名字
声音似缤纷的丝带一样交缠着。孩子们咯咯的傻笑像明亮的饰带,冰激凌车招摇的回旋曲如同昏暗中的烟火,当然还有其他的声音,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一场早已结束了的比赛。鸟儿歌唱着,嘤嘤地盘旋,伴随着凄厉的叫声落回地面,那声音就像机械摩擦发出金石声般刺耳。循环。停止。循环。
斯玛吉疲倦地睁开双眼,光线穿过她那条挂在窗前的扎染围裙射了进来,死苍蝇、塑料袋,还有躺在一边的伏特加酒瓶十分扎眼。早上吗?噢,不,已经到下午了,下午太阳才会从这个角度晒过来。又荒废了一天。
笔、火柴和卫生棉条在桌上散落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正慢慢地烧进桌面的塑料板里,板子被烫出伤疤般的皱褶。一把牙刷横躺在制冰的冰格旁边,冰格里盛满了凝固的玫红和紫色颜料,看上去像干涸的血。
她深陷在躺椅里,眼睛紧紧盯着画布,画布撑在已经坏掉的煤气炉上方的架子上。画面是这样的:一张报纸钉在椅座上。因为这幅画,昨夜,前夜,又或者从很久之前开始,她就没法入睡,脑袋里嗡嗡响着,搜肠刮肚,想找出赋予这个平面汹涌的颜色和造型的手法。她希望自己能再次抓住那种感觉,灵感到来时,就像巨浪,冲碎她意识的堤墙,将她拽进那灰色的大海中飘荡,浪潮消失后,只剩一堆残骸。这张画布见证了这一切——右上角那一抹纷扰的亮色意味着即将消逝的波浪。椅座上报纸的头条写着:“领低保的老人在街头巷子里遭遇抢劫。”
迷人的想法终会逝去,但总有一些声音重新涌入她的内心,填补空白,挥之不去——有时是喃喃自语,有时是严厉的呵斥。好吧,也算是有点意思。至少,有那么点意思。
她举起手,揉了揉眼,这时,铃声又响起来。电话?她还有些迷糊。怎么还没停机?堆在玄关那儿的信里,起码有二十封是电信公司的催缴单吧。
她一动不动,任由电话铃响着,没有一点去接的意思。未接留言又多了一条。可能是那些所谓的“热心人”打电话来问候她的近况。不管怎样,她压根儿没想过明天再给他们回复,更不会想如何编造借口搪塞过去。
当然,这通铃声也可能是她的幻听。不过,她觉得自己已经同糨糊一般的大脑不会再玩什么新花招了。
她继续睡眼蒙眬地盯着墙上被撕得凌乱的日程表。今天到底是哪天?日子已经过糊涂了。在搞清楚之前,星期四插在了原本应该是星期二的地方,你正盯着的是属于星期五的那个格子。还有那些该死的星期一,混乱得令人作呕。从日程表里看不出一丝日程。根本弄不清楚哪天是兑账日。从来就没弄清楚过。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她觉得该去弄点吃的。她站了起来,地板在缓缓倾斜,就像走进参加主题公园花车游行的马车的门。视野里所有东西的边缘都泛着烟火般的闪光,她牢牢抓紧一把椅子。(“别犹豫!”一个声音在她脑中的一个角落突然响起。)稳住。
她走出房间,穿过走廊,剥落的墙纸上挂着三三两两的钉子,厨房的门厅中弥漫着变质牛奶的酸臭味。厨房里,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扎紧了口,挨个儿摆在厨房的地板上,就像养鸡场里的母鸡。垃圾从垃圾桶漫出来,像瀑布一样,水槽里的餐具堆积如山。
斯玛吉打开冰箱门,电话铃声又凄厉地响起来,她一个踉跄失去了重心。她试着伸出一只胳臂撑住自己,却被电线绊住了。她重重地摔进那堆垃圾袋里,有什么东西被她从墙上扯了下来。头顶的天花板已经裂开了,好在大部分被托住了,不会直接砸到她脑袋上。
她听见另外一个声音,这一次,声音似乎是从身外的某个地方传来。
“艾丽?”一个微弱却严厉的声音,“艾丽?”
她环顾四周。厨房的龙头滴滴答答,一如往常。她把头埋进手里,脸上磨出皮屑。她摇摇头,努力赶走那些幻觉。
“艾丽?”那声音再次飘来。
她转过身从指缝中偷瞄。声音从她身旁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她小心翼翼地抓起电话,举到耳边。
“艾丽?”电话那头的人说道,“是妈妈。嗯,听着,我可没时间跟你傻了吧唧地捉迷藏,我知道是你,尼克给我了你的号码。”
死一样沉默。头顶上,冰箱门因为长时间敞开着,发出了哔哔的警告声。
“行,你要这个样子,我也没办法。”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道,“要不是海伦的事,我才不会打这个电话。”一声轻叹,“出了一场事故,我想海伦大概陷入了昏迷。那个,按道理还是应该告诉你。说真的,我可不愿打这个电话,不过……还是……反正就这样了。我告诉你,总比你看新闻才知道要好。”
她感觉厨房里似乎有暗影涌动着,蔓延着,仿佛一朵畸形的毒花。各种声响在角落里嘲笑她,随时准备扑过来。她却从未像此刻这般麻木和虚弱。
“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伤透了心。”电话里的声音说,“贺瑞斯还能撑住。理查德已经请好了假。”
那团暗影朝她涌来,像烟雾一样翻滚着,穿过塑料的吊顶,这一切让她毛骨悚然。她想动一动,可某种感觉将她牢牢地固定在那里,她有些手足无措,躁动从指尖一直蔓延到脖颈儿。伴随着冰箱报警器的节奏,恐惧潮水般袭来。
“现在大家都争取每分每秒待在医院里。”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道,“当然,很多媒体也在关注这件事。”
那声音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是一声咆哮:“你难道吐不出一个字吗?!”
暗影彻底包围了她,她感觉无法呼吸,眼冒金星。她咽了咽口水,深呼吸,紧紧抓着电话,眨着眼。
(“碎嘴婆子,”她心里炸开一个声音,“才最该死!”)
斯玛吉闭上眼,深呼吸。“恐怕您打错电话了。”她说,语气平静,每个字都得像会计们桌上的硬币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
就在话筒中愤怒的声音几乎要冲出来将她撕碎的时候,话筒掉了。她跌坐回那堆袋子中。一个纸盒正往她的肩膀上漏着什么,但她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她脑中乱成一团。冰箱里的灯光从天而降,阳光般洒落在她的眼睑上,跳跃着,嬉闹着。冰箱发出的蜂鸣声似乎模仿郊区的街道上的旧货车的倒车提示音。哔哔,哔哔。这一切,就发生在不久以前,某个夏日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