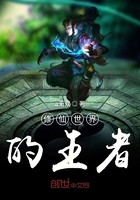“堂下可是湖北龙田镇人士李信生?”
“堂下可是湖北龙田镇人士李信生?”
“啪!堂下可是湖北龙田镇人士李信生?”
李信生恍然,失魂落魄地抬起头来。
台上台下众人惊之。
只见他那紧闭的两眼竟流出两道血泪。
“唉。”作为父母官的县长见此不由得轻轻一叹,下堂将之扶起,温和地说,“这老人是你何人啊?”
“我的师傅。”李信生悲痛又低沉地道,“却胜似我父亲。”
“斯人已逝,生者当如斯啊。”县长轻轻拍着李信生的袖子,宽慰道。
“但请大人为我报仇。”
“定当如此。”
就在这时,门外却突然进来四五人,打头的就是本县的捕头。他看见堂内情况,知道自己抓住的这个犯人是重中之重,可……
“犯人被抓住了。”一旁的师爷提醒道。
李信生闻言浑身一震,连忙回过头,他知道自己看不见,所以就向那里跑,因为不熟悉路,途中还摔了个跟头,却没人嘲笑他。
捕头眉头一皱刚要将之拦住,就见县长大人摆了摆手:
“这是我答应他的。”
张信生扒拉犯人的脑袋,让已经歪了的脑袋对正反向,随后他用手摸索这犯人的五官。
“这人已经死了。”捕头轻声道。
张信生没有理他。
县长却追问:“怎么死的?”
捕头转过身,从手下那里接过一木盘,呈了上去:
“悬梁自尽。”
只见那木盘上正摆放着一道粗厚的绳子。
县长“哦”了一声,心里颇为古怪。就听那名为李信生的少年癫狂大笑:“死得好,死得好!”
笑了两声,李信生又复悲哀。
仇人死得突然,一如师傅死的突然,一切都这么突然。
他恨这突然。
……
……
第二天一大早,李信生孑然一身的行走在忝州城的大街上。
“好冷。”他喃喃道。
街上一如既往,熙熙攘攘的热闹非凡。
阳光晒在他的脸上,他突然不知道何去何从。
“代写,五文一张,童叟无欺!”
吆喝声一如既往的洪亮。
李信生却突然止住,慢慢地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先生,能为我读一封信吗?”
读信?那老书生微微抬起头,只见一位干净俊朗的少年郎站在自己的摊子前,只不过眉眼间有着一种难以掩饰的悲伤和低落,像是家前那只刚被母亲丢弃掉了的狸花猫,让他忍不住地心生怜悯。
“快坐下,信呢。”
“给您。”
老书生慢慢将信拆开,抽出一张写着寥寥几行字的纸。
他扫视一遍,清了清嗓子,缓缓地道:
“忝州的六合学府,教盲人诗书,那里的秦先生我认识,你拿着五十两去就可入学,钱会准备好,不必担心。今后遇到危险,不要提我名字,当好自为之,如到万不得已,亮出你的胎记,一切自可迎刃而解。我死后,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李信生失魂落魄。
“生而不易啊!”老书生微微一叹,将信纸塞回信封。
“先生,请问您知道什么是好好活着吗?”李信生迷茫道。
“活着,仅此而已。”
那活着又于死了何异?这话李信生没有说出口,从怀里掏了半天,没有铜钱,仅有几颗碎银,不知怎得,平常该精打细算的精明劲儿此刻消失地干净,便将银子放在桌上。
“快拿回去!”老书生喊着,却见那少年郎越行越远。
“唉,活着。”老书生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复想起了家中嗷嗷待哺的外孙,一把将桌子上的银子狠狠握住,揣在怀里。
——
“骗子,明明说是有五十两,却放在哪里?那包袱里就几粒碎银子罢了,你为什么抱着求死之心来到这忝州?”
那张信无疑是师傅算的命,算的是师傅自己的——师傅知道自己来忝州会死,遂提前留下这封信。
“在来的时候师傅并未把信交给我,这意味着还不到时候?”
“什么时候是时候?”
“我进入六合学院的时候。”
“师傅为什么觉得自己会死?”
“……”
李信生心中的那个招摇撞骗的形象突然变得模糊不清。
天上突然的掉了雨点,街上的脚步声变得嘈杂不堪。
“预知下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说书人洪武有力的声音在李信生的耳边响起。原来不知不觉又走到这里了。书虽说完了,避避雨吧。他朝着声音的方向走着,临门,抬起脚,而等右脚缓缓落下的时候,框的一声,门被阖上了。
屋子里的客人交头接耳,落在李信生耳中却是鲜有的人情世故。
从前,他或许会觉得有趣,可现在却不那么觉得了。也许是听得多了,也许是心累的已经不再愿意停留了。
“不过就算知道真相又能怎样呢?师傅已经死了,那杀死他的人亦已死了。”
他莫名想起县老爷的那句话:斯人已逝,生者当如斯。
自己是该如同师傅说的那般好好活着吗?可这样不知为之所活的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啪”
“诸位请安静,在下为大家继续说一段故事。”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
堂下霎时间悄无声息,纵使是避雨的路人也难免的想用这段无聊时间听一会儿有趣的故事。
李信生也看向了那人。
这回,那人才缓缓而道:
“在十八年前景国与卫国交战的时候,有一家人居住在景国的边关上,这家人姓李,是当地的豪绅,他们早早听到了交战的消息,遂早做了打算——那便是逃开,去更安全的地方。这家人就一个儿子,在发生战乱的前年刚刚娶了亲,夫妻琴瑟相和,恩爱有加,还为老人们生了个大孙子。
本来他们做好了准备逃离,可谁想那敌国的铁骑却突然杀向了这边陲小镇,这家人马上逃离,他和父母坐在一车,亲自驱使,他的儿子和妻子坐在一车。
幸亏准备的快,他们逃了出去。可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已经逃出危险之时,一队铁骑却迎面杀来。
敌人凶猛,家中护卫不敌,那家二老护儿心切,死于敌人刀下,那人的屠刀生生砍在这七尺男儿的心上,可他又能怎样,他只是一豪绅之子,怎能敌的过那虎狼!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景国的军队来了,那屠夫顾着逃跑,让他留下一命。
不过他的妻儿却尽被那贼子掳走。
在这之后,他深入敌国寻找妻子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那屠夫。
可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自家妻子被那屠夫……
他恨,他想撕碎自己的萧,毁了那放在屋子里的琴,更想杀了那贼子。
可一个饱受战乱摧残的普通人,怎么能够?
他决心要活着,要为了死去的父母报仇!为了死去的孩儿报仇。
至此,他不光是留心着那人的下落,更是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的好本事。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景国的铁骑,却已经踏进了卫国的边关。
屠夫战败,一切好似上天的报应,可他却不信那屠夫已经死了。
往后,他苦苦追寻那屠夫的痕迹,功夫不负苦心人,那屠夫终于被他找到。
原来他根本不在卫国,而是在景国!
那屠夫在战败后侥幸逃脱,藏在寺庙里,后来换了个身份出来。
屠夫以为别人找不到他,可却忘了那被害了全家的人。
萧清河,这个名字我这十八年的每个日夜都忘不掉。”
堂下寂静一片,听书人目瞪口呆许久……
李信生却大吃一惊,那名字他记忆犹新,昨天晚上的那个凶手也正是喊出了这一个名字。
没待他想多久,前方的那说书人的声音就向他步步逼近。
“那萧清河隐姓埋名三十年,竟换了和我同一个姓氏?他配吗?”
“李若梦,他这屠夫若是一生似梦,那怎么就我在这苦海艰难挣扎?”
“我恨,所以我好好活着。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杀死他。”
“可有人却不给我这个机会,没关系,他和那个女人的儿子还活着,为了我的儿子我要报仇杀死他的儿子,佛说因果有循环,那今天总该轮到我了。”
说书人轻轻抬起手,抚摸着李信生的眼睛:“好好的人,怎么瞎了呢。”
“可惜啊,可惜。该让你见到我的样子的。”
李信生心里复杂,原来这就是真相,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真相。
自己的师傅就是他说的所谓萧清河,那个灭人父母,虏人妻子的敌国屠夫。
“你说的是假的。”李信生声音颤抖。
说书人微笑着摇头,语气平静:“我从不说假话,你应该感受得到。”
“不,我不信。我师傅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他甚至连杀鸡都不敢。”李信生挣扎,意欲逃脱。
说书人却把着他的肩膀冷笑视之:“这就是事实,这就是苦海。”
“我来为你解脱吧。”说罢,他便扬起了右手。
就在这时,角落里,缓缓走出一位中年男人,一边拍手一边叹道:“无趣,无趣。”
说书人的手不知道为何停了下来,乜斜着那中年男人:
“离远点,不管你和那屠夫什么仇什么怨,这个人该轮到我报仇了。”
而当李信生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心里倏地出现了一个人影,他惊恐莫名:“你怎么还活着。”
说书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那中年男人却未对此答话,而是笑着道:“这段戏不够精彩,不如我再加一段吧。”
“这故事还是得从十八年前说起,上回说到,那男人的妻儿被萧清河掳走,而在掳走之后,那萧清河对她威逼利诱,女人抱有死志气自不愿从他,继而他又以那孩儿威胁,女人仍不愿就范,对他说道‘你杀我男人、父母,此仇不共戴天,我的孩儿若泉下有知,想必也不会怪我。’那萧清河听了怒火中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拍晕了那女人。这女人也是怪,之前说的干净利落,决绝如此,之后就像是忘了一样,待那萧清河同自家男人……
这孩子自然也就未死,并且被那萧清河一路抚养长大。
就是被景国军队俘虏也未忘了这孩子。”
说书人听了这话沉默半晌,又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何必明知故问?”中年男人道。
李信生听着这话心内莫名奇妙的烦躁,仿佛有什么在破碎,在崩塌。
说书人颤抖的要将李信生的胳膊拾起,撸起袖子,那白皙的皮上正画着一道似小剑一般的红色胎记。
“孩子,孩子,原来你没死。”
说书人泪流满面,双手犹似铁钳握住那个有着胎记的胳膊。
李信生却不知道该怎么答话。
他本不是个说话会犹豫、遣词造句的人,可此时此刻却像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