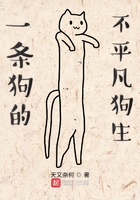冷,忝州城的天气还是那么的冷。
“十八年前我来过,以为不会再来,没想到终究还是来了。”
湖北老相师李若梦紧了紧单薄的衣服生出感慨。
后面被他牵着的少年抓住雪花,眼睛一眨不眨。
以为抓住冬天?其实什么也没留下。
少年任由水珠从指缝中消失。
这少年姓李名信生,十八年前还是婴儿的时候在忝州城被李若梦捡到,后来这俩人就成了师徒。这十八年的春夏秋冬就像是一个短暂的瞌睡,微微地翻翻眼皮就到了今天。只不过李信生十多年来从不爱翻眼皮,因为他看不见这世间是黑是白,分不清男人的英俊、女人的美丽——只因为老天没有赏他一双正常人该有的眼——在龙田镇,街里街坊都管他叫李半仙,一是因为他有个算命的师傅,二是因为他是个总加常人臆测的瞎子。
李若梦牵着李信生的手,进了一家客栈。临了进门的时候李信生却将手从师傅那双铁钳中挣脱开,李若梦拍了拍他的头什么话也没说,掏出挂在胳膊上的一串铜钱,开了一间房要了壶茶水,递给了自家徒儿:“楼上左拐第二间,自个去吧,师傅出去有事。”
李信生心领神会,接过茶水便要往楼上走。
这时,一只手握在他的腕上将他拦住:
“小哥一个人上楼可行?”
原来是店小二看见李信生那紧闭的双眼,略微有些担心。
踏出门槛的李若梦回头一笑:“没事儿!”
门外,雪满街头。
“我走得了。”李信生将他抓着自己的手挣开,扶着把手一步步往上走,虽然速度不快,却不出差错,就像是看得见一样儿。
店小二目视着这小哥儿的背影,轻轻一叹:
“这么俊俏个人儿,怎么就是瞎子呢?”
“嘿,别看人家是瞎子,保不齐比你活得更快活!你没听说那城南李半瞎吗?算一次命,够我喝十次酒,可神着呐。那话怎么说?睁眼看的是人,闭眼看的是鬼,啧啧,要算命还得找瞎子!”
店小二往那一瞧,说话的这位爷脸蛋红的跟个猴屁股似的,不由得尖叫一声:“哎呦,爷儿,你怎么又喝了这么多。”
“不算事!”他轻蔑地挥挥手,又喝了口不算呛人的酒,不知怎得眼前就出现了皮子白净、臀子硕大的朱寡妇,心中不由得一热,“得找小算命的问一问,这朱寡妇啥时候能从了俺。”
……
少年人终究少年心性,回到房里,李信生便不顾冷风地打开窗户,霎时间,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卖猪肉的、卖狗肉的、吆喝的、唱戏的、五光十色,无不有之。但他还是最惦记那说书的,只听那嗓音浑厚的说书人还在哟呵:
“狐妖进了书生门,书生进了狐妖心,这一妖一人,竟阴差阳错生了情!看那狐狸,白面媚眼、娇娇滴滴,犹是铁面无私的判官老爷也动了心,何况这足不出户的书生,我看啊,情有可原!哪想有一天,这隔壁老母突然闯进门,狗血如墨泼洒连天……”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说书的道了一句:预知下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李信生还意犹未尽:“怎么讲到精彩处就留到下回啦?”
门外兀地响起一轻一重的脚步声,他连忙将窗子阖上。
“哎哟,屋子里怎么那么冷!”
比外面还冷!刚进门的李若梦打了个喷嚏。
李信生面无表情地转身道:“冷就多穿点,都什么天气了。”
李若梦哼了一声,将手中的东西朝着自家徒弟站着的方向晃了晃。
“阳春面。”
“鼻子倒是灵巧。”刚说完,却见自家徒弟已经正襟危坐在饭桌旁了,不由得开怀大笑。
“情况怎么样?”将滚烫的面条吸入肚里,李信生口齿不清。
李若梦打了个哈欠:“还能怎么样,你师傅我从来不都是马到成功?”
“那明天就不怕了。”
“是啊,不怕了。”
李信生有些困惑地抬起头,这句话的语气有些不对,可他纵使抬起头,也看不见师父脸上到底是个什么表情,不禁失落,便继续低头吃面。
所谓算命,就是江湖骗术——他不知道别人算命是否如说书里的那般神奇,但自家师傅的,他总归是知道的,要算命首先要摸底,摸清楚那些人家的底细,这样算起来就显得措置裕如了——但他现在不免的有些担心,这摸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咚咚”地敲门声突如其来。
“谁啊?”李若梦望向房门。
那人并未回答,反而问道:“屋内可是算命的?”
李信生停下筷子,听那声音浑厚有力,似是一个壮年男子。
“不是。”李若梦想也不想地回。
听到这里,李信生再次吃面,他知道师傅有个规矩的,便是“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没想到那人却不依不饶:“怎能不是?我是刚才在楼下喝酒的人,亲自看见你开了房,那布上写着‘铁口直断’四字,想是算命的。”
李若梦皱着眉头:“我今天不算!明日再来。”
“不成,就今天。这样吧,我这里有一百两,权当赔罪。”
“一百两?”李若梦大吃一惊,“你是什么人?”
“楼下喝酒的人。”
“嗯……”李若梦心底有些犹豫。
李信生听到这里,拉了拉师傅的袖子,小声地道:
“拿一百两算命的这般冤大头,想必也好糊弄。”
李若梦有些复杂地看了自家的徒儿一眼,再望向门口,眼中神采莫名,半晌才缓缓开口:
“来者即是客,这便开门!”
说罢,就将锁着的门闩拉开,只见门外站着一穿着布衣的中年男子。
看到他的穿着,李若梦的热乎劲没了:“一百两?你怕是拿不出来。”
“怎能拿不出来?你看这是……”
“你……”李若梦的声音戛然而止。
“扑通。”
那个人的声音却还未停下:
“我来算的是,萧清河的死期。”
“这债得换,我看不惯。”
“再会!”
不远处,饭桌上的面还未冷,却被仓皇失措间打翻。
李信生被桌子腿绊倒在地,脸上闪过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