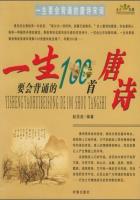空翠。很喜欢这个词。可以让人因空见色,自色悟空,正如《红楼梦》所言。王维的诗,《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空翠,是一种氛围。它就在那儿,无处不在的样子,很美好,但又无法触及。也许正因为无法触及,才如此美好。我少年时总想突破种种限制,现在能意识到限制也是一种美好。庖丁解牛,正是清楚限制在哪儿,所以才能游刃有余。
2010年12月,我到陕西秦岭山区游玩,初冬的下午,漫步于金丝峡大峡谷。四山静穆,空旷无人。天气虽然很冷了,松竹丛杂,林木犹绿,正是空翠之意。据说山中兰草很多,我寻了很久,却未见一丛。“空翠湿人衣”,王维诗中前两句是写秋冬之景,如果是写实,那么最后这个“湿”字下得太重了,重得使诗句有了盛夏之意。如果“空翠映人衣”呢?也不对,太亮了。王维的另两句诗,“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同样写“色”,就很轻灵准确。
王维有悟识。悟识高的作者极少,近当代作家中,悟识好的有胡兰成、废名、顾城。阿城差不多也算一个。废名没有发展好,他极为可贵的独特的文学个性,后期完全废掉了。
木心也有悟识,看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他的修养、气度和识见绝对是一流的,但他的原创作品相对于此,却有很大一段距离。这是为什么?直到有一天重读维特根斯坦的一本笔记小册子,无意中看到这几句话,我才算彻底明白:“即便最精微的鉴赏力,也与创造力无关。鉴赏力是感受力的精炼;但感受力没有做任何事情,它纯粹是接受性的。”
朋友谈日本文学,谈及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认为前者的文学才华要远远高于后者。和谷崎润一郎相比,写人性的幽暗、曲折和繁复,川端康成太清淡,显得小资了。但川端那种细腻到骨子里的感受力,却遥遥领先于谷崎。川端在《山音》中,写人性中那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背面敷粉,却造成某种不便言传的氛围,正是“空翠湿人衣”。
我在微雨中到小区转了转。里侧花带中那株梅花正在开放,昏暗中既看不见色,也闻不到香,只看到很多花朵的影子,在夜空里疏疏横斜。但你能感到那种花开的感觉,就在你周围。
清人笔记《冷庐杂识》中有一对联,“炉火红深,与我煨芋;窗树绿满,烦公写蕉”。是写给一个和尚的。我不是和尚,却很喜欢此联。绿树映窗,也有空翠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