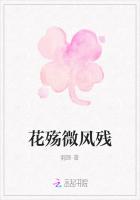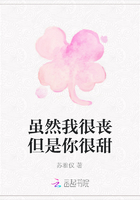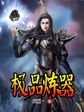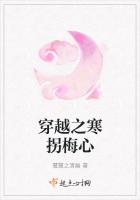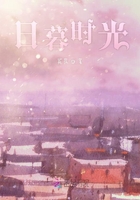我要承认让我提起笔来,是因为刚刚看到过的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的第一段话:“小泳,我日日夜夜止不住地悲伤,不是为了世间的错误,不是为了身体的残败病痛,而是为了心灵的脆弱性及它所承受的伤害……”在那个冬日的下午,这句话打到了我,隔着电脑冰冷的显示屏,隔着玫瑰花茶蒸腾而起的白色水汽,隔着和同事之间有一句无一句的抱怨,彼时,我35岁,离认识苏铃,已经过去整整十五个年头。
记忆的潮水总是这样汹涌,奔流不息却又无知无觉,总让你裹挟其中,让你感觉似乎是时间和生活的主人,而又让你明白,那只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像。正如我此刻开始回忆苏铃,但我却不能不从内心最深处承认,我对于苏铃的怀念和记忆,事隔多年以后,早已打上了各种变形扭曲的烙印,对细节的美化,对痛苦的强化,如海滩边如雪般绽放的虚幻浪花,蔓延无度却难以还原。
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整整十五年,我没有再见到过苏铃,保存在我的记忆中的,始终是那名高大健美的鲜活少女。我何尝不知道人会衰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迈过三十的大学同学们开始集体怀旧,而我也因此,得以在班级的微信群看到苏铃的近照。她的身量比我印象中小了很多,可能是因为瘦下来的缘故吧,笑起来仍十分好看,露出招牌式的雪白牙齿,只是眼神比大学时悒郁了许多。虽然从群里的描绘来看,她仍属于有幸运女神眷顾的类型,家庭富足、夫妻和睦,只是,生活的重担总是或多或少辗压过每个人,没有例外——除了那些年纪轻轻就终结了自己生命的孩子。
想起来多么疯狂,我差点也成为那样的孩子中的一员,并且,我至今也还认为,拿把剃刀切开动脉,并不是一件太艰难的事,只是我不会再做而已。正如如今我已经成长为,年轻时所不希望、不愿意看到的那种人,世故、自私、冷酷、势利。
然而,这不过是每人生而在世保护自己的盔甲而已。
所以我在冬日沉沉的雾霭天中怀念当年,在统计报表枯燥乏味却必须精准的数据中,在对孩子的关注担心和呼吸道疾病增加的忧心忡忡中,在漫长会议连手机小说也无法打发的无聊点滴中,我仿佛能感到,只要一仰起脸,仍能浸到当年清凉如水的月色,以及月光下苏铃俯身向我的脸庞:莹洁、丰满、笑而不语,宛如一轮满月宁静。
苏铃,隔了那么多年,我轻轻呼唤她的名字,我仍能感受到从心底震起的阵阵悸动。这清脆的发音,好像花一样枝蔓横生,有娇嫩如须的小茎,青轻,柔脆,却有玉一般的颜色,好像旧时的月色从未褪去,好像那一年的凤凰花开,艳红的花瓣一簇簇覆过来。
我怎能忘记她,那和青春一起葱笼,也一起死去的人,她见证了我一整个惨绿青春。曾经我走到了生命的悬崖,只因为她,事过境迁后可有种种后怕?我的记忆里铭刻着她月光下的脸,俯身向我,微笑如花,眼波澄澈如水。哦,苏铃。
记忆是否会欺骗人?正如我们小时候看过,认为非常巨大的人和物,等到我们成长为成人身量,发现小时候的眼光有失偏颇,在不同的视角里,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我第一眼所看到的苏铃,美丽灿烂,然而不过如此,也许是因为少了一份情感灌注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大学伊始,有太多新鲜的人和事等着我们去挖掘和发现,美丽的苏铃只是其中背景图的一部分。要是这样,她也许就会像我本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在我的大学生涯中,面目模糊地飘过,然后消失,不留太多的痕迹,更遑论对彼此的生命产生斧劈刀刻般的影响。
斧劈刀刻,多么重的一个词。我不知道在我的大学里,遇到这样美丽的同性,是幸,还是不幸。当我挣扎着从情感的阴影中走出,从苏铃的令人窒息的美和伤痛中走出,发现任何浓冽的美也激不起我太多的兴趣时,我的心也为之震慑,为之而哭,哭我再也不能如此敏感多情的心,哭我从此的冷漠和从容。
若干年后,我问过研究生同学贺箫,青春是什么?
彼时,我们坐在Z大洁净的石栏杆下,放眼望下去,巨大的操场尽收眼底,底下有一排排的小人在操练,那是新一届的新生军训操练,年轻而稚嫩的嗓音划过天空。贺箫眼神凝滞了一下,缓缓说,我不知道。
或许,青春就是一场瘟疫,一定要发过,发了,就好了。
这是贺箫给我的答案。彼时我们研二,已不再天真烂漫。生活漫漶无形的压力却也还未彻底涌来。然而,贺箫给我的答案仍然模糊不安。并没有一个敞亮明净、干燥舒畅的青春,如果有,那一定是假像。我和贺箫喝完易拉罐中的可乐,把易拉罐踩成薄片,喀嗒一声,有撕裂般的快感。
贺箫和苏铃多少是相同的类型,高大、丰满,血色饱满的双唇似乎要嘟出来,眉眼漆黑。贺箫爱把漆黑的长发牢牢编成麻花辫不带任何女性特征地做调查、写论文、做演说。在我的生命里反复出现像苏铃这样的女子,多少说明,年轻时的审美影响烙印何等之深。其实,我从未走出。
也许,我需要的是如外科医生般的精确,在事隔多年之后,把那一场瘟疫的诸多细节,一一道来,看着血肉模糊的青春,如何淡了肌理和纹路,在巨大的痛楚中,那如岩画般深烙的场景,才会一一再现。
致我无处安放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