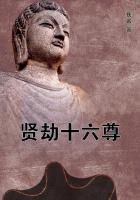在桥镇,出行很少坐车,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坐船。
乌蓬小船靠岸,沈愚山付了船资,背着书箱抬步上岸。
今儿天气正好,阳光明媚,一扫前些日子细雨蒙蒙的阴沉,岸边有许多人家的家门口,竹架子一溜儿排开,晒着大大小小的渔网,好些汉子拿着锤凿敲敲打打,正在修补船只。
这一片大约都是水上人家,即是在水面上讨生活的穷苦人家。沈愚山这么一个打扮干净的白面小书生忽然来了这里,顿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沈愚山没在意那些流连在身上的审视目光,近些日子江面上不太平,僵尸阵闹得沸沸扬扬,已经有好些个渔夫杳无音信,估摸着就是遇害了。
故而,村子里忽然来个陌生人,谁都要在意几分。不过,沈愚山的打扮倒是很能降低人们的戒备心,自问这么一个俊哥儿,不大可能是坏人,即便是坏人,这么多年轻力壮的汉子,足以将其制服。
汉子们互相交错着视线,隐隐戒备着。
只不过,若是叫这些汉子们知晓,在他们眼前的这平凡少年,曾经一夜间斩尽了芦苇泊数十名湖匪恶盗,怕是要吓得瞠目结舌。
沈愚山提着几包东西,张望了几眼,走到一户人家面前,发现了几个围蹲着的光屁股小孩儿,走近一看,才知道这几个孩子正拿着木头小棍戳蚂蚁玩。
“叨扰片刻,请问你们知道老艄公家在什么方向吗?”
“老艄公?村里有好多呢,你找哪个?”孩子们挠挠屁股蛋,又挠挠脸。
沈愚山又笑道:“给城隍庙沈家开船的老艄公。”
这下子,几个孩子立刻便知道了,沈家逢年过节常送东西,一些点心零嘴儿,老艄公全散给这些孩子们了,所以一说起是给沈家开船,立刻便知道是哪个老艄公了。
几个孩子齐齐指了个方向。
沈愚山谢过,下意识就去摸口袋掏几个钱,然而又忽然顿住了,他的钱全在芦苇泊撒了个干净,身上仅剩的这些钱,还都是暂且跟先生借来的。
沈愚山尴尬的笑了笑,从手上提着的几包东西里抽出一样,送给这些孩子们。
这个时候,沈愚山发现已经有几个汉子走了过来,大约是看到他和这些孩子说话,心里头不放心,沈愚山挥挥手,朝着孩子们指着的方向,慢悠悠的去了。
孩子们彼此对视了一眼,把油纸包着的东西打开,原来是切得整整齐齐的肉鸭膏,脂肉分明,油光灿灿,立时欢呼一声,顾不得手脏,高兴得争抢了起来。
几个大人走到近前,发现没什么事情,安心了许多,然后困惑转眼间又在心底油然而起:
“怎么今儿个,这么多人来找老艄公?”
……
……
老艄公住的地方有些偏僻,在一片半人高的草林子后头,一座简单的木屋静静矗立。
离着路口还远,便有一拨人从坡上拥着下来,沈愚山眼尖,发现这些人是桥镇的护卫队,众人围着一个塌鼻子道士。
“呦呵,怎么是沈家二郎,你怎么来这儿了?”
正陪着塌鼻子道士说话的粗豪汉子,瞧见前面路边立着一个俊朗的后生,发觉是城隍庙沈家二郎,惊奇了片刻,打了个招呼。
“我还想问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呢?”沈愚山不答反问道。
对面的粗豪汉子是护卫队的队长,名字叫做张林,他原本不姓张,而是随母姓林,只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受到张员外的照顾,遵从亡母遗命,改名叫做张林,颇有身好功夫。
张林在护卫队很有威望,桥镇百姓也支持他管理护卫队保护一方平安,即便是镇长张开钱,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护卫队去操办的,也只能通过张林差遣护卫队。
张林闻言,脸色顿时一沉,肃声道:“还不是那僵尸阵闹得……”
“不是僵尸阵,是僵走,这是两码事。”那塌鼻子道士忽然打断道。
沈愚山不由得抬眼打量了对方一眼,这道士居然能分辨得出僵尸与僵走,看来有几分门道。
“对头,对头,我又记岔了,是僵走。”张林拍着自己的后脑勺,继续说道:“听说老艄公已经很久没出现了,消失的日子正好和僵走阵闹起来的那几天对得上,我们来查一下有什么线索。”
“查到什么了吗?”沈愚山为老艄公的遇害有些伤感,立刻追问道。
张林一指身边的塌鼻子道士,介绍道:“这位是马道长,我们是陪他来的,具体有什么线索,得问马道长。”
塌鼻子一扫拂尘,说道:“无量天尊,俗家姓马,草字纯良。”
“原来是马纯良道长,请问发现什么线索了吗?”沈愚山追问道。
马纯良低眉垂目地摇摇头,自然是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老艄公便是当初救他,反被他一脚踹下江里,让僵走们分而食之,活活咬死的。
双方寒暄几句,沈愚山便继续往山坡上走去。
待他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马纯良搓了搓塌鼻子,嗅嗅沈愚山穿过的空气,眼底掠过一丝惊愕,这是……杀人放火的味道?
是火星气和血腥气,不仅仅是人血,还有僵走的血。
马纯良的脸色顿时蒙上了一层隐晦不明,带着几分探究的心思问道:“刚刚的这位俊后生,是谁家的孩子?”
张林笑说道:“城隍庙沈家的二郎,说起来他祖父和道长是一样的,也是仙道散修出身,在咱们桥镇这儿安家落户了。”
“哦,是吗?”
马纯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
……
距离老艄公遇害的那天,时间已经过了有些日子了,正巧前几日落雨纷纷,山野间的草木绿植疯长,老艄公屋面前已经满是杂草。
沈愚山小心趟过草丛,一路走来,倒是没有以前常见的蛇虫鼠蚁,沈愚山心中了然几分,约莫是体内的灵元流动,这些蛇虫鼠蚁趋吉避凶,躲着他吧。
山里木屋只要有些日子没人住,就不免有许多动物来安家落户,沈愚山的到来吓得好些黑不溜丢的小东西落荒而逃,沈愚山笑笑,挥手扯去蜘蛛网,走进了屋内。
人死魂消,老艄公又不是修行之人,可没有保护自己魂魄不散的法子,这也导致了沈愚山无法动用手段招魂,当面询问老艄公究竟是如何而死。
罢了,不出所料,应是缰走阵无疑。
沈愚山叹口气,自打他去竹林书屋读书,便是老艄公每日载他往返,风雨无阻。他小时候顽皮贪嘴,回家的路上嘴馋想吃花糕酸枣,老艄公有时自掏腰包给他买了吃,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叔叔婶婶。
直到渐渐长了几岁,初懂些事,沈愚山才明白老艄公简单朴实但又情真意切的爱护关怀。他尚且记得,那日老艄公来家里吃酒,贺喜他新婚大喜的满脸笑容。
然而,老艄公被僵走害死了。
不,准确的说应该是被操纵僵走的山魅害死了。
沈愚山暗自咬紧牙关,将老艄公之死深深刻印在心底,等到他成就通幽境的实力,便要上乱葬岗,剿了这害人不浅的山魅。
深深呼一口气,沈愚山找来一张小木桌,把手上提着的东西一一打开,一壶小村浊酒,一包卤煮猪头肉,一碟茴香蚕豆,东西虽简单,但却是老艄公生前最爱吃的酒食。
恭恭敬敬作揖,敬一杯水酒,尽数撒在了地上。
再斟一杯,沈愚山一饮而尽,辛辣的回甘荡漾在喉头,酒液淌入肚腹,烧心得难受。
俗礼已过,沈愚山转身欲走。
倏忽间,人顿住,抬起的脚尖始终没有落到地上,就那么悬在半空。
只因,洒在地上的酒水,仿佛受到了莫名的牵引之力,就那么流淌开来,渐渐勾勒了一幅简单却又传神的画像。
画中人是一个道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满身污秽落叶,狼狈慌张的样子。
沈愚山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只因画中的道士……脸庞中央长着很是少见的塌鼻子。
“喂,沈家二郎是吧?”
背后忽然有人叫他。
沈愚山心肝儿咕咚咕咚跳得像在打鼓。
转身,回首,张望。
画中的塌鼻子道士,正站在门口,笑吟吟的打着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