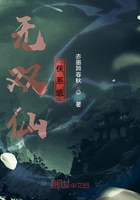干什么活就得有什么本事。
路远杀过人,也摆弄过炉灶,当然是在另一个世界。
他回忆起来了,在那里,他曾经当过一名火头军,一个既会杀人,也会做饭的老兵。但除了锅铲瓢盆刀,他唯一学过的杀人兵器是一种需要离得远远地,扣动扳机的长棍,名字叫枪,只有离得近了才会像长矛一样使用,但招数也不多,无外乎刺、格、挡、挑这几样。
这就是两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反正他在这里没见过长这样的枪,只能勉强耍着外貌有些类似的长矛。
这算不算是入乡随俗?
……
现在,老斧头的尸体需要下葬。
葬礼这件事,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习俗,路远理应遵循此地的习俗来安排,但他这时却发现,有时候想入乡随俗都有些困难。
之前,路远以一种不怎么情愿的方式,旁观过一次这里的葬礼,西山家老白首的葬礼。这一次算是近距离接触了此地的习俗,可他很难复刻出来,毕竟还有很多细节都不知道,就算强行模仿,现在的条件也不允许。
尤其另两个清醒的家伙——大个子与小石头,他们对于怎么操办葬礼也是一无所知,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现在怎么办?总不能随随便便点起一把火,就这么烧了不成?
葬礼之所以为礼可是需要仪式感的。
路远没了办法,只能不再坚持入乡随俗这一点。
吃完饭,他带着大个子去野外挖了个土坑,再把老斧头的尸体埋进土坑,重新堆上土,多出来的土在上面隆成一个包。
找来一块木板,用木炭在上面写上“老斧头葬于此处”,插在土包前充作墓碑。
没酒,就洒了点水,没香,就烧了点枯叶。
关键是有人叩首。
这完全都是仿照路远记忆里入土为安的习俗,可能来自于他的家乡,而且还是简化的。也不知道地下的老斧头满不满意。
不过在路远想来,他应该没什么不满意的,毕竟丑儿被救了下来,西山家也遭了报应了。
再说,以这里的世道,身为“贱奴”,活着才是不易,死了反而是种解脱。
这该死的世道!
有谁会喜欢做一名“贱奴”?
……
带着对救命之人的感恩之心,就算条件简陋,路远也是带着严肃的态度,一板一眼地做完每一个动作。
这种肃穆的气氛也感染到了身后的大个子与小石头,他们虽然看不懂,可也安静的待在后面,一样一样地学着做。
回去的路上,小石头突然开了口。
“路家贵人,哦,不,路……远?那个,我的姐姐也被埋在了土里,你能不能也给她们做一套之前那种……葬礼?”
“可以!”
“要堆个土堆,要插小木牌子,上面写上她们的名字,要洒水、要烧火、还要磕头!都要!”
“可以,都可以,但不是现在,回头我领着你去弄。”路远原本还想顺手摸下小石头的脑袋,安慰下他,可看见那板结黏连在一起,一缕缕的,仿佛带着扎人锐角的头发,最终还是没有下去手。
……
现在还有更急迫的事情,毕竟回去后,有两个病人等着照顾呢,那可是活人命的事。
醪奴与丑儿的高烧始终没有完全退下,人也是昏昏沉沉,在半梦半醒之间辗转往复。
最是需要休息的时候。
所以今天连老斧头的葬礼都没带上丑儿。
……
回到草庐,先烧了热水。
路远从小石头换回来的衣服里,挑了一件干净的拿在手上,让大个子站在一边仔细看着。然后他把醪奴从枯草堆里刨出来,扒去已经被汗水打得湿透的破衣裳,权当那干衣服是毛巾,先把身体表面的汗水擦去,再沾上热水拧干,反复用力擦拭胸背,直到皮肤被搓得红彤彤的。
醪奴在半途中醒来过一次,舒服地哼哼唧唧了几声,但很快,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
最后路远重新找了件干衣服给醪奴换上,反正小石头用肉换来的衣服足够多。
一套做完,路远告诉大个子,这是示范,一会其他人都会出去回避,让他也给丑儿照做一遍。
听完,大个子看着路远发了会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一张脸立时变得羞红,就算那黝黑的肤色也遮掩不住,如同被蒸熟了一般。
路远感觉如果一直这么下去,大个子的头上迟早能冒出烟来。
“啊!”
这时,丑儿躺卧的方向传出一道短促的轻呼,接着窸窣间翻转了身体,面朝墙壁。
嗯——看样子也是醒着的,没反对就行。
玩味地观瞧了两人半天,路远总算“好心”地收回了视线,让大个子能够冷静下来,省得被自己灼热的情绪“烧死”。
再回头专心帮醪奴正骨,上药,夹上木板,绑牢。
可惜小石头没能换回疗伤和退热的草药,据他所说,尖奴他们那边也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要收集草药,各种类型的草药都没有。
处理完醪奴的腿,路远叫来小石头一起把他小心地抬出去,晒到太阳底下,把草庐这个私密空间留给大个子与丑儿两人独处。
擦身虽然是件一点都不困难的小事,但毕竟男女有别,也就大个子与丑儿的关系几乎都挑明了,要不然还真没合适的人。
只是出来了半天,草庐里都一直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咳——”路远故意干咳了一声。
一串明显透着慌乱的杂音立时响起,传了出来……
……
坞堡里的火已经灭了,几道黑烟袅袅升起,一直到极高处,才慢慢变淡散去。
一片白里掺黑的云朵从远处飘来,压在了头顶。
两个人影并排从坞堡里走了出来,彼此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
……
小石头没定力陪着路远一直晒太阳,出去转了一圈,带回了新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怎么打听到的。
坞堡里的吃土奴大部分一早就散进了山林里,现在剩下的又分成了两派,选出来两个头头。
就是刚刚出来的那两个,现在正在尖奴那边商量事情呢。
小石头说得很是兴奋,但路远只是无所谓的“哦”了一声,就再无下文,直接打断了他说话的欲望。
……
“里面的,动作快点,不怕…再着凉吗?”
大个子与丑儿磨蹭了许久,直到路远忍不住了。
一阵窸窣声后,大个子终于把门帘挑开,示意可以进去了,但始终低着头别着脸,不敢直视路远。
路远刚想进去,就发现有两个人一左一右,并排从远处走了过来。
左边那人身形略高,脸上笑嘻嘻的,头顶秃了一片头发,秃发处有着一块显眼的烂疮。身上穿着一件艳丽的红色衣服,也不知道是衫还是裙,而且尺寸明显不合身,紧窄绷紧,明明是长袖,可袖口却高高吊起到手肘处,行走中连手臂也摆动不开。
红色衣服的样式一时看不出男女,可不管怎么样,一大男人穿着,怎么看怎么妖异。
另一人较矮,身上却穿了一件相对身形过分宽大的素色长袍,下摆都已拖到地上,染满了泥浆,行走也多有牵绊。虽然这人肃面直视,刻意将一手搁于体前小腹,一手收至背后,一步一停,力图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可踉跄之间却更显滑稽。
“这就是刚刚坞堡里出来的那两个吃土奴,他们之前先去了尖奴那边。”
“红衫的那个叫烂头,是从林子里抓出来的蛮子,平时就有点刺。”
“矮的那个是庭家人,大家都叫他束奴,之前挺老实的,这次不知道怎么就跳起来了。”
路远想起了小石头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在下游被西山家灭掉的庭家。
烂头远远地就向这边打起了招呼,虽然能听懂,但异地的口音确实很重。
“远奴是吧?叫我烂头!听说你是个好手?”
另一边的庭束到得面前两步左右,才停下脚步,并腿站稳,一板一眼的拢手躬身行礼。只是看得出,动作其实也不熟练。
“庭家子,束,见礼。”
……
上门为客,打过招呼,路远让开道,请两人进了草庐。
挤开庭束,烂头当先钻了进去。
“打扰了。”庭束未受影响,依旧规规矩矩地行完谢礼。
烂头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到火塘边,一只手肘撑地,几乎半斜躺在地上,一点也看不出吃土奴曾有的那种怯弱。庭束进去后,嫌弃地瞄了眼烂头,走到火塘的另一头,毕恭毕敬地跪坐于地上,姿态谨慎。
路远是最后进去的,小石头都走在他前面,一脸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事情的急切表情。
“听说你们很会打?”还未等路远坐定,烂头就开了口。
路远没有接话,微微一笑,反问道。
“两位准备做什么?为什么…来找我?以什么样的身份?”
“嘁——和你们这帮有姓人说话就是麻烦!”烂头一脸不耐,“有吃的、喝的吗?给我烂头送上来点,还有说在前头,我们是苦命人,不喜欢听人叫我们吃土奴,小心翻脸。”
路远点点头,小石头给他倒了一碗水递过去。
烂头也没起身,用一只接过水,先喝了几口。
“要知道我现在说话有多少人听吗?告诉你,里面的人现在全听我的!”烂头说话时的情绪很亢奋,动作也大,完全不顾手中的碗盏,不时有水洒落出来。
“慎言!并不是全部人!”庭束往旁边挪了挪,拉开距离,皱眉道,然后转向路远,“确实有很多人被他蛊惑,但不包括我,还有不少人想法与我一样!”
“是、是,其他人都知道我厉害,就你们几个傻子看不出来!”烂头气急败坏道。
“所以你们不是一起的?”路远问道。
“自然不是!我这边且等他把来意说完,再与你商议!”庭束应得斩钉截铁。
“你们这班有姓人的心眼都坏得很!”瞪了一眼庭束,烂头气哼哼地说道,“我要说的事情很简单,你们昨天冲出来的时候,杀了不少我们无姓的苦命人!这帐要不要算算?我也不要你们赔命,我们里面需要能打的,你们自觉点进去赔个不是,以后好好听我的话就行了!我不嫌弃。”
闻言路远笑了。
“可我觉得这帐…没什么好算的,他们上前挑事,我不能还手吗?”路远没有提坞堡里那些仆奴女眷的惨状,也无意为那些人伸冤报仇,毕竟很多伤害是相互的,只是当时立场倒转了而已,双方其实都有不堪。
“也没有什么不是…好赔,我们更不愿跟在谁的身后,听谁的话!”
烂头愣了一下,仿若完全没想到路远会这么回答一般,顿时气急败坏。
“你、你、你说不算就不算了吗?你们这些有姓人还讲不讲理?信不信我们里面的苦命人出来把你们这推平了?”
“哦?你是在威胁我吗?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就此把你留下?省得你回去再煽动人来对付我们?”
原本坐在丑儿铺前的大个子猛地站了过来,虎视眈眈。
烂头立时傻了眼,“呃——”的一声打出一个紧张的水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