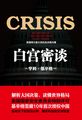历史对清官循吏的含义有进一步的解释:“吏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世称曰廉。才足以经济,智足以决断,世称曰能。奉法遵职,履正奉公,世称曰循。明国家之大体,通古今之时务,世称曰良。”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合格的官员需要哪些条件,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清官意识其实是从民本思想那里派生出来的一个定义。“安民”“保民”“养民”“为民请命”等思想行为,在历代清官身上体现得都比较突出。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另一方面,清官还是官家对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唤,也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儒家思想中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孔夫子怀抱着“天下有道”“礼治”的社会理想,孟子也同样憧憬着“仁政”,他们都为自己心中的理想行走在路上。而后世清官作为儒家的信徒,也同样怀抱着这种理想。其实很多人在现实面前被撞得鼻青眼肿,甚至搭进去身家性命也依然九死不悔。
在官家政治结构中的权力信仰实际上是一出被清官话语遮蔽了的超级悲剧。
经济学中有个第二假定,被人称之为“资源稀缺假定”。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清官作为古代官场上的一种稀缺资源,当贪者越多,就越发显得其稀缺与无价。市场上越稀缺的东西,往往想得到的人就会越多,结果就会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包括皇帝老子也喜欢赶这种奇货可居的时髦。但作为稀缺资源拥有者的皇帝,他对这种稀缺资源的稀罕程度与老百姓的稀罕又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官家集团对清官的喜欢还是有限度的,有时候还不太感冒。韩非子的法术,就挠到了皇帝心灵深处的最痒处。术是什么?韩非子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在《定法》中,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在《难三》中,韩非子也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两层意思合二为一,“术”就是指皇帝驾驭官僚集团的秘密之术。群臣当然包括清官这种“稀缺性资源”,于是清官在皇帝那里往往会得到两种不同的下场。懂得鉴赏宝物的君主知道手里捧着的是宝,惜用之;而那些不懂的君主则会把宝物当做破铜烂铁扔在一边。你不是稀缺吗?那我就让你生锈贬值永远地失去市场。
现代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人有趋利性的一面。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在观察一个官员是否愿意选择当清官时,重要的是看他在选择时是如何做好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的。
施行恶政的古代官场就像鱼在吞吃大船,大船虽大,也架不住群鱼四下来攻,最后落得千疮百孔。如果一个官员想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迁,他就必须参与到这个贪腐集体中,否则,作为异己就无法存活于这条食物链中,因为他的上级和同僚会担心他有可能揭发。
而在权力的食物链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猎食方式。这就好比动物世界里,就算处于食肉动物最底层的鬣狗,也有吃腐肉的份。
我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发生在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7年),这应该是清朝建朝以来的头号贪污大案。其中涉案人员之广,级别差距之大都刷新了一项新的纪录。在这场贪污大案中,从封疆大吏到州县官员,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一场肃贪之风横扫过后,甘肃官场为之一空。如果总结甘肃贪污案,它的突出特点就是无官不贪,而且不是盲目的,是有组织、成系统、走程序的贪腐。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贪腐金字塔式的政治生态系统。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香港黑帮片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黑帮老大,把一把枪或者砍刀硬塞到一个人手里让他去干掉一个被打得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这个人一般是他的手下或者即将成为手下的,而且一定很正派。
这样做的目的想必大家都知道,你和我们一起杀了这个人,你就是同谋了,就是集团中的人了,就不用担心你出卖我们了。整个甘肃官场,这时候就产生了这种“齐黑”效应。想将自己抽身而出是不可能的。你不和大家一起玩,不遵循游戏规则,怎么能放心你啊?你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不上路不识时务,升迁啊提拔啊什么的只有靠边站。
要黑大家一起黑,在那样的生存环境里,谁都别指望做“白乌鸦”。这就是我在这里杜撰出的“齐黑”效应。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向朝廷谎报全省连年大旱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为,如果不是全体官员关上门来集体配合,玩了一出“齐黑”效应,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被揭穿的。要做到“齐黑”,那就必须要将每一个官员都拖下水变成共犯,很多时候,还要把好人硬生生地逼成坏人。
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
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相当于甘肃省省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在当时,甘肃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每年中央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用于地方购买粮食,以抚恤当地的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74年),政府规定:各州县存储米谷,大州县存一万石,中州县储八千石,小州县存六千石,全国统一标准。以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局部地区的粮食储备数额进行调整。像甘肃这样的穷省,因为老百姓没有其他收入,主要就靠两亩薄田维持自己的生计,如果遇上大灾之年,吃饭往往就成了大问题。朝廷令该省大州县存谷两万石,中州县一万六千石,小州县一万两千石。由于区域之间差异性较大,根据不同类型,又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80年),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可以通过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读书人通过考试,取得监生的资格才能做官。但是对于达官显贵、豪门巨富来说,通向官家大门的路径就不只这一条了。比如说他们可以用金钱买到监生的身份,这就叫“捐纳监生”。对于有钱人来说,拿钱捐纳监生,买个官家的VIP身份,还不是小菜一碟。
省内外商民跑到甘肃省的地盘上买来监生头衔后,他们并不要求能够进京入国子监去读什么书。对于买监生头衔的人来说,他们对读书并不感兴趣。获得监生头衔后,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很多富裕商民子弟进入官场的一条终南捷径。
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外商会跑到甘肃的地界来“捐纳监生”?主要是因为甘肃开捐的价格比其他地方低,每名监生只需要麦豆四五十石。当时一石二十八公斤,四五十石相当于一千四百公斤,按照今天的市价也就三千多元钱。
这种做法刚实施几年,就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经手的地方官借机大捞特捞,挪用捐监粮,有的嫌收取实物太麻烦,还要折收银两,干脆就直接收钱。不过时间长了,政府也就摸清了底数,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政府只好恢复拨钱购粮。
这时候,户部每年都要给甘肃拨银一百好几十万两用来采购粮食。可让乾隆皇帝奇怪的是,虽然自己每年都在批拨专款,可甘肃还是打报告上来,哭着喊着钱少粮多。虽然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哭,难免会让人生疑。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80年),陕甘总督勒尔锦打报告要求能够恢复捐监旧例,乾隆皇帝也同意了。但这一回,皇帝长了个心眼。他不能继续再当这个冤大头了,当长了,下面那些官员们评价自己会用四个字:钱多人傻。乾隆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副省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找自己信得过的人,办让自己信得过的事。
王亶望走马上任时,向乾隆皇帝拍着胸脯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话说得那个一个漂亮,可暗地里却另有一番勾当。乾隆这个冤大头当得实在是冤,自己挑的人,却在做忽悠自己的事。
为了捞取好处,王亶望和总督勒尔锦在私下里结成利益共同体。
他们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都不要再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王亶望和兰州知府(相当于省政府所在地的一把手)蒋全迪那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各地仓储都是底朝天,空对空。所以我们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实践证明,王亶望不愧是乾隆信赖的官员。在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吴思先生总结的“皇上也是冤大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大家都认清了皇帝的真面目。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当官。
既然想让皇上当这个冤大头,那就要好好地糊弄一把。一国之君又不是三岁毛孩子,要让他当这个冤大头,还是需要动动心思的。对于王亶望这样的官场老油条,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他很快就找到了让乾隆当冤大头的办法。
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同时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省长带头忽悠朝廷,也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毕竟上面的大帽子扣下来,有高一级的领导在那里顶着。
在这个案子中,地方各级官员几乎倾巢而出参与到这场权力分肥中,他们之所以敢如此置皇权国法于不顾,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权力监督机制的荒废有着很大的关系。努尔哈赤的子孙入关后,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恨不得将阻碍皇权强化的因素都清除干净。这样一来,科道官的监察权日渐削弱。
科道官在明朝时期又叫言官,他们由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组成。这些官员级别不高,若论品级,很多人只是七品的芝麻小官。别看级别小,可权力却不小,他们有权力监督正二品的尚书。这主要是因为科道官在官家权力系统中的设置相对独立。户部尚书级别够高了吧?可负责监督户部的户科给事中根本不用怕他,因为他与户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