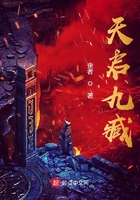残阳似血,斜照着一片大草原…草原的草已经衰败…渐渐的成了满眼黄沙…
沙漠中有零碎的干枯的荆棘树,被“呜呜”的风吹得往一个方向倒,呼啸的风似要将它连根拔起,然后,带走…
会被带去何方?模糊地在思想的人并没有得到答案…
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直到夕阳落进了地平线…风更加地放肆,呼嚎着卷过来…带起一片狂沙,似一张黄色的大大的幕布,扑头盖脸地罩上来。
人一下子进入了黑暗的世界,被一张布缠裹得紧紧的,透不过气…想呼救,又张不开嘴…
窒息感越来越强,心脏越来越被揪紧,疼痛…似乎被人捏着,即将爆裂…疼痛,绝望,似乎还有一些过往都袭上大脑…
“嗷呜…嗷呜…”两声狼嚎从天边而来,响彻旷野,窒息感陡然之间消失…
“呼…”
忽的一下,从床上坐起的赵影捂捂依旧“嘣嘣”的跳着,却还有疼痛感的心脏,定了定神,才发现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梦。
她将另一个多余的枕头掀开,又用手背擦擦额上,后颈的汗,摸摸背心,睡衣已经湿透。
她扭转身子,摸索着开关,摸着以后,扭一扭,昏黄的灯光瞬间照亮整个房间,整张大床。
起床换了睡衣,赵影看看时间,午夜2点46分。她又躺上床,关灯…闭上眼,脑子里却翻腾着梦里的场景。
为什么又会做这样的梦?
赵影又摸摸还心有余悸的胸口。想着,明天应该去看看医生!
她记得,这个梦景出现过好几回。到底预示着什么呢?
以前,听二姐说她梦见家里的房子往里面倒,结果,父亲就去世。还有一次,她说梦见家里的房子往外面倒,外婆去世。
赵影认为梦景的预兆是一件很玄幻的事情。她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
毕竟世间,有太多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
她经常做梦,多数醒来就了无痕迹。能够记得清楚的梦景,都会记下来,希望某一天,有用到的地方或者是得了奇特的解释。权当有趣的童话和神话听。
越想得多越睡不着…赵影又打开床头灯,手机不在卧室,就看看书吧。
有时,书可以催眠。
随手拿起《四书五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又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读完这一段,看注释,没读几行,觉得眼睛涩了。
正好,躺下继续睡觉。
睡着之前,赵影自我提醒,明天上医院看看医生。
逐渐进入睡眠的赵影又做起了梦。
夏天的夜晚,天空有一轮圆盘,还有滿天调皮着眨眼的星星。
她觉得她成了那轮月亮,有了明亮的眼睛,眼睛却满满都是焦急,急切地想阻止,却又无能地够不着,只能看着那即将发生的一幕幕场景。
她非常的想下去阻止,发现幻成了一片朦胧的光,似乎喊出了声也没用,她的声音融进了风里,被空旷的寂静的夜吸纳…她就只能像看电影一样的眼睁眼地看着…
一个从晚班车上下来的女孩子,身高大概162厘米,身材瘦削。
有一头掩住了后颈,还显得参差不齐的短发。
这短发是她自己修剪的前面,又麻烦二姐帮忙修剪了后面。
她斜肩背着书包,下车后急急地要走进女厕所。
“不要进去啊…”
不一会儿,三个高矮不一,胖瘦不一的男人抬着一个装东西的麻袋从厕所里出来。
车站已经没有什么人,剩下有一个腿脚不便,走路一边高一边低,跌着向前的矮个子男人问:“你们抬的啥子东西?”
一把有些心虚的男声:“嫩包谷棒子。”
一把恶狠狠的声音:“关你啥子事?死瘸子。”
问话的残疾人缩缩脖子,不敢再开腔。他想,又是这些二流子偷了别人的庄稼,现在玉米还不够熟,但也快熟了。用来推(磨)浆,做成玉米饼,甜得很。街上已经有卖的,城里人就好这个。
他虽然怕怕的,但也总是忍不住好奇心,跌地越发艰难,越发的慢,一直用余光瞟着他们抬着麻袋,走到路边的一架堆了许多玉米杆子的架车前,“碰”的一声,两人扬手将麻袋甩上架车,然后,一人拉,两人推的朝前走。
胶轮胎摩擦着地面,又磨着木头架子,大概木匠的手艺也不过关,架车一路“咕辘辘”的叫唤,很快地越过他,又转弯,响着,不知去向哪里。
眼睁睁看着的赵影知道,那个麻袋里装着的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她后天就要参加高考,明天还要在老师那里领准考证,熟悉一下考场。她耽误不起时间。
可麻袋里昏迷着的女孩并不知道她的焦急,还无知无觉地堆在那里,由一架一人拉着,两人各护一边推着的架架车前行。
麻袋被盖上了深青色的玉米杆子。人力架架车一震一震,又叽里咕噜的响,过去了不知多久,被人敲晕的女学生终于从疼痛中醒了过来。
她的嘴被一条烂毛巾堵着,毛巾有很大的异味,让她直犯恶心。
她微微地睁开眼,微微挣扎了一下,然后被人大力地拍了一下,拍在肋骨上,很痛。
她虚着眼睛,左右瞄一瞄,光线非常暗,感觉了一下,被装在麻袋里。粗糙的麻绳磨着她裸露在外的肌肤。
她挪了一下身子,从歪曲状态中伸直腰身,平躺下来,仔细地听着动静。
应该是在架车上,听喘气声,是一人在前拉,两人在后面推。看来,一共是三个年轻的男人施行的绑架。
她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一直小心谨慎的自己什么时候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
估计,可能是县城里的二流子。绑她无非是发现她的容貌,要想奸污她,应该不会要命。
她扭了扭,挣了挣手腕,借着透进来的昏暗光线看了看,发现双手被绑缚的并不专业,却是打的死结,不好挣脱开。
也好在他们不专业,并不懂得将人反绑。不然,恐怕她真的可能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任人鱼肉。
她不停地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千万不要慌,不要怕。架车一直咕噜前行,不知道要去到哪里,黑摸摸的,她也分辨不清方向。
估计都是往城外的郊区走,这个县本来就是属于丘陵地区,边界处也多有连绵的大山。他们用人力架车,多半是找个山林或者竹林之类的地方作案。
这个时节,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满山遍野都是玉米地,玉米林也是做案的地方。
如果他们选择在纯粹的山林会好些,容易跑,跑了也容易躲藏,而且也更容易找到工具,武器。
她听到了拉车的有些大声地问:“拉到哪里哟?好重哦!”
右侧的那人地喝斥他:“小点声。”然后又低声叽咕:“小心被人发现了。”
另一个在左侧的男人,似乎还是头子,低声却语气严厉地训斥两人道:“不要乱开腔。”
他又吩咐右侧的男人:“你去拉。走快一些。”
女孩子仰躺着,透过玉米叶的缝隙,麻袋的缝隙,感受到了月光。
天空白白的月亮,繁多的星星,都在静静地注视着人间的一切。
女学生听着车轱辘上了郊区的机耕路,机耕路是泥土辗成,震动感明显小了。
风声更大,虫鸣声更大,她一直静静地听着蛐蛐儿的叫声,风穿过玉米地的沙沙声,摇动树叶的哗哗声…
架车还在前进…不知道他们会拉她去哪里。不安的心更加不安…她又开始挣扎,但有麻袋的束缚,又被绑着双手,挣扎也是徒劳…
架车大概又行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停下。
麻袋上的玉米杆,玉米叶被人掀开。扎紧的麻袋口子也被人割开,月光一下子笼罩了她,星星也一闪一闪地落入眼帘。
她赶紧闭上眼睛,假装还陷入昏迷。然后,有人重重地拍她的脸:“醒过来…别装死…”
她睁开眼睛,没有表情地看着拍她脸的男人。大概被看得心虚,他虚张声势地厉声喝斥:“看什么看,滚下来。”
另一个男人走上来,拖着她的两只手,不管是否会伤到他,将她连同还裹在身上的麻袋一起粗鲁地拉下架车,翻滚进一边的玉米林。
当她停下了翻滚,一人上前拉掉了麻袋,缩在地上的她,顾不得被格楞碰撞到的疼痛,又挣扎着站起来,同时,被捆的双手抓握了点泥沙。
她几下子站住,站稳后开始打量四周。
这是一片玉米地,路对面也是一片玉米地,茂密的玉米林会遮挡视线。地里除了一行行高高的玉米,还有的就是已呈现旺盛生机的红苕,在脚下的小土堆上生长。
一人大力地推搡了一下,使走神的她差点朝前扑倒。
狠厉的声音响起,又被风吹散:“朝上面走,不要想着反抗,逃跑。你是逃不掉的。”
她时不时地被人推一把,朝坡地的上方走。
高高的密密的玉米杆子遮掩住了月光,只有漏出的暗淡的光线。努力地抬头,仰望,都不能看见月亮。
深一脚,浅一脚,被一人前面领着,一左一右的两人押着,就像被绑上刑场的红色人犯。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脑子里涌上了《红岩》的剧情,突然也有了悲壮的情绪和不怕死的无上勇气。
她在大脑里演练了一遍已经好久没有打过的拳,又过一遍叔叔和养父教导的对付坏人的招式。
终于走出了那一大片的玉米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块曾经用水泥碎石子碎瓦片之类混合打成的三合土大坝子。
她被人推着,押着,跟着三个男人围着坝子转了一圈。
大坝子的正前方是一片山岩,山岩大概五六百米高,上面应该是茂密幽深的树林,月光下,隐约可见的树影被风摇动,阴气森森。
山岩底部的石壁上开有几间石室,洞口大开,背着月光的石洞里面黑洞洞的,像凶兽张开的大口。
原来有的木门已经被拆掉,只有一些木屑散落在洞口。她估计大概是以前存放粮食的保管室。
大坝子的左右两边是一片已经腐朽的不堪的破房子。
右边的房顶已经被扒了,不高的墙体已经残缺,泥胚的墙也东垮一块西垮一块。
左边的更是朽的不堪,只剩下矮墩墩的一点旧时痕迹。生长了一些杂草,灌木,风吹来了空气中依旧还有的牲口的粪便气味。
这里应该是以前的晒场和牛棚。
“妈的…这里这么破,咋子行事。”
“就是…都长这么深的草了。不晓得草草头有蛇没有?”
“别吵。走,上右边看看。”
两个男人又推搡着女孩子走…进了右边…中间还有一间屋子像样点,大概地上打成了水泥地,没有长杂草,只是有了青苔。
“这里也不行,太脏了。滚一圈,身上的衣服都会洗不出来。”
“那去那个石洞里?可是里面黑黢黢的,你不怕有蛇啊?”
“哪个喊你穿着衣服滚,衣服脱下来放一边。”
“嘿嘿嘿…”猥亵的笑声,“是是是,老大。”
两个男人走远了些,又蹲下去了,不高的残埙挡住,看不见两人的身影。只听见他们低低的叽叽咕咕的谈话和嘿嘿嘿的猥琐的笑声。
矮小一些的男人邪笑着脱衣服,裤子,从皮带上解下一把匕首,在月光下挥一挥,又比划了几下。
“你乖乖地从了,老子可以放过你,不毁你的容,还带你去广东找大钱。广东那边,好找钱得很。
你长得这样子好看,不读大学也能发财。你说你这样子好看,干哈子想不开,要去勾引别个的心肝宝贝儿子。
不过,好在你遇上了我。哥可以让你吃香喝辣,穿漂亮衣服,有钱用。不过呢,你得乖乖的听话。过了今晚,你会晓得,好看的女人是可以舒舒服服的找钱的。
怎么样?叫声哥,跟着哥找大钱。”
她认真地注视着小个子男人,人长得斯斯文文,160厘米左右,穿着的确良的白衬衫,认不出是何种面料的青色裤子。
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
她认真地听着他说话,大概听出了些信息,又听见了他的问话,她用双手抬起,指指嘴上,示意他拿下堵嘴的毛巾,以及勒着的带子。
“你不要喊哦,不过,喊也是白喊,荒郊野岭的,离这儿远的很才…”
他只着一条四角内裤,晃悠到她面前,一手扬着匕首,一手用力捏着她的下巴,抬起来对着月光仔细地左右打量。
她忍着下巴被捏的疼痛,屈辱,控制着情绪。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捏着脸打量,审视了。那个可恶的养母在她小时候,就时不时地这样子对她,似乎想从她脸上找什么证据。
“真他妈神奇…你咋个长成这样子,真逗人。你今年多大?”
她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可怜兮兮的含泪抬眼看他,呜呜着想说话。
他揭开带子,拿下烂毛巾…
她含糊地喊了一声“哥哥”,趁他怔了一下的时候,扑进他的怀里,在他的双手搂上来时,抬膝重重的一顶,双掌一起贯胸,他倒下时匕首划破了她的背,她顾不得伤,双掌握着泥沙,跟着倒地的他扑去,将泥沙拍进他大睁的眼里。顺脚踢飞了他没掌握住的匕首进草丛。
他的呼痛声,呼伴声招进了两个同伙。
他们走到之前,她已经又抓起地上的碎砖头砸向他的眼鼻…又重重地跳起来踩了一脚他躬缩在地的身子,听着他的哎哟声,又整个人砸向他。
他闷哼一声,想滚开,动作不够利索,痛晕了过去。
她又弹跳起来,与已经回过神来的更高一些壮一些的人对峙。
互相凝神对峙了一阵,一个人转到她的后面,一个前面,企图进行夹攻。
她又喊了一声哥哥…然后,前扑后踢,打斗开始…
后来,只晕了一会儿的男人也爬了起来,丢了眼镜的他也没找到七首,三人只能凭肉身战斗。
当她终于体力不支倒地时…当她的衣服快被剥干净时,当她悲愤羞愤欲死时…
一声狼嚎“嗷嗷…”的响起,一头高大健壮的狼纵身扑向了敌人
“啊…”
敌人的惊叫声,痛叫声惊醒了她…也惊醒了陷入梦境的赵影…
“呼…”赵影蹭的一下,坐了起来…
拍拍胸口,安抚激烈跳动的心脏…
又梦见那气恨的场景。
过去三十几年了,已经好多年不曾想起…
她以为她已经忘了那个光怪陆离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