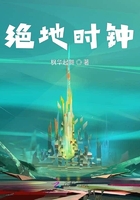定国侯这话已经问的足够明白了,薛继在一旁听得头皮发麻,他听见什么不好就非听这些东西,知道太多可不见得是好事儿啊。
秦胥没有做声,可他眼中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就要看你钓上钩之后打算如何处置了。”定国侯若有深意地说道。“毕竟,血浓于水。”
“如果不是血脉至亲,我也不必跑这一趟。”
定国侯拿着鱼竿走出了清波亭,踏过几层台阶,在湖边侧身坐下。“这种戏码老夫见得太多了。我不会苦口婆心说什么兄弟如手足,你们也不会听。”
话说到这儿,定国侯稍稍停顿了片刻,他回头看向紧跟着过来的秦胥,轻声笑说:“再者,分明是两个人的事儿,这话只对你一人说,不公平。”
“那您的意思是?”
“鱼无水不能栖,鹰无爪不如雉。”
四目相对,秦胥尚在沉思。
定国侯将鱼钩投入湖面,回过了头。“至于鱼能不能钓上来,这是垂钓者的能耐。你能有今日,必然不差这么点儿能耐。”
两人都不再出声,似乎是在专注钓鱼,可两人的目光都没有落在湖面上,一个看着天边,一个暗藏心事。
过了午时,日头最为毒辣,半个时辰里一阵风都没有,湖面风平浪静不起一丝波澜,边儿上垂柳也跟静止了似的,有气无力落在水面上。
“还不准备走?留着陪老夫用午膳啊?”
“您这么快就赶我走啊。”秦胥仍在原处不动,显然是没打算走。“您还没说……您觉得我这么做,对吗?”
“老夫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你对还是不对。反正是与非、成与败,能争一个已经足够了。二者兼得?你拿不起,拿得起也太累了。”
秦胥语气有些复杂:“那为何读书人还要读那么多圣贤之书。”
定国侯看了看他,竟是放下了鱼竿仰首大笑。
“那些圣贤之道,要是人人都能做到,还用得着读吗?”
这话听着别扭,是个歪理,却又挑不出错。
“那不也有先贤说过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生在这位子上,就只能干这勾当事儿。想置身事外,图个清静?也不是不行,那你打开始就该学我。”
秦胥颇为无奈道:“那是学不了。”
“行了行了,你这么大一团龙气在这儿压着,老夫能钓到鱼就奇了,没啥事儿赶紧走啊。”
虽没有明说,可谁都知道秦胥来江淮这么一趟就是为了见定国侯。
既然已经被定国侯下了逐客令,那江淮也没什么可待的了。
次日清晨,马车停在城外,秦胥挑开帘子看着远处一人一马,忍不住皱了眉头。“又奔北边去了?”
齐徽听得云里雾里:“您不是说去江南吗?怎么又改往北了?”
回想起昨日,定国侯说再晚来一日他就走了。
薛继明白了,远处往北去那身影显然就是定国侯秦傕。
“他藏得深。”秦胥自言自语道。
这老东西可没闲着,朝中多少大小事,只怕没有他不知道的吧。
——————
“薛老板又来江南了?”
“今儿还是跟沈老板一块来的,人家做大生意、大买卖。”
“前些年不都跟陈老板一起,怎么改沈老板了?”
“嗐,陈游今年都那个岁数了,哪儿还跑得动啊,他家又是独苗一个,比不得薛家风光!”
“可不,长子继承家业,幼子达官显贵,薛尧这俩儿子生的好啊。”
今儿夜里城中热闹,尤其号称江南第一酒楼的‘观江南’附近,那是灯火璀璨、热闹非凡,隔着三条街都能听见里边的丝竹声。
刚刚踏入大门的正是薛祁,一旁簇拥着各地商贾,其中不乏名声显赫的大人物,或是江南本地的世家公子。
谁不知道薛家小少爷薛继不久前当上了尚书令?不过三十五岁的年纪,官至二品,远远胜过当年的陈渝啊。
这一群人跟薛祁敬酒道贺,难免吹嘘几句。薛祁嘴上不言,心里多少是有些感慨。
酒过三巡,不知谁无意间问了一句:“薛老板,您今儿住东边啊?”
薛祁刚刚饮下杯中酒,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今儿住沈老板家的别院啊,谁说的住东边?”
那人也愣了:“今儿下午不是您的人到东边自家客栈说的,要两间房……还有个宁老板呢,嘶,怎么没见着宁老板?”
薛祁那点醉意顿时清醒了不少,脑子里迅速思考了一番,却始终没想起有这么一件事。抬头对上这人半醉半醒的目光,稍稍犹豫了片刻,随即笑着遮掩了过去:“嚯,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得,那今儿就不麻烦沈老板了。”
往后大半个时辰薛祁都心不在焉的,装着心事,这酒自然就喝不进去,待时候差不多了,即刻起身离席,连着道了几声对不住,自顾自离开了‘观江南’。
“去东边店里看看,怎么回事。”
这一声令下,车夫即刻往东边去,说远倒也不远,不过得绕过官府。等薛祁到了薛家经营的客栈外,已经过了戌时一刻有余。
店里伙计见着人还发懵呢,看见薛祁腰间的牌子就明白了。可就这一会儿,大惊失色:“你,你!他……”
薛祁示意他噤声,又板着脸问道:“人呢?”
伙计急忙在前引路,到了门前,正好能看见屋里亮着灯,隐约一个人影靠在桌边,手里还握着一卷书。
薛祁上前推门,那伙计明白事儿,即刻退下了。
门一开,里边人愣住了,外边人也愣住了。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两人异口同声道,又同时止住了声音。
里边的不是旁人,正是薛继。
薛继下午才到江南,进了城之后就照着老办法找到了自己家的客栈,轻车熟路报了薛祁的名号,这就住下了。他也没出去扫听扫听,那伙计是知道薛祁今日在江南,谁也没多想,谁也没多问,谁能想到就撞上了。
薛祁突然瞪大了眼,抄起一旁的扇子就打在薛继面前的桌上,随即用扇柄指着他,紧张问道:“你惹什么事儿了?官员私自离京可是重罪!你还,你还弃弟妹于不顾了?我怎么跟沈长青交代!”
“别别别,误会!”薛继顿时窜起来往后躲,抬起手臂下意识挡着他,心里是无奈之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照实说就暴露了,不说这又已经误会了。秦胥出来微服是舒坦了,怎么尽给他招事。
“兄长,你听我说,我不是私自离京,这是陛下准了的……”
薛祁仍是狐疑,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手里的扇子还没松开。“圣上准许?那就是办差?办差你不住驿站,偷偷摸摸报我名字干什么?”
薛继硬着头皮解释:“对外不能说是办差,反正就是只有陛下知道。你可别给我泄出去,泄出去我这就是罪过了。”
“当真?”
“当真。”
薛祁盯着他看了半天,到底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劲,这就放下了扇子,转身准备离开。
刚到门口,迎面走来一人。
“你这儿怎么了?”
两人一碰面,都愣住了。
来的正是秦胥。
“你同僚?还是——‘宁老板’?”薛祁回头看向薛继。
薛继此时真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躲,可偏偏两个人都在这儿,他无处可躲。
秦胥打眼看了看面前的人,从面相就能看出与薛继有七分相似,心里盘算一番也猜到了。
“薛老板?久仰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