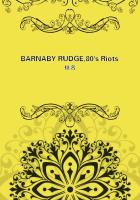他不曾想到,他在这镇中学的一年,竟然视那鄙陋的冲凉房为胜地,他的疗病密室。
夜晚,他双眼熠熠,整夜整夜地与细菌精灵战斗,让他害上了失眠症,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过,他并不孤单,整一个宿舍的人差不多都跟他一样,在轧着床板,咯吱咯吱响,抓着痒呢。
白天,他强打精神,听着课,可还是控制不了哈欠连连。傍晚上自修前,如同朝圣般,他打了一桶水,准时去到冲凉间。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他还是控制不了对自己身体的鄙夷之情,每每在他开始脱衣服的时候都不忍瞧上一眼。
那些创口和患处,只要一沾上水,就跟被火烫着一样,痛得凄厉。他挥动着毛巾,仿佛火上浇油似的把水泼到身子上,让身上的痛感神经如蜘蛛吐丝一般缠绕全身,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
尔后,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这可恶的细菌精灵了。起初,他的药品只有酒精,还是向同学病友借的。他没有棉球,只得用手指或手掌抹上酒精去擦。这回可不像是火烫了,简直就跟放上去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似的,要将肌肉撕裂开来的疼痛,几乎使他蹦了好几尺高,好比脚上踩着钉子的猴子。
每一次酒精浴式的治疗,都让他痛得跟脱胎换骨似的。可那细菌精灵依旧岿然不动,他不得不狠下心买来了药膏。那一小管猪油似的药膏,足可抵他几天的伙食费了。他往身上涂抹的时候,还心痛一阵子。
他用掌心使劲在肌肤上揉搓起来,让那一小摊奶白色在力量与热度的作用下,慢慢消失,如一缕青烟,化为乌有。他满心希望乳膏不亚于一剂毒药,渗入皮肤之后,就如一阵毒雾,随风而至,细菌精灵闻之则倒,纷纷死绝。不过他的希望落空,用药两个星期之后,仍是不见效。
那时市面上新出了一种听说有奇效的皮肤良药,叫皮康霜的,价钱却贵得很——够他一个星期的伙食了。宿舍里就有一个买了这药的,起先还看不出大家的羡慕之情,待他发觉了,立刻神气活现得像一只骄傲的公鸡,仿佛举在手上的不是拿来治疗的药物,而是上天赐给的仙丹白露,抹一点就可羽化成仙似的。
那个家伙从此以后把全宿舍里的人都当成贼了,俨然一副小心防备的架式,那支药膏东藏藏,西掖掖,成天不安心的样子。他猜那个家伙当时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赶快把病治好,而是热衷于跟大家捉迷藏了。因为明摆着的事实是,那个家伙的皮肤病仅仅是比大家的一年时间提早了一个月痊愈而已。
他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身体让他吃尽了苦头,他也尝试着不给身体好果子吃。
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他从小就懂得事理,到这镇里的学校上学,学费还有伙食费,对家里已成了一笔不小的负担。家里每个星期给3元钱,他就决意要省下1元钱。
学校里的饭是自己带的米,装在饭盒里放进大蒸锅蒸的。他一顿饭只放进去两把米,一个星期下来,他还省下半袋子的米。
他都能记得那时父母硬是将两块钱放进他衣袋里,千叮咛万嘱咐,劝他千万不要省着用,不要心痛钱,要买菜吃,要吃饱饭,别糟蹋了身子。爸妈给得就不多——他都能记得,每每末了,母亲说完这句话之后,总会撩起衣角揩眼泪。
那年头去镇上的路还是土路,走路要一个多钟头。他从家里出来,肩上挎着书包,手上提着米袋子,瘦弱的身躯由于负重,走起来还有点摇摇晃晃的。
他走出村口,上了公路,绕过小道,过一条小河,穿过好几个村子,爬过了一个高高的土坡,为了抄近路,他还绕上了田埂,经过了一片广阔的田野,然后他又走上了公路,拐了一个弯后,他就可以望见学校那井井有条但显得疲惫不堪的房子了。
五天后,他一样肩上挎着书包,手上提着半袋子的米,又沿着这条路,行了将近一个多钟头,当他穿过小道,走上进村的公路,他就可以瞧见村子里家家户户茅草房顶上升起的缕缕炊烟。在饭桌前,他同样地将省下来的1元钱交给了母亲。
一个星期只花2元钱,他吃的是什么呀。
他清楚记得,那时一等到开饭时间,从老师住的四方院宿舍里,从附近村庄如蚯蚓一样的红土小道上,走过来一群差不多模样的妇女,挑着担子,脚步轻快,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如同赶集一般,云集在学生宿舍门前的土场上,打开担子两端箩筐的盖子,里面盛着好几大盆的菜,屁股还未及坐上自带的小板凳,就扯开嗓门吆喝,新鲜出锅的私家菜就可开卖了。
那时候,因为学校没有完备的食堂,只有一个大伙房,不过是负责把学生的饭蒸熟而已。而菜就靠这学校里老师的家属以及周边村子里的农妇了,她们是最初从事私营饮食业的开拓者,她们或利用自家出产的蔬菜,或到集市上买来鱼肉,一般每家炒四五种菜,一次可够卖出几十人份,收入可观,一不小心就走上了服务业改革开放的创新之路。
那个时候,学校的管理者或因财力上捉襟见肘,或因心无旁骛,一心只想着抓好教育,没有大包大揽的,没想着什么事都握在手上,没有把食堂办全了,不期然地就孕育出了最早的一批创业者。这些家庭妇女、村妇,在自家的几尺厨房之内,翻动几下炒锅,挥动几下锅勺,非但能增加家庭的收入,走上致富之路,还开一时风气之先。
几年以后,当他在县城读高中,到大城市上大学时,学校食堂的经营权已成了一个香饽饽,学校的管理者这时候真不想包揽一切了,也不想细水长流式的经营了,学起了从外面舶来的所谓经营权外包、业务外派,还美其名曰“抓大放小”,“一心一意抓教育”,甩了包袱,顺了潮流,还得到好处,真是美不可言。
围绕着这食堂的经营权,各方神仙各显神通,厮杀争夺,好一番热闹。他上高中那年,他班上一个历史老师“三生有幸”——这是他老师的话——拍到了学校食堂的经营权,脸上像涂了猪油一般,整一个月都红光满面的,他那时还纳闷了好一阵子,一个老师能乐成这样子,居然是因为他从教学领域之外得到的东西。作为老师,难道他最大的快乐不是他在教学上得到什么荣誉吗?
——可那些妇女做的是什么菜!韭菜呀青菜呀什么的,通通是用清水煮,末了出锅时,才浇上几滴油,油还没完全化开,就成几朵油花漂浮在汤水上面,卖的时候,用勺子搅拌几下,那油花就像观世音菩萨手上挥动着柳枝洒向人世间的仙露一般,纷纷到处施恩,让那些素净得如同修女的菜枝、菜叶沾上一点珍贵的油腥。
唯独咸萝卜干、用田蟹腌制的蟹酱,还有煮鸡蛋才是原汁原味的,没有偷工减料,因为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食物,大伙在家里也常吃。
他记得最清楚,大伙最喜欢吃,也最不舍得买的,是红烧猪肉,以及同猪肉一起炒的那些菜。那年头,猪肉可是顶金贵的。
农家人养一口猪,跟侍候一个人似的,也跟开着一个银行似的,当存钱,操着心呢,有的农妇,竟然还让猪睡到她的床底下,喂猪唤猪,就像叫唤自己的孩子一样。
食料又是天然的,无非就是薯叶子、谷糠、豆粕或是剩饭剩菜,猪也娇惯,不见长,慢慢起膘,通常都要两年才出栏。那肉,红烧、白灼、煮汤,真叫香的,香飘十家八户的。
他在家里,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那时村上有一家食品站,一天限量宰一头猪,供应附近的十多条村子。村里能吃上肉的人,手上提着买来的肉,甩得老高,从村前的小市场一路慢悠悠地踱回家去,一路上不停地跟人打招呼,还把肉伸到人家的鼻子前——啧啧,瞧这肉,鲜着呢——仿佛担心别人看不见似的。
不过,他在学校精打细算,犹如账房先生打着算盘计算着每天的伙食标准,一个月下来他就能至少吃上一次肉。
在那一月一度的饕餮之前,他吃的是什么呢?一顿菜钱必须控制在1毛钱5分钱之内,早餐顶多只能用5分钱,一天的费用顶多不超过3毛5分,到了星期四,共四天,最多花去1元4毛钱,虽则这是最大的预算,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状况,通常他会在每天省下5分钱,这样到了星期五的上午,一个星期在校内的最后一顿饭,他在2元钱的预算之内还有余钱可对付。
下午下了课,他就收拾行装回家,饭在家里吃了。如此算下来,他总能达成一个星期花2块钱,省下1块钱的打算。
他就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统帅,对遥远的一个月之后的每一分钱如同调度麾下的每一个兵士一样了然于胸。他指挥着这些兵士,今天出动多少,明天派出几个,大旗所指,毫不拖泥带水。
他调动着这支未来之军,去攻克一个个阻挠他清纯意志的贪婪、贪吃和自私的堡垒,用最少的兵力达到最准确的打击。他可以用5分钱买一份“油花”韭菜,3分钱买一勺子的蟹酱,将就一餐。他能做到只需一个8分钱的煮鸡蛋,外加几番讨价还价达成2分钱半份的“油花”青菜,就可以将半饭盒的白米饭送下肚子去。
他就好比一个爱兵如子的将帅,不轻易牺牲手下的每一个士兵,而每一个兵士一旦被派出去都能出色地完成他的战术任务。如此,在毫厘不爽的一个月后,他的手上就握有一支精干的突击队,这支突击队由30个分钱组成,也就是“3毛钱”的兵,足以去攻破一座无比坚固的由食欲、本能及卑微构筑而成的堡垒。
到了那一天,他就像过节一般,那种仪式感、豁出一切的决然,让他的内心庄重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手握着那足足由30张1分钱的纸币组成的3毛钱,犹如抱着有3吨当量的炸药包.
随着放学的铃声响起,好像等待冲锋的战士听到了号令,他比往常更为敏捷地从堆得如满地的萝卜一样的饭盒中找到了自己的饭盒,打开来,混和着蒸汽的米饭香味比往日更加沁人心脾。
在这一时刻,他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想象过无数次的景象:一片约有5厘米长,3厘米宽的红烧猪肉从妇女的勺子中倒出,滑落到他的饭盒里,尽管那肉片薄得状若一张他从学校的杂货店买来的信纸,但在他的眼里,却胜似他刚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的那薄如蝉翼、号称千古奇珍的金玉缕衣。
最为吸引人的是,追随着那肉片一起降临的肉汁,金黄,红中带紫,流金溢彩,像一团燃烧的火,又仿佛老天赐给的琼浆玉露,浇洒在那雪白米粒之上。此刻,他口舌生津,满嘴口水,饥肠辘辘,眼神发紧,迫不及待地朝那些妇女走去,活像要将她们生吞活剥了似的。
菜吃得差也罢了,连饭他也只是吃个半饱。他的饭盒是全宿舍里最小的,淘米蒸饭,也是敷衍似的抓了三把,又放回去一把。他那份俭朴之心,就好比民间传说中的那位巧媳妇,每次做饭都会抓起一把米省存下来。
饭蒸熟了,只到半个饭盒。刚开初,他也饿得慌,那半盒子的饭,他也是扒拨几下就光底了。
宿舍里有一个家伙,嘴唇厚得犹如猩猩,大脚板,每次蒸饭都是一大饭盒的,但吃起来比他还快,简直就跟直接倒进胃里去一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非常鄙夷地瞅着他的饭盒,瞅着他,仿佛从来没见过的稀奇古怪。
他饿,他也想吃得饱饱的,但他又天真而偏执地认为,多吃就是一种罪过,他那时就已经在幼小的内心里自觉地践行起了孝悌之道,渐渐地往其中注入殉难的精神,让受苦受难变为成长中的一个过程、一个必需。既然绕不过去苦难,不如就制造些苦难来尝试尝试。
他宛若圣教徒一般不管不顾地对身体自虐,胃液、胃粘膜成了他的帮凶,它们在消化完了那可怜巴巴的一小堆食物之后,淫威未歇,在空荡荡的胃袋里继续为非作歹,胃液翻腾,倒海翻江,胃粘膜犹如害了严重的哮喘,大张旗鼓地收缩伸张,一种俨如虚脱般的饥饿痛感就弥漫全身,他的口里就泛出一股酸楚而又阴凉的唾液。
这痛楚却给他创造了一种无以伦比的愉悦。他像测量师一样精确地实施他的“两把米”试验,不给受虐的身体丝毫的乞饶机会。渐渐地,饥饿感就不像初时那样清晰粗砺了,它变得迟纯怕生,就像羞涩的小姑娘,不敢见人了。
在某一天,约莫在学期第三个月的一天,他吃完了那半饭盒的饭后,居然产生了饱满的感觉,在那一瞬间,他知道他赢了,他获得了苦难历程上的头一个胜利。
宿舍里的那个大胃王,对他的吃饭情状仔细端详几日之后,就曾经对他下过这样的评语:这家伙是把自己当鸟儿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