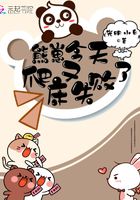她正端着茶杯给她的孩子喝水。对于我的询问,她很不耐烦。用手指指:“上面!上面!”上面有很多层楼啊?我把情况说明,想让她明确地给我指引一下。她就不再说话,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我出去。后来,在另一间办公室,另一位老师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儿子班主任办公室的位置,在那里我接回了正生病,等着我去接的儿子。
我也曾遭遇过无数的冷遇。可是在那种情形之下,那位老师的冷漠,确实让我心寒。她不理解一位家长对生病的孩子的关切和焦灼?其实,多说一句话或者把一句话说清楚也就够了。当然,她可能有她厌烦的理由。
可是,那一瞬间,给我这个陌生人的脑海里永久地留下了这样的情景———她在给她的孩子喝水,厌烦、不屑的表情像一层霜冻在冷漠中凝固。
我同样记住了另一个瞬间。去银行取工资,柜台前挤满了人。没轮到自己时,大家都事先把取款单填好,而圆珠笔只有一支。我向身边一位已经填好单子的少妇借笔用一下。她很反感地对我说:“笔是我自己带的,又不是银行的,凭什么给你用?”我一下子愣住了。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婉拒足矣,何至于这样呢?她把笔放在包里,走了。其实,给别人用一下笔,能耽搁多长时间?有多大损失?
旁边的一位女孩递给我一支笔,而她的单据还在空着,我说:“你填好后给我用吧!”她不以为然地笑了:“这么个小事情!谁先填不都一样吗?”或许,对她这只是个不经意的瞬间,而我却记住了那个阳光下午的瞬间———女孩很好看的笑容和温暖的手指。
其实,两种感觉只是一瞬间,可是我宁愿留住那点指尖上的余温,以抵御人情的冰凉,进而说服自己。
几天前,我大姐在电话里惊慌失措,说出大事了。大姐一向很沉着,可是发生的事,让她没法冷静。
那天,她在银行办银行卡,办好卡,一转身,柜台上的手提袋丢了一只。一只袋里装着十万元现金,没丢。丢的那只里面装的比现金更重要——是我外甥下半年出国的相关手续。当即,大姐汗出如浆。
打电话时,大姐恨得咬牙切齿,他怎么就不偷走十万元现金,偏偏偷走那个袋子呢?
这确实是天大的麻烦。对出国的手续,我不太清楚,但可以想象,像签证之类的资料,应该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补办到的。除了让大姐赶紧报案之外,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外甥是品学兼优的好青年,下半年就要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本来顺风顺水,突兀起了这么大的变故。这事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刚才,我大姐打电话来说那只手提袋找到了。就在昨天,银行保安发现银行旁边的变压器上放了一只手提袋,打开手提袋,保安发现了一张名片,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保安找到了我姐。
这件事中,很有意味的是这位小偷。笑纳了手提袋里的几百元钱,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为了还回手提袋,他还颇费了一番心事。手提袋如果重新放在银行的柜台上,可能会被另一个人拎走。他选择把它放置在银行旁边一人多高的变压器上,行人无法看见,即便看见了也无人敢取,但银行的地理位置很高,站在台阶的保安一眼就能看见。
除了袋里的五百元钱,其它资料,一应俱全。面临最坏的结局,最终却找到了最好的答案。大姐欣喜若狂,说了半天小偷的好话。最后,我老姐十分肯定,这人干这行肯定是另有隐情,因为他在作恶时没有完全放弃善,否则他把手提袋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对他来说更省事,更少麻烦。
我心里有异样的感受。于是直截了当地问,老姐是不是对小偷还心存感激?大姐沉默了片晌,按理说应该恨他才对,可是,对这样的结局,心里确实充满了感激,这是一种不好用语言来表述的感激。
是的,这是一种很另类的感激。感激的当然不是小偷梁上君子的勾当,而是在犯错的同时,并没有泯灭良知。千错万错,良知尚存。我们都不是圣贤,有意无意,在世间也难免犯下这样或那样的过错,甚至罪孽。心中永存一份良知,做事就有了底线。这是自我救赎和获取他人原宥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对眼前这位黑胖的汉子着实感到奇怪。
这是位外地人,操浓重的外地口音。租了小区的一间车库,开着糖烟酒类的杂货店。平日里殷勤待客,但在他吃午餐时,想让他离席买点东西,他总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一餐饭也吃不好,你就不能等一会儿啊?”
他就这样常常对我抱怨,让我十分不快。其实,附近不远处就有一家超市。我是看他一个外地人来此地谋生不易,有意照顾他的生意。不过,撇开午餐时光,他还是很殷勤的。
在我印象里,这家人对待午餐很隆重。十点左右,这汉子就在小店门前的煤炉上支起小锅,小锅里喷起浓烈的油烟,烧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然后扯起店门前的宽大的帆布蓬,摆上方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一杯寻常的啤酒,被这汉子喝得惊天动地。他眼睛贪婪地看着杯子,猛一灌,杯子重重放在桌上,张大嘴,嘴角下撇,发出“呃”的一声,显然是陶醉了。我从来没看一个人喝啤酒有这么夸张。
我让他给我送一箱啤酒。他说,你回家等着,马上就去。这天我家来了客人。我听信了他的话,可餐桌上的菜都上全了,还是等不到他的啤酒。再次去他的小店,他正喝得快活,可是我不快活,我得说了。
我说,你这人真是,你怎么把你的午餐看得那么神圣,老主顾的生意怎么就抵不上你一杯啤酒?说完,我就转身回家。
一会儿,他扛着啤酒,敲门进来了,一进门就向我道歉。
他说,我确实把午餐看得很神圣,我妻子在外做钟点工,累了一个上午,赶回家吃午餐;我老娘从康复中心,走三条大街过六个小巷,赶回家吃午餐;我女儿在城郊的一个企业打工,要骑近十五里路的自行车,赶回家吃午餐;我儿子背着十多斤重的书包,赶回家吃午餐。吃完午餐,一家人又像潮水一样散去,各忙各的,你看我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午餐对有些家庭来说,是神圣的。在各自的时间里忙碌,只有午餐以午餐的名义,把全家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坐着。
现在,我不再去打扰他的午餐。有时碰上了,看见这汉子夸张地喝啤酒,我装着路过。一家人面对面坐着,我没法替他找到另一种欣慰,替代他眼前的情景。
晚饭后,我习惯将一袋垃圾放到门外。第二天早晨上班时,顺手拎走。搬入新楼不久,发现围绕门外的一袋垃圾发生的事,颇为蹊跷。正常情况是,一袋垃圾靠在门外等我到天明,可有时候垃圾竟会被人拎走,这就让我感到有些奇怪。
渐渐地,隐约窥探到其中的秘密,这一事好像与另一物产生了联系:在垃圾袋放入可乐瓶,垃圾就会消失;相反,垃圾则存在。于是断定,垃圾袋的消失,应该跟可乐瓶有关吧?
后来发生的事,证实了我的判断。
暑假,为带儿子晨练,我起得很早。绕城小跑半圈回家,天才刚刚放亮。楼梯爬到三楼,遇上了一位拎垃圾袋的中年汉子。他的左手掐住一只可乐瓶的瓶颈,右手拎着我很眼熟的垃圾袋。
见了我,表情突然有些尴尬,估计他认出了我。擦肩而过时,开口跟我说话。他说,可乐瓶放在垃圾袋,我想,你们是不要的,我拿了,顺便把垃圾拎下去,不知,不知你是否介意。我连忙说,谢你都来不及啊!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这位中年汉子,我也眼熟。常常来小区收点破烂,掏些垃圾。其身份不言而喻,表情中,带着在生活底层挣扎的匆忙和焦虑。
他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值一毛钱的可乐瓶,即便装在垃圾袋中,也不能白拿,要拿,也得付出价值对等的劳动,用拎走垃圾来作为回报。
同样是可乐瓶,在我的印象中,这汉子是有所取有所不取。上次,我听他收破烂的吆喝声,打开门。“这儿有几个可乐瓶,拿去吧!”我跟他说。他扫了一眼,目无表情,向上走。当时以为他迟钝,我大声喊,他连头也不回,继续向上走。事后想想,或许是因为我态度轻慢,或许是他不愿受嗟来之食。不付出,他就不愿有所取,他是不想占几个可乐瓶的便宜。
有段时间,我常看到一些言论。什么贫穷是一种病啦,什么穷人缺什么啦,这些论者板着面孔,像严厉的老师,用教鞭边敲边指“穷人的缺点”。其实,他们所说的缺点,是人性普遍的弱点,只是被有意放置到穷人的身上,大加渲染而已。
不要看低了穷人,或许他们的品质是我们人生的课堂。当某些大鳄毫无愧疚地大肆侵吞社会财富时,一位穷人却不愿意平白无故占有一只可乐瓶。将欲取之,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劳动代价。
大婶指着我的脸,又指指一只最大的、白里透红的苹果说,瞧你的气色多好,跟这苹果没什么两样。大婶很风趣,我知道她在恭维我,可是听了这话,纵然我的面皮如松树皮般粗糙,心头也难免一喜。这是大婶促销的手段,我不买她的水果就有点不好意思啦。
水果摊摆在进菜市场的入口处,长年累月,大婶在此处坐如磐石。她告诉我,她家就在附近的郊区农村,儿子读大学,丈夫病歪歪的,做不了什么事。见了面,她就说,我儿子毕业就好了,像你一样成为“国家人”就好了,我就不用在这里日晒雨淋卖水果了。我心生同情,打趣说,您儿子将成国家栋梁,到时候你就专门给儿子买水果啦!我把“买”字说得很重,大婶的老脸乐得像一个红富士。
可是,后来的发生的事,让我觉得大婶远非我想象的简单。一次,我看她用塑料袋装了一袋苹果硬是塞给城管。还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表情是谄媚的。我见了很自卑,连卖水果的大婶都比我城府深,我总把所有人都想象得很单纯,其实单纯的正是我自己。
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我买菜回来。路过大婶的摊位,正好遇上她与一位买菜的农妇发生争执。嗓门很大,模样凶狠,与日常和善乐呵的大婶判若两人。两位都是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我走过去,心里有些难过,想到了当年阿Q与小D、王胡的那场“战争”。
从此,我不再去买水果了。一天,大婶叫住了我,夸我长得气派穿得体面。我直截了当,我不再买您的水果了,您对那位卖菜的那么凶
大婶很长时间地沉默。很委屈地说,你不买我水果不要紧,话得说。她说,孩子,我没做生意在农村的时候,你去四里八乡打听打听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心善得连蚂蚁都怕踩死,现在你让我怎么办?像你这样苹果香蕉一买就是十斤,这样的主顾我得奉承着;像城管那样狠的,一脚就能将水果摊掀翻的,我得巴结着;像卖菜的那样和我争地方的,我不凶狠,生意就没法做,我也知道她是苦人也心疼啊
我无话可说。
生活是一双无形之手,威力无边,而人生像一块泥巴。这双手不停地揉捏着泥巴,终究会捏出一个人生存环境所要求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