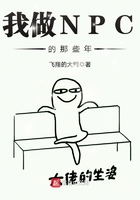第十五章至第三十一章
从小凯蒂的过早降世,到凯瑟琳的黯然安息;从小林顿的不幸落地,到伊莎贝拉的凄然身故;从小凯蒂和小林顿的被迫成婚,到辛德雷和埃德加以及小林顿的相继殒命,遭受自然考验的呼啸山庄和享受文化熏陶的画眉田庄为观众上演着一幕幕生死大戏。在这里,人类充满着争夺和竞争,善恶界限已不分明。这十七章在多层次、多视角的变换中不断透视着人物内心世界及其命运,前后互相照应,相互补充,一环扣一环,直至将全部疑惑稀释殆尽。
第十五章
《呼啸山庄》第二卷开始,时间为1784年3月。叙述者丁耐莉继续着她对洛克伍德的故事。本章主要讲述了凯瑟琳死前的最后日子以及她和希斯克利夫的爱情绝唱。这是很重要的一章。如果说第三章中洛克伍德的梦魇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为残忍的场面,那么本章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诀别就是“英文小说中最感人的爱情场面之一,然而丝毫没有俗套的浪漫和感伤成分”。这是本书的又一高潮之处。
凯瑟琳虽然得到了埃德加的尽心呵护,得到了医生的全力医治,但她“那双眼睛给人的印象不是在看她周围的东西,而是凝视着远方,很远的地方——你会说是这个世界之外的什么地方”(203)。这里女作家艾米莉借叙述者丁耐莉的双眼向读者暗示,凯瑟琳距离坟墓只有半步之遥,这也证明丁耐莉的推测是正确的:“我认为——都不是明显康复的证据,相反却标明她注定不久就要香消玉殒了。”(203)丁耐莉回到画眉田庄的第四天,那天是星期天,全家人都去了教堂,她才能有机会把希斯克利夫的信转交给凯瑟琳。凯瑟琳还没有反应过来,希斯克利夫就直闯进来。对希斯克利夫而言,凯瑟琳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灵魂,须臾不可离分。这样,凯瑟琳脆弱的前期康复一下子就被希斯克利夫的侵入打得粉碎。这种感情的大爆发简直可以说是残忍的、非人性的。希斯克利夫紧紧地把凯瑟琳搂在怀里,有五分钟左右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紧紧搂住她不放。他一眼就看出凯瑟琳“已命中注定,要死了”(205)。他跪在她脚下悲绝地叫喊:“噢,凯蒂!噢,我的生命!我怎么能承受得了。”(205)所有的爱情宣言,在这十几个字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早已相互视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本真状态。“因为他和她一样是风暴的孩子,这使他们之间有一条交织在他们生命的本质之中的纽带。”希斯克利夫直瞪瞪地看着凯瑟琳,眼睛里燃烧着痛苦的火焰,却没有泪水。他想站起来。在前几章里,女作家给我们展示的是女主人公在埃德加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模棱两可之情,而在本章,女作家终于让凯瑟琳无所保留地倾吐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凯瑟琳心酸地说:“我但愿我能抓住你,直到我们都死的那一天!……我才受罪呢!你会忘记我吗?……”(206)凯瑟琳十分清楚,由于嫁给了埃德加,离开了荒原,她已丧失了自己的精神乐园,过着灵肉分离的生活。一失足成千古恨,今生今世她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乐园与自己心爱的人结为一体了。也许只有死后自由的灵魂才能重返故里并最终与心爱的人在属于两人的天堂相伴。“凯瑟琳死亡的动力源于两个主要的愿望:想和希斯克利夫融合,想返回到童年的纯真状态。”小说最后情节的发展也正是遵循了这一结局。此刻希斯克利夫把头挣脱出来嚷道:“别把我折磨得像你一样疯狂……你想过没有,所有这些字都将像烙印般印在我的记忆里,在你离开我之后会永远在我心里越咬越深……你知道,只要我活一天,就不会忘记你!当你得到安息的时候,我将正在地狱里受着煎熬痛苦得直打滚……”(207)对于他们的爱情,希斯克利夫抱有这样的信念:穷困也罢,堕落也罢,死亡也罢,无论是来自上帝还是撒旦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把他们分开,可是,由于凯瑟琳的失误,两人只能暂时分开。再见的时候,欢喜、怨恨和悲伤,一齐涌上心头。同样凯瑟琳也呻吟道:“我不会得到安息的。”(207)她伸出手钩住希斯克利夫的脖子,让他托住身子,把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脸上,他以疯狂的爱抚回报她。他狂野地说:“你现在使我明白了,你是多么的残酷——残酷而虚假。你为什么瞧不起我?为什么你要背叛自己的心……你自己杀死了自己……你过去爱过我——那么你有什么权力离开我?……上帝或者撒旦所能施与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将我们拆开,而你,出于自己的意愿,把我们拆开了。我并没有揉碎你的心——你揉碎了自己的心,而你在揉碎自己心的同时,把我的心也揉碎了。我身体强壮,这对我来说就更糟糕。我想活下去吗?……你的灵魂在坟墓里,而你还愿意活在这个世上吗?”(209-210)希斯克利夫这段发泄式的话,明显的有对凯瑟琳背叛自己的谴责。但对于临死前的凯瑟琳而言,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是谴责实则包含着对凯瑟琳无限的深情、无限的爱。因此凯瑟琳抽泣着说:“别逼我吧,如果我做错了事,我正为自己做错的事而死去。”(210)这里凯瑟琳仅因出于良好的动机背叛希斯克利夫而嫁给埃德加一事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他俩相爱之深。他们的脸贴在一起,他们的泪水冲洗着对方的脸。希斯克利夫这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流泪了,他看着凯瑟琳的眼睛,摸着她一双消瘦的手说:“再吻我,别让我看见你的眼睛!你对我做的一切,我都可以宽恕。我爱谋杀我的人——但谋杀你的人呢!我怎么能宽恕他们?”(210)他们俩紧紧挨在一起而不管埃德加已经来了,直到凯瑟琳的手无力滑落。这一幕被阿诺德·凯特尔称为“这是一切文学作品里最粗暴的章节之一,但它也是最感人的。因为这种粗暴不是神经病式的,不是虐待狂的,也不是罗曼蒂克的”。这一场情人的生死离别写得何等惊心动魄。他们的爱情仿佛和仇恨一样一点也不温柔,两人有的只是在互相咬牙切齿、互相愤怒中的撕扯。这样的激情——粗犷、野性,带着荒原的气质,它没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绵,有的只是“大江东去”的魄力。它如狂风吹过你的心灵,永远刻骨铭心的是它的不可抗拒和无所阻挡。对于他们,人们不妨借用约翰·兰索姆描写地狱里情侣的一句诗来形容:“恍恍惚惚,他们在亲吻时互相愤怒地撕咬。”他们的关系早已突破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爱情,而深入到了存在的层面,或者说,两人成为相互之间存在的人格化和外化,成为相互存在的象征物和主体投射。正如英国当代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ngham,1874—1965)介绍《呼啸山庄》时说过:“我想不出另外还有哪本书,把爱情的痛苦、欢乐和残酷无情表现得如此强有力。”
病重的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匆匆会面的情景,充分说明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远非小情小爱,而是不可离分的灵魂之爱。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这刻骨铭心的爱、相互哀诉和谴责,给予了凯瑟琳最后致命的一击,终于夺取了凯瑟琳的性命。在他们的对话中,希斯克利夫深信凯瑟琳将永远萦绕在他的心际,而凯瑟琳则怀疑二十年后,希斯克利夫会把她忘掉。这点呼应了第三章在洛克伍德的梦魇里,凯瑟琳的鬼魂的哭喊声:“让我进去!……二十年来我一直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29)
第十六章
1784年3月20日,也就是在上章提到的当天午夜,女主人公凯瑟琳生下了一个仅仅七个月的女婴,“她出生后才两小时,她的母亲就死去了”(214)。在某种程度上,凯瑟琳的死亡是一种幸福,她终于摆脱了尘世带给她的情感纠缠,她现在所需要的是荒原的新鲜空气,她早已厌倦被困在几乎令人窒息的画眉田庄里,死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救赎和幸福,因为死可以让她重获自由,有机会和爱人的灵魂合二为一,在自由的荒原上漫游。埃德加给她的所谓的天堂并不是她真正想要的家,她情愿自己被扔在呼啸山庄的草原中间,即使是死她也不愿与教堂屋檐下的林顿家族为伍,而宁愿在露天竖一块墓碑。“那一片儿的围墙很低,荒野上的荆棘、覆盆子树爬过墙来了,泥煤土丘几乎要把它淹没了。”(220)“这的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好像是给她的灵魂开了一个方便之门,让它逃逸到过去她和希斯克利夫经常漫游的沼地里去。”自由的灵魂是无法真正忍受束缚的。像小说中的凯瑟琳一样,女作家艾米莉深谙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在自由和束缚间挣扎,并不是维多利亚时期独有的现象,而是每个人、每个时期都会面临的两难境地。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凯瑟琳即使在死神来临的那一刻也没有想到希斯克利夫,而只是表现出对天国的向往。这里女作家是在暗示读者,凯瑟琳已不满足于一般的世俗之爱,因为世俗之爱是有缺陷的,她不但要赋予爱情以理性,还要赋予其以神性。死后二十年在旷野上飘荡流浪,其目的就是要找希斯克利夫,帮助他恢复已失去的人性,可见凯瑟琳责任心之强,爱之博大。她在临终前曾说,她死后不要人们把教堂压在她的身上。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正如德里拉特拉弗西所说:“人们应意识到……构成受时间限制的人性的各种因素必然不可能完美无缺。”只有死亡才可以克服这些缺陷,使人性达到最终意义上的和谐和复归。艾米莉刻画这个人物时,既有同情也有愤慨;有惋惜,也有批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凯瑟琳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崭新的妇女形象,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女子也是不多见的,其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大凡这样的女子既无法忍受贫穷的物质生活,也不甘于平庸、沉闷的家庭生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既富有又有情趣而浪漫的男子实在微乎其微。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凯瑟琳这一分裂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女作家艾米莉对女性困境的思索,反映出超前的女性意识。
凯瑟琳的死是那么的平静,诚如丁耐莉所言:“没有哪一个天上的天使比她显现得更美丽了。永远的宁静守护着她的安睡。”(215)女主人公凯瑟琳的确是死了,“她的灵魂如今是与上帝同在”(215)。对凯瑟琳而言,“她的生命结束在一个温柔的梦里——但愿她在另一个世界醒来时,也是那样亲切”(218)。然而她的死对希斯克利夫来说却是痛苦不堪。女作家艾米莉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希斯克利夫在凯瑟琳去世之后所经历的折磨与痛苦。当他得知凯瑟琳的死讯后,他对着那多节疤的树干撞着头,抬起眼睛吼叫着,不像一个人,却像一头野兽被刀和矛刺得快死了,以至树皮和他的手上、前额上都沾满了斑斑血迹。在凯瑟琳去世的那天夜里,他在画眉田庄外守候了一夜;在葬礼的前几天,埃德加夜夜在灵堂为凯瑟琳守灵,而他夜夜在田庄外的树林中守灵,甚至当埃德加都熬不住,去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仍固执地守候在外边。他又买通丁耐莉,趁埃德加不在之际,溜进灵堂,打开棺木,和凯瑟琳见最后一面,并把凯瑟琳胸前小盒中埃德加的一绺头发扔掉,装进自己的一绺黑发。“这也许象征着女主人公具有两种不同的个性特征,同时作者还给我们传出这样一个讯息: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它处于不断地背叛自己又回归自己这一双向逆反的运动过程之中。”小说中的爱情模式的不同往往是由人物不一的双重人格所决定的。“性格美的和谐,并不是性格的单一化,而是性格的变化、差异、丰富性、复杂性的对立统一。”凯瑟琳死了,希斯克利夫生命中的全部欢乐没有了,他的生存也失去了意义。他本想同凯瑟琳同去,但他要报复那些害死凯瑟琳的人,因此他还得忍痛活在这个冷酷的人世。这里女作家艾米莉或许是在告诫世人,爱情,当它还是甜蜜的时候,它是阳光,是雨露,是糖浆。当它不再甜蜜的时候,它就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冷剑,爱得越深,就越鲜血淋漓。希斯克利夫现在永远无法向凯瑟琳赎罪了。他相信凯瑟琳是真的死了,从此他便成为了没有灵魂的人。正如凯瑟琳在第九章里所言,“我是希斯克利夫”(105),此刻的希斯克利夫唯一的希望就是,将来他的灵魂可以和凯瑟琳的灵魂在一起。
本章中女作家艾米莉虽然对埃德加的描写只有寥寥数语,但她仍然用谨慎和理智的笔调,描绘了那一份存在于凯瑟琳和埃德加之间的温情,这种平平淡淡的温馨和细细琐琐的体贴,同样是真实而感人的。或许这种人间的温情,和那非人间的爱恋比较起来,太逊色了,太黯淡了,太枯燥了,然而我们要明白,爱情毕竟只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它只是一种唯美的虚幻和情感的激流,因为它并没有建筑在天伦和理性之上,它只是最大限度地寻找一种快感的释放,而匮乏久远的目光和深邃的智慧,当那些非人间的意象消失之后,爱情也就随之而亡了。那真正维持人类社会秩序和文明的纽带,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那一股平平淡淡的相濡以沫的温情,这种温情才是人间不灭的天伦,人间无数幸福家庭的存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温情。在艾米莉笔下,埃德加是一名温文尔雅的绅士,尽管他懦弱胆怯,但不失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他对凯瑟琳的包容和忍让让读者心生怜惜,虽然他是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爱情的绊脚石,但这不是他的错,而是凯瑟琳的自愿选择。
第十七章
就章节而言,这一章刚好是全书的一半,故事也进行到了一半。这一章是故事的过渡章节,在此章前故事主要讲述凯瑟琳、希斯克利夫、辛德雷、埃德加、伊莎贝拉的人生经历,在此章后故事将主要讲述他们的后代——年轻的小凯蒂、年轻的小林顿和年轻的哈里顿的心路历程。故事的第一阶段结束了,从这章开始故事的第二阶段。就在凯瑟琳死后不久,有天丁耐莉正在照料小凯蒂时,伊莎贝拉突然闯了进来,从她对丁耐莉的叙述中,读者了解了一些呼啸山庄最近发生的事情。
本章开篇女作家艾米莉就给我们巧妙地布置好了一个阴郁的场景。凯瑟琳刚死,天气突变,当晚就是“雨夹雪”(221),第二天早晨是那么的“凄凉、阴寒和黯然”(221),这里的“樱草花和番红花都被积雪掩盖住了;云雀也不歌唱了,幼树的嫩芽被风雪打得发黑”(221)。而随后伊莎贝拉的逃跑、辛德雷和希斯克利夫的打斗,都是在这种背景中展开的。“艾米莉·勃朗特的景物描写是所有英国小说里最有表现力的。”大自然往往是人们抒发胸臆的背景、展示人类英雄气概的舞台和陪衬以及人类征服和主宰的对象。但艾米莉对大自然的认识却另辟蹊径,“她的背景描写不是静物写生,而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的动画片。荒原像个动物似的享受着阳光;风以人的声音号叫或者沉默不语;秋天渐渐消逝时最后的花朵带着不安的忧伤垂下了头。季节的变换不是作为静止的舞台布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是像一幕幕生动的戏剧……在读过多数其他作家的作品之后再读艾米莉·勃朗特,就好像离开一个风景画展览会到野外一样”。
本章充满着暴力、流血和压迫。女作家艾米莉通过节奏的微妙变化,使随后的情节有效地与开头一章所引起的期望背道而驰。她让人间的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人间世事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整个节奏瞬时快了起来。辛德雷本来打算要去参加妹妹凯瑟琳的葬礼,但因喝得酩酊大醉而未去成,而希斯克利夫最近这一星期整天去画眉田庄周围游荡。葬礼当天的午夜,希斯克利夫去凯瑟琳墓前守灵,辛德雷把他锁在门外,然后和伊莎贝拉商量,让她和他一起动手杀死希斯克利夫。但善良的伊莎贝拉仍不想置希斯克利夫于死地,因此她便警告了门外的希斯克利夫,让他走远一点。辛德雷用枪瞄准窗外的希斯克利夫时,却被对方抓住,反而射中了辛德雷自己的手腕。希斯克利夫便破窗而入,扑向辛德雷并殴打了他一顿。希斯克利夫对自己的仇人毫不心慈手软,尽管辛德雷已被切破了一条大动脉或大血管涌出大量鲜血,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但他还是猛扑上去,踢他,踩他,不断地把他的头往石板上撞。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刀枪相见,鲜血淋漓。哥特小说传统的“恶魔式”人物跃然纸上。希斯克利夫的残暴的确印证了凯瑟琳曾经对他中肯的评价:“他是一个凶恶的、毫无怜悯之心的、豹狼一般的人。”(132)第二天辛德雷看起来十分虚弱,而且病病歪歪的。伊莎贝拉在谈话中提起辛德雷的眼睛很像凯瑟琳,激怒了希斯克利夫,他拿起一把刀子向她扑来,伊莎贝拉只身从山庄逃了出来,永远不想再回呼啸山庄了。伊莎贝拉讲完这些后,就离开了画眉田庄去了伦敦。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林顿。后来的十二年,伊莎贝拉一直与丁耐莉保持书信来往。辛德雷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面碰面大战终于宣告正式开始了,激烈冲突的结果是辛德雷因欠希斯克利夫的大笔债务而在一整夜的酗酒之后,郁闷而死,时值1784年9月,凯瑟琳死后的半年。而希斯克利夫曾借给辛德雷大笔钱以满足他的赌博欲望,现在希斯克利夫终于嬴回了山庄,成了呼啸山庄的新主人了。希斯克利夫的野性力量和恶棍习性,借助丁耐莉的言辞得以在本章很好地体现。希斯克利夫一罪接一罪地发泄着他的复仇欲望——残酷虐待单纯善良的伊莎贝拉、骚扰殴打身心疲惫的辛德雷以及在第二十八章无法无天地囚禁丁耐莉和小凯蒂。女作家艾米莉对希斯克利夫的这些暴力描写一方面说明希斯克利夫正在费尽心思地实施着他的复仇阴谋,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强权的社会里,法律是不会保护弱者的。上一代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希斯克利夫,他需要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复仇大业。小凯蒂和小林顿的诞生,预示着新一代的故事的开始,而希斯克利夫是贯穿这两部分故事的一条纽带。
本章是辛德雷的告别演出。与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相比,辛德雷的性格相对不那么复杂,尽管如此,他也有他矛盾的一面。儿童时的他向父亲要礼物时,要的是小提琴,这说明他有艺术家的气质;当小提琴坏了,他哭起来,这又说明他是软弱的、敏感的。正如丁耐莉所言:“辛德雷表面上看上去虽然是一个更坚毅的人,结果证明却是令人悲伤地更糟糕,更软弱。当他那条船触礁时,船长放弃了他的职守,而全体船员,不是尝试挽救这条船,而是张徨失措,乱作一团,没有给他们这只不幸的船留下一丝得救的希望。”(241)不过这方面的气质我们以后没再发现,也许在他的婚姻中还有一些表现吧。看起来,希斯克利夫进入恩肖家庭之后,家庭中那种紧张气氛压抑或摧毁了辛德雷天性中较为和善的那部分。虽然他先前对希斯克利夫施以粗暴而残忍的折磨,但婚后的他对妻子的爱却是一往情深。弗朗西斯的死使他精神崩溃,绝望地过起了放荡的生活。艾米莉曾从她的弟弟勃兰威尔身上看到过放荡狂饮的下场,“白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在家里四处打盹度日;晚上则大吵大闹、胡言乱语。他整个人的行为,变得极端不负责任,使家里终日不得安宁,家人个个消沉丧志”。 辛德雷的生活道路对她来说太熟悉了,极有可能辛德雷的艺术家之梦的毁灭是以勃兰威尔毁灭了的希望为基础写成的。
第十八章
从本章起,时间一跃到了1797年,作者一开头便一笔带过了自上一章之后12年来发生的事情。凯瑟琳的死亡成为了小说的分水岭。围绕着凯瑟琳的死亡,艾米莉在前几章不惜笔墨地描述了凯瑟琳的严重病情、她和希斯克利夫的最后诀别、希斯克利夫和埃德加的再次狭路相逢以及希斯克利夫对她灵魂的诅咒。这些场景都是小说的高潮、核心和精髓。因而,当小说情节推进到第二部分后,却并不被许多读者看好,他们认为高潮已过,剩下的也只是余波而已,甚至是狗尾续貂。尽管后面的章节确实未能达到前面章节的感情大爆发的高度,但它们对于小说的结构,尤其是对小说的主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如火如荼的爱情的诗篇(第一代情人的故事)给感动的读者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但是对人生的哲理思考(第二代情人的故事)才是整个作品的核心部分。”
命运之轮经过一个轮回,新的和谐开始建立。从本章起,故事主要围绕第二代年轻的小凯蒂和哈里顿以及林顿·希斯克利夫之间展开。故事开始时凯蒂已是一个13岁的可爱的小姑娘了。她对人亲热的态度使人极易想起已故的凯瑟琳,“但是她不像她的母亲,因为她像鸽子那样温和柔顺,她的声音又是那么柔和,脸上一副沉思的表情;她的爱也不是炽烈的,那是一种深沉、温柔的爱,但是必须承认,她有缺点来衬托她的优点,莽撞的性格是一个;再就是任性固执”(246)。小凯蒂继承了父母的优点,她有着恩肖家族漂亮的黑眼睛,林顿家族细嫩的皮肤、秀气的身材和黄色的卷发。她有着母亲凯瑟琳的敏感、活泼和任性,但她不暴躁,因为她同时继承了父亲埃德加的温顺、深沉和文雅。小凯蒂的这种性格特质在充满宠爱与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呈现出与文明和解的状态。她的父亲埃德加时刻铭记着呼啸山庄给他带来的痛苦回忆,时刻也不忘记情敌希斯克利夫现在就住在那里,所以从小女儿凯蒂出生就未离开田庄半步,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恐怕算附近的礼拜堂,因此长大了的凯蒂当然对山谷那边的呼啸山庄和那里的人一无所知。虽然埃德加想保护女儿,使她免遭魔鬼希斯克利夫的残忍迫害,的确在父亲的极力保护下,小凯蒂成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循世者,而且显然十分满意自己的生活”(247),但这临时的庇护又是那么的无力和短暂。孩子们都是有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小凯蒂也不例外。她渴望去看看山谷那边的盘尼斯顿山崖的仙人洞,但每次都会遭到父亲埃德加的推脱,因为埃德加明白,潜在的危险就在那里。但有一天,埃德加接到信说妹妹伊莎贝拉在伦敦就要死了,并请求他把儿子小林顿带回田庄,他便前往伦敦去接她的儿子小林顿。当父亲不在画眉田庄时,小凯蒂就由丁耐莉照看,埃德加反复嘱咐,在他不在时要丁耐莉时刻陪着小凯蒂。开始时小凯蒂还能安心待在家里,但没过几天她便厌倦了,丁耐莉允许她自己出去在附近走走。可是有一次,小凯蒂独自离开了田庄去了盘尼斯顿山崖的仙人洞,去闯荡外面的世界,并且循着荒野原始的呼唤只身来到呼啸山庄,从此陷入希斯克利夫复仇的漩涡之中。这下可把丁耐莉吓坏了,赶忙去找她,最后在呼啸山庄里找到了她,她正和哈里顿在一起。那儿的女仆告诉丁耐莉,小凯蒂和哈里顿一起到山崖玩了一天。丁耐莉催促小凯蒂赶紧回家,但顽皮的小凯蒂还没有尽兴,不愿意走,丁耐莉威胁小凯蒂说:“如果你知道这是谁的房子,你就会巴不得快些离开这里了。”(253)哈里顿已经长成了一个身材匀称的青年,魁梧而健康。小凯蒂和他相处得很不错。小凯蒂从丁耐莉的口中得知,原来哈里顿是她的表哥。她们俩回到家中,丁耐莉向凯蒂解释埃德加是多么讨厌呼啸山庄的人,知道小凯蒂去过山庄将会多么生气,说不定还会因丁耐莉的失职而解雇她。小凯蒂同意保守秘密。实际上在本章中女作家艾米莉已为日后的故事情节发展作了伏笔——小凯蒂对哈里顿有好感,故事的结尾他们最终结合在了一起。同时本章还又一次强调了小凯蒂和哈里顿都长着一双恩肖家族的眼睛。这一描述为第三十三章的内容奠定了基础。在那一章里,他们把他们那双酷似凯瑟琳的眼睛转向希斯克利夫,从而使得他激动不安。但小林顿即将登台,这就为故事的喜剧冲突抹上了一笔。感情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
本章值得注意的是,丁耐莉让我们第一次全面了解到了长大成人的哈里顿的情况。哈里顿是位“身材匀称健壮的青年,容貌端正,魁梧而健康”(256)。丁耐莉把他目前的状况比作“好苗子埋没在荒野的乱草丛里”(256),虽然它们的成长暂时会受到一些阻力和挫折,但“只要换一种情况,在良好的环境中,是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的”(256)。这实际上是艾米莉向读者表明了哈里顿受到的压迫不是永远的,他必将会自发图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作为整个呼啸山庄的主人,希斯克利夫现在以最卑劣、粗暴的方式抚养哈里顿,准备把他的复仇行动延续到第二代身上。作为呼啸山庄的合法继承者,可怜的哈里顿除勉强糊口外被剥夺了一切,而且他还得时刻记住:作为与希斯克利夫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儿子,他只能靠希斯克利夫的施舍寄居在呼啸山庄。“哈里顿是在没有爱怜、没有教导,只有轻蔑和嘲笑、损害和侮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可怜的身世使人想起了《灰姑娘》。”但由于哈里顿无畏的天性,不甘受压迫的性格,尽管希斯克利夫竭力阻碍他的发展,但希斯克利夫并不能够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希斯克利夫只是“把这孩子培养成一个粗野无礼、没有教养的人”(256),让他每天在农场干活。或许希斯克利夫对哈里顿心存恻隐之情,因为现在的哈里顿就像当年的自己——有血性、有骨气,但受到极不公的对待。这也为后来故事的发展作了铺垫,最终希斯克利夫原谅了哈里顿。本章我们还需注意的是,艾米莉又一次提到了仆人约瑟夫(Joseph)。在丁耐莉看来,哈里顿之所以堕落得那么快,约瑟夫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娇惯哈里顿,别有用心地想激起哈里顿对希斯克利夫的憎恨,然后某日让哈里顿公开去对抗希斯克利夫。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尽管约瑟夫是位令人讨厌的人,就如同他的名字那般,但他始终对恩肖家族忠心耿耿。
第十九章
本章写得不长,开篇就宣告伊莎贝拉的死讯,时值1797年7月。伊莎贝拉的一生可谓生命之火时时在她身上闪烁。她的名字使人想起18世纪英国作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676-1745)的《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4)。该作品的女主人公也叫伊莎贝拉,她是一个脆弱的、任凭邪恶的曼弗莱德摆布的女子,“她对曼弗莱德的恐惧很快压倒了其他任何恐惧”。而艾米莉笔下的伊莎贝拉,她在生活中是勇敢的。在她爱上希斯克利夫以后(虽说这爱是糊涂而愚蠢的),她大胆地与他私奔,在她那灾难性的婚姻之后,她还不失勇气,先是联合辛德雷把希斯克利夫锁在山庄之外,然后又和他大闹一场,逃离呼啸山庄,只身逃往伦敦。在她出走南方之后,便杳无音讯,一直到她去世,我们才得到她的消息,但不难想象,她只身一人在外,还要抚养孩子,想必一定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
伊莎贝拉死后,埃德加带回了她和希斯克利夫的儿子小林顿。虽然小凯蒂想象表弟有许多优点,他的到来肯定会使自己兴奋不已,但当她当面见到小林顿时,却十分失望。这就印证了那句古话,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小说第一次对这位在异乡长大的希斯克利夫的儿子做了描述。丁耐莉第一眼看见他时,小林顿正坐在马车的角落里睡着了。他“身上裹着一件暖和的、镶皮边的外套,仿佛是过冬天似的。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纤细、带点女性气质的男孩”(261)。虽然小表弟对她起初很是冷淡,但小凯蒂后来还是对小林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已决心把自己的小表弟当一个宠物看待,而她也满心希望他是一个宠物,她开始抚弄他的卷发,亲他的脸蛋,用她的小茶盘给他端茶,像对待一个婴儿似的”(263)。小林顿从父母那里遗传过来的似乎都是他们的缺点:希斯克利夫飞扬跋扈、苛刻暴虐的坏性格和伊莎贝拉敏感脆弱、傻气固执的特征。这些缺点都是希斯克利夫和伊莎贝拉最糟糕的一面。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在故事中只能充当一个消极的因素。小凯蒂从一开始就对他抱有一种怜悯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贯穿于他们关系的始终。如果我们把小说中的四位男性人物(埃德加、辛德雷、希斯克利夫、小林顿)放在一起对比他们的性格,我们不难发现女作家艾米莉实则在嘲笑男性统治的世界——宗法思想的核心。这种父权制不仅表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里,也表现在他们的婚姻中。因此,他们要么软弱多病,要么强悍粗暴。19世纪初的英国,虽然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足和悠闲,但妇女还是处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是男人的附属品。少数上流社会的妇女不用工作,但只能结婚做家庭主妇,或是成为父亲终身的负担。而处于这两个极端的妇女们也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以性别为向导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都给女性带来了焦虑和恐惧。女作家艾米莉不想做“房子里的天使”,在她的《呼啸山庄》里,她对男性权威的态度是否定的。小说中的女主人们对恶棍式男主角最初都是既畏惧又仰慕,既依赖又想挣脱,但最终她们都能同命运抗争,要么勇敢挣脱枷锁,要么公然反抗****统治,要么运用语言能力挑战男性权威地位,成功捍卫了女性尊严,展现了不可遏制的女性力量,虽然她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小说中凯瑟琳的丈夫埃德加就是一个男权文化和意识的“杰出”代表。
当小林顿抵达画眉田庄的当晚,呼啸山庄的老仆人约瑟夫忽然来到,说希斯克利夫吩咐他马上带走小林顿,因为他是希斯克利夫的儿子,他决心要回自己的儿子,让埃德加马上把儿子交给约瑟夫,让他领回。埃德加既不放心又难过,但他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于是答应第二天把小林顿送到呼啸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