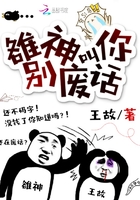淮阴城的四周轰鸣四起,比常见的霹雳车大一倍的霹雳车,在淮阴城四周竖起上百架,连续不断地往城墙上砸着巨大的石块,城墙上的士兵个个面色铁青地看着这些庞然大物不断地朝自己飞来;城墙上的砖块一次次地脱落着,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里内的土胎。
扬州、荆口方面由元霖镇着,元钺亲自在淮阴城边督战。他一瞧城墙有的地方被砸掉了三层砖露出土胎来,便觉得有戏,命几台霹雳车一同加紧往一处投石。就算这中大型霹雳车的准头相当差,城墙依旧被元钺的军队硬生生砸出缺口来,可惜城墙下半截比上半截还好厚实好多,用了一倍的力气,似乎没什么变化。
第三日,从附近山里开采来的大石块已经被砸得差不多了,霹雳车也消耗损毁过半,
元钺命令休战一天,做些准备工作,再派人去城墙边招降,淮阴城已经被围困五个多月,城内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他相信,梁军的军心已经有了动摇。
没想到,这个简博是真狠!
他居然把南琅琊其它四城里那些高级官员和武将的亲属女眷绑到城墙上,并向元钺挑衅:“元钺,你不是号称你北渝是仁德之师么?有本事你继续砸啊!”
元钺修养这么好的人,见了简博这贱招也是气得差点骂出脏话:“他奶……的,拿女人做挡箭牌,尔乃小人!非忠义之士,实属愚忠!愚不可化!”
别说渠头城和渎城两座被主动献出的城内的世家大族已经归顺了元钺,阫城和泰州城内的大部分地绅土豪还有大族都已经投降归顺元钺,现在的军需粮草有一大半几乎都是这些人打自家仓库里拿出来的。
这些人看着自家嫁出去的孙女、女儿、姨妈一个个被绑在城头,便都跪在元钺的军帐里,用哀求的眼神看着面如铁色的元钺,求他手下留情,他们愿意去劝降简博。可任谁去也没用,简博越听他们劝,就越是觉得自己忠君不二,乃是世间难得的真正君子。
元钺骑着马,在城墙前来回溜了不知道多少遍,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命一排士兵拿着盾牌和绳子冲到城墙下,对着上有喊:“有愿意归降我北渝者,跳入护城河!我们愿拼死相救!”
开始还没人敢动,可突然有个年轻的小姐,一下就跳了下来,扑通一声,掉进护城河。那排士兵都是水性好的,有的就跟着跳下去,用盾牌顶着城上射下的箭矢,抛去绳索,将那小姐救上来。
其它女眷见有活路,胆量大力气大的,纷纷挣脱官兵的桎梏跳下城墙。
这可把简博大喊:“弓箭手!给我射!射死这些没有廉耻的娘们!”
可城上的士兵似乎不忍,一时间,竟然没人下手,简博气坏了,大叫:“给我抓紧她们!死死绑住!”然后亲自弯弓搭箭,对准了一个正在下落的中年妇人射了过去,一剑刺中那妇人的心脏,等到元钺的人把她拖上岸时,她已经没了气。
“这是哪家夫人?可有人认识?”
军帐中铺着简单的草席坐着一排正等着自己的亲人来接的女眷,为了救她们,死了好几十个人。元钺带着那被简博一剑穿心的妇人,进了帐,对着众女眷询问道。
众女还在惊恐中,帐中期期艾艾的哭声此起彼伏,有人装起胆子道:“回殿下,奴家……奴家知道。”
“何人?快快讲来!”
“这是卢家三老爷的夫人,陈氏。”
“陈氏?”元钺一听,眉头一皱,想起陈庆余来,于是问道:“本王问你,她可是跟陈庆余有关系?”
那妇人道:“正是正是!她是陈太守的姊姊!”
元钺心中想笑,真是天助他也,可面子上却是眼中含泪,叹息一声,亲自把陈氏的尸首带到关押陈庆余的地方,还把那敢说话的柳家二少爷的夫人带去了。
陈庆余一见姐姐,伏尸大哭。
元钺给柳二少夫人使了个眼色,那少妇便凄凄惨惨地诉说起简博怎么把先把她柳家、卢家还有陆家的老爷给杀了,然后把他们全族关押,抢了他们家的粮仓,最后还把女眷拖出来,逼着她们上城墙,再说道如何有人跳墙,还有卢三夫人陈氏如何惨死在简博箭下……
陈庆余乃是没落士族人家,从小便没了母亲,父亲又忙于生计,是姐姐将他照顾大的,她为了他到了二十岁才嫁人,嫁给了年近五旬的卢老爷,这婚姻也依旧是为了陈庆余的仕途,陈庆余视她如母。
听完柳家二少夫人的话,陈庆余双眼通红,咬牙切齿,元钺趁热打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道淮阴城内饿殍遍街的场景,几乎是潸然泪下,好像他见过似的,他给悲愤中的陈庆余亲自松了绑,然后握住他的手,动情地劝道:“陈大人,那简博小儿如此无情无义,就算是为了淮阴城的百姓,你也应该帮助本王啊!”
陈庆余没有当即答应,他只是没有吭声,元钺命人给他准备卧房休息,他知道,陈庆余离被策反已经不远了。
再说在泰州城的玄甲军,正当元钺用霹雳车如火如荼地轰着淮阴城墙时,晚上军营来了个来小偷,可惜没抓到,次日中午便有人开始腹痛不止,到了晚上,玄甲军军营里几乎有一半人开始腹痛难忍,就连元霖也未幸免。
翌日,全军只有喜儿一人好好的,这难道还有什么好狡辩的么。元霖气坏了,命人把喜儿重新绑起来,他面如菜色,忍着腹痛问厉声质问喜儿:“说!你到底是何人派来的!”
“我想办法治好大家就是了!”喜儿不服气地顶撞道。
“你若是治不好,我定叫你陪葬!”
喜儿想破了脑袋,想出几张方子来,也不知道哪张方子能奏效,霖王不放心,去元钺那里借了军以来。几个大夫商议一番,各自意见不同,于是大家决定各自开方子,熬好了找人试药。
三日后,竟然是喜儿的开的其中一张方子凑了效,元霖起初不信,可喝过药后,大吐一场,身子立马爽利了,人也精神了,午饭吃了三大碗饭和整整三斤牛肉。
可军中这么多人,药也不够用,让喜儿去元钺那里要。喜儿一听元钺的名字便缩成一团,死也不肯,元霖对这个小女子更加起了疑心,可问她,又是什么都问不出来。
元钺听说玄甲军军营里闹了疫,便让自己手下的部队换了个地方重新安营扎寨,派了人去把玄甲军军营看守起来,命人不得随意出入。
这令下得相当地不近人情,查大牛还想去找卫长征讨教武功,闯进殿去却发觉元钺竟跟陈庆余下棋下得正在兴头上,两人有说有笑的,似乎完全不把玄甲军的死活放在心上。
查大牛来火,嚷嚷道:“喜儿还四殿下那儿呢!”
元钺一听,面色跟着沉了沉,封营令依旧未改,只叫人把大牛轰出去,便继续继续与陈庆之下棋。
此时,陈庆余的心思却不在了棋盘上,他像是想起什么事来,只走神这么一小会,便让元钺占了上风,接着便一败涂地。
“陈将军心中可是有事,怎么后半局跟前半局像是换了个人在下棋似的。”
陈庆余惭愧地笑了笑,抬起头,端详了元钺一阵,悠悠开口道:“以殿下性情、风度喝至于被派到这东南一隅来?”
元钺淡然一笑,道:“无论在哪里,对得起良心天地便好。”
“殿下当真如此淡然,还叫人怎么放心跟随殿下?”
元钺立刻停下手中收拾棋子的动作,一瞬间有些愣神,这样的回答让他始料未及。
“这世上许多事非左即右,就算是江湖中号称不问朝局的逍遥阁亦免不了在子丑寅卯中做个选择,殿下何故,以为能在这琅琊一地做个偏安一隅的闲散王爷?陈庆余盯着窗外淮阴城的方向,眼眸中散出拒绝的光来,“殿下可知,五十多年以前,被封为琅琊王的北渝皇子,姓甚名谁?”
这倒把元钺给问住了,陈庆余讥讽地一笑,道出二字:“元漓。”
“元漓……”元钺手里攥着茶杯,思索着这个名字,之前见过一次家谱,当今渝帝乃是文帝的二皇子元安,其余的皇子病的病,死的死,如今只剩下一个六皇叔元复。
而独独排行第七的那个人,没了名字,没了事家谱中竟然半点痕迹也寻不得,如今被一个南朝的臣子提起,甚是奇怪。
陈庆余接着道:“当年我父亲跟随大梁的开国皇帝萧承从琅琊州起兵,一举推翻了南宋。可有谁知道,当年在琅琊州资助萧承的,乃是一个渝人?而南宋灭国前两年,宋渝在淮北一线大战一场,结果是淮河以北尽归北渝,你们武帝元安一战成名,但你可知,这背后让淮北十三州刺史,尽数投降北渝的又是何人?”
“难道,都是我这位皇叔?”
陈庆余一脸讽刺地笑道:“你们武帝还真是有意思,这样的人物竟然将他除了姓名,痕迹全无,若不是南人的国仇家恨,恐怕是没人记得他了。”
光是讲这人的故事,陈庆余便花了三个时辰,一直讲到半夜,最后画了一张淮阴城的秘密暗道图给元钺,道:“这些密道乃是旧时琅琊王元漓所建,是为了百姓危难时刻逃命所用,可后来被我父亲填埋了出入口。若是殿下答应我一件事,我便把地道口的位置,告知殿下。”
元钺道:“将军请讲。”
“我听说一旦南朝城破,平民百姓都要被拉去渝国充当奴役。请殿下,免去这些百姓的奴役之刑。”
元钺微微颔首稍作掂量,随即点头答应:“好,我答应你,不仅是淮阴,南琅琊全境五城二十三县的姓,只要不扰乱治安,本王一定护他们周全。”
“还有第二件事。就是攻城之事,莫要让玄甲军插手。”
“这……”元钺犹豫了,不明白陈庆余的用意,陈庆余也不解释,只是盯着元钺,要一个回答。
元钺得不到答案,顿了顿,坐正了身子,再次点头道:“好,既然我信了将军,便答应你,攻淮阴之事,不让玄甲军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