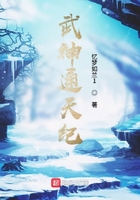城西鬼屋,近日方才闹出来。
传闻那屋子本已荒废,可近日也不知怎么的,一到夜里都会发出阵阵悠扬琴声,曲子每日都不同。有胆子大的人不信传闻,非要去,结果次日醒来时,不是在街头赤着膀子呼呼大睡就是把自己吊在树上,满脸画着王八。
再细问那些人之前发生了什么,却没一人记得。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就有了鬼屋的传闻。
夜里谁家孩子不听话不睡觉,只需说上一句,信不信待会就有坏人把你丢到鬼屋去,孩子必然转眼就老实了。
夜,伸手不见五指,阴风瑟瑟,吹的人身上直起鸡皮。花赫儿手上拎着一只鸡,背上扛着一个开过光的瓢。据说那瓢经过某著名大师开光,还是离孽在街头花了十个铜板才买回来的呢。
别问为什么探访鬼屋要带这个东西——因为实在不行,方便自己敲开瓢了自己。
花赫儿推开大门,身后跟着一身红衣一脸正气的叶霓。
别看叶霓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可实际上却是个胆小的。
之前还被半夜睡不着出门游荡的花赫儿吓病过,堂堂神医,居然被吓出一身毛病,说出来实在是令人汗颜。
花赫儿弓着腰,小心翼翼的往前走。
叶霓拍拍她的肩膀,“大人,为什么咱们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啊?”
“啊呸,什么叫偷偷摸摸,这叫小心为上。”
当然,这是怕打草惊鬼嘛。
花赫儿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些封建迷信?只不过,不怕野鬼,就怕野人。
若此处真有这么邪乎,那么必定有人作祟。
叶霓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不耐烦道:“好吧好吧,小心为上,那为啥怎么还要蒙着脸啊?”
又不是做贼。
再说了,这黑灯瞎火的,就算是不蒙着脸,也绝不会有人看见她们的模样,顶多记住她们雪白的牙齿的模样。
花赫儿不说话了,食指在唇前一比划,低声道:“别说话,你听,是不是有动静?”
闻言,叶霓立马闭上嘴,抻着脖子认真的探听起来。
听了半晌,哪里有什么动静?
她话还没问出口,就见花赫儿笑的一脸得意,“我听见了三只蚂蚁刚才路过的声音,怎么样,惊不惊喜?”
三只,蚂蚁,路过?
叶霓的拳头渐渐捏紧,面目狰狞,内心OS:突然很想一拳头把雇主打到泥巴里抠不出来怎么办?
当然,叶霓的心理活动花赫儿自然不会知晓,她此时正悄咪咪的前进着。这院子的确古怪,白天据说是锁着的,院子里又没人,何以到了夜里,院子就开了?她刚才只是轻轻推了一下门就进来了。
难道这门还能成了精不成?
花赫儿猫着腰,顺着白日里她摸来的院型结构图,堪堪没有撞在柱子上,勉强的进了传闻中闹鬼的拿件屋子。
待进了屋子,花赫儿从袖子里掏出一根火折子点亮,四下打量了一番,“这地方用来与人幽会,或是逃课喝酒倒是极其合适啊。”
房梁上的横木早已倾斜,不知何时就会掉下来,屋内桌椅板凳全部没有,倒是一张破破烂烂的木板横在屋角处,坐在那里,抬头便可见窗外风清月明,视角极佳。
叶霓跟在花赫儿身后,见屋内什么都没有,胆子这才大了起来。
她抱着胳膊,扭着腰转身,“啊!!”
一声尖叫撕裂夜空,花赫儿掏掏耳朵,嬉皮笑脸的扭头对上叶霓身后的那人,“兄弟,房梁上趴着的滋味儿不舒服吧?”
叶霓身后的人,一身暗色衣裳,脸色惨白,偏生那双唇却又殷红如血,在这夜色中,乍然间看见这么个人,三魂七魄都能给吓的离家出走一半。
那是个年轻人,花赫儿白日里也曾见过。
毕竟这年头,上县衙借钱的人,也着实是不多。
少年见到花赫儿,眼中的震撼溢于言表,他抿了抿唇,冷声质问:“你跟踪我?”
这一路上,跟着他的人不下其数,可花赫儿应该是唯一一个身上没有杀气的。
他小心翼翼,连出门都换上了乞丐的衣服,这县令难道发现了什么?
思及此,少年脸色一变,手下意识的攥成了拳头,似是一头困兽,随时准备奋力一搏。可少年毕竟是少年,即便是表现的再凶狠,眼中的无措和纯澈也骗不了人。
花赫儿无奈,苦笑一声:“本官长的如此一脸正气,居然还有人把我当变态跟踪狂吗?”
少年蹙起眉头,目光冷冷的落在她身上,事关性命,不可大意。
毕竟对于此时的他而言,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的人。
见少年这副防贼防狼的警惕样,花赫儿无奈的摸摸鼻子,看了眼少年,“并非是跟踪你,我说是碰巧,你信么?”
“你有什么目的?”
少年避如蛇蝎,脚下不动声色的后退了几步,“想要我的命?”
花赫儿抚额,无奈叹息:“我要是想要你的命,还会在这儿动手?”
少年面色一怔,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可对花赫儿的警惕却丝毫没有放松。
“你身上的沉香味儿,挺浓的。”
花赫儿说着,顺手敲了敲屋子内用沉香木做的房梁,不得不说,这户人家之前八成也是个富户,否则能用沉香木做房梁,这不是脑子抽了就是有钱烧的慌,炫富炫的如此低调,简直令人汗颜。
“就凭这么?”
花赫儿摇摇头,“其实,是因为今年你解答的那道题。”
寻常百姓人家的孩子与世家贵族公子之间的差距,大概就在一个眼界。他今日的作答,明显的隐藏了实力,只是轻描淡写的抛出重点。
“我曾拜读过当朝翰林大学士刘先生的字迹,可谓是惊为天人。”
提及刘学士,少年眼神微变,似水面忽的起了涟漪。
花赫儿勾唇,继续道:“普天之下模仿刘大学士字迹的人不下少数,可能称得上是三分神韵三分形韵的,只有你。”
少年深吸了口气,“我敬重刘学士,临摹他的字迹,有何不妥?”
“并无不妥,刘学士曾说,他的继承人,只有一位,那便是他的小公子,刘迟之,我曾见过他唯一亲传弟子的字迹,不如你。那么你说,你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