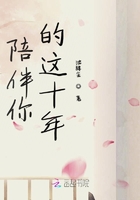一中国古代名学的地位
中国古代有所谓“名家”,无所谓“名学”,名学这个名词,不过近人用以译西洋的Logic之后,才通用于学术界。初学者流,以为Logic是西洋的特产品,中国实绝无其学。稍进者则谓东洋也有,即如印度的“因明”,虽不能与西洋近代的Logic相比,至少也可以敌西洋古代的Logic。于是有些名学家,插入因明,与西洋论理学相提并论。见解比从前自高一筹了!却于此外很少论及中国名学的,未免是一个大缺陷!
今欲说明中国古代名学的重要,当先研究中国古代名学的地位如何?
1.中国古代名学在世界名学上的地位——世界名学,可照世界学术的分野,划为三大派:
A西洋名学——即Logic,又译为“逻辑”或论理学,始于Aristotle,著有Organon一书,多讲形式论(Formal logic)为西洋古代逻辑的经典。到Bacon,乃反对Aristotle的说法,著Novamorganon一书,提倡归纳法(Induction)。更经Mill的发挥光大,而西洋近代逻辑乃完全成功。他的A System of Logic,可算个代表的著作。到现在杜威(Deway)极力推尊试验(Experiment),因有试验论理学(Experimental logic)的徽号。他的How We Think一书,就是这派代表的著作。——这是西洋名学的小史,也就是世界名学的一部。
B印度名学——印度名学,叫做因明。始于足目,号古因明;到陈那,著《正理门论》,大为改革前说,号新因明。自此至今,在印度无大改进。——这又是世界名学小史的三分之一。
C中国名学——中国名学的变迁,可分三大时期:a固有名学时期——断自秦汉以前。不但古代所谓名家有一种名学,即儒家,道家,法家也各有一种名学,尤以墨家为较完备关于名学的理论,多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书。如《论语》,《中庸》,《大学》,《庄子》的《齐物论》、《天下篇》,《尹文子》,《公孙龙子》,《荀子》的《正名》和《解蔽》两篇以及《墨子》等,尤以《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较详细而有西洋科学方法的色彩。b印度名学输入时期——自汉唐到明,因佛学输入日广,而因明也次第输入,为治佛学者所必知。其较有系统的著作,只有唐玄奘法师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复经窥基注疏,乃更为完备。印度名学得有光明于今日的缘故,赖此而已!c西洋名学输入时期——从明末到今,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为西洋名学输入中国之始。自后译者渐多,其最著名而又可代表西洋名学精华的要算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二书,次为王星拱编的《科学方法论》,和刘伯明译的《思维术》,科学社的《科学通论》,虽为杂集,也可窥见西洋近代论理学的一斑。至于从日文中重译过来的,多不出《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二书的范围,而且多属形式论理,不足指数。必欲举一二部充数,以我所见,就要算胡茂如所译日人大西祝的《论理学》,和张子和杂辑日籍所成的《新论理学》二书而已!其它坊间关于名学的教科书,更简陋不足道了!——这是中国名学的小史。除印度因明,在中国稍有光大,而且在一部分思想界,稍生影响外,西洋逻辑,还完全只有翻译,无所发明!在学术思想上的实际影响也甚微弱!质而言之,尚未成中国的名学,可以在我们脑筋中发生极大的化学作用。所以论到中国名学的精华,还在古代。我们欲完成世界名学的大观,合西洋名学,印度名学,中国名学于一炉而冶之,就要知中国古代名学的概要,和在世界名学上的地位。
2.中国古代名学在中国学术上的地位——世界名学有三大派别,而学术也因此产生三大派别:即中国学术,西洋学术,印度学术。中国名学,是中国学术的工具,有中国的名学,才产生中国的学术。西洋名学,是西洋学术的工具,有西洋的名学,才产生西洋的学术。印度名学,是印度学术的工具,有印度的名学,才产生印度的学术。中国系的学术,不发源于西洋和印度;西洋系的学术,不发源于中国和印度;印度系的学术,不发源于中国和西洋,他们的最大最要的原因,就在各系都各有一种特别的名学和方法。所以我们要研究西洋学术的精神,不可不先知西洋学术的方法,要研究西洋学术的进化,不可不先知西洋名学的进化。要研究印度学术的精神,不可不先知印度学术的方法,要研究印度学术的变迁,不可不先知印度名学的变迁。要研究中国学术的精神,何以不能如西洋学术的正确进取,印度学术的精深度大?也不可不先知中国学术的特别方法和名学的变迁了!
不但欲明世界学术的异同,须明各派的名学和特殊方法,就是欲明中国学术中的各派异同,也非明各派的名学和特殊方法不可。儒家何以不同于道家?墨家何以不同于儒家?所谓“孔老之争”,“儒墨之辩”,其最大的原因,又在何处呢?简单说来,多由各家的方法不同,名学殊异。所以欲知中国学术的支分派别,也不可不知支分派别的方法。老子和杨子的“无名”,孔子和荀子以及法家的“正名”,墨子的“实用”,庄子的“齐论”,(庄子的齐物论有二义。一为齐物,二为齐论。)皆各家名学的根本观念。不明这种根本观念,也就无由知他们的真正异同了。
中国学术,多发源于古代。古代学术,又以古代名学占重要的地位。一来是古代学术的一部分。二来是中国学术的根本方法,即Bacon所谓“诸学之学”。所以我们真欲整理国故,使古代学术复明于今日,则研究古代名学,实为先务之急。
二中国古代名学的派别
我国分别学派的标准:有用“家”的,如所谓道家,法家,名家;有用“人”做单位的,如孟子,荀子同家而分别叙述,老子,庄子同家而各别讨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多用后法。我今说到中国自古代名学的派别,如用“家”做标准,则学说不免有所出入。法家的名学,多同于儒家,庄子的名学,不同于道家的老子,就是实例。如用人做单位?又不免支离,不易得中国名学的要旨,而且也太词费。所以我今以学说的异同,做分派的标准,不袭“九流”之说,也不必人各一篇,只要学说大体相同,就合成一派研究,如不相同,虽昔人叫做一家,也必分别讨论。综其大略,约有五流如下:
一无名学派——老子发其端,杨朱继倡其说,以时代论,无名学说发生最先。故为古代名学第一派。他的要旨,可分二端,略述于下:
A无名主义——老子最先主张无名,他的理由大概有二:他说:
“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他既说常名无名,而有名之后,又常同出异名,自必至于失“道”,所以不如复归“无名”之始,而可入于“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开宗明义的第一义,也就是他主张无名主义的第一个理由。且有名了,最易引起人去争名好名。老子曾为周室柱史。历观前代争名和好名的事实自多。又见当日周室衰微,名守俱乱,他是一个学术的大革命家,富有反抗的精神,更不得不主张无名,使世俗无所借口,两相争执,与孔子的正名同一用意。不过孔子是用的积极方法,老子是用的消极方法罢了!所以他说:
“名与身孰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大辩若讷,……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这是他主张无名的第二个理由,到了杨子,更说得显明。他说:
“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他以“名”为人造的东西,与“实”不相干,所以他又说:“不矜贵,何羡名?”“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名焉。”“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照这样说来,所谓名者,已由名物的名,变为名位的名了。他恶名位,而主张无名,与孔子欲赖正名以定分的适相反对。或者杨子即以孔子主张正名过度,而毫不顾实际,遂有此反动,与老子默合了。
B观物法——老子虽然一面主张无名,却一面又指出观物法。其意或者即在名可无而物不可不观。西洋论理学原有二大派别:一为注重正名的,即为Aristotle的形式论理学;二为注重观物的,即为Bacon的归纳的论理学。老子的名学,即偏重观物学。他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所谓“物”,“象”,“精”,“真”,“信”,即事物,现象,真理。“阅众甫”,即观察万物。与西洋逻辑注重事实与观察的有些相同。他还指出两种观物法,很有研究的价值。他说: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无欲以观物,是一种客观法。有欲以观物,是一种主观法。前法要人除去个人的利害观念,以观察物的变化,那么就可知物的妙。妙,就是物的真相。后法任人挟着主观的利害观念,观物的结局对于人怎样,所以不免于“徼”。“徼”,有偏蔽的意思。比如看见一老虎,我们就说他是个孽畜,这全是从老虎对于人的利害关系上着想,所以不免把老虎的真相变了!其实老虎与耕牛同生宇宙间,离开个人主观的欲心,完全平等,无所谓孰善孰恶。不过人类容易以有欲观物,不易以无欲观物。所以所谓是非善恶,有许多是人的,不是物的;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老子即欲人由主观法,到客观法的。所以他说: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无名主义,应用于哲学,就成老子所描写的无名扑之道而任其自化。应用于人事,就成了杨子的逸乐主义,恐易于流于放纵,不顾社会了!晋世清谈之士,多不讲行检的,就由受了无名主义的流毒。
无欲观物法的应用,就成了老子所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质而言之,不得以私心害事就是了。
B正名学派——正名主义,发端于孔子,荀子更专论其说,而法家则窃取这种主义,应用于政法,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大多数人的主要观念。其起源大概有两种理由:一对于老子无名学说的反动;二对于纷乱的时局,藉正名以救济。我们考察孔子与子路为出公辄不认其父蒯聩,而称祖父灵公为父的问答,就可见孔子主张“正名”的作用。他们的问答是: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