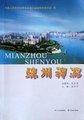(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诗云:“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麑,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吾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夫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欲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观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印度佛书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字俗语。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