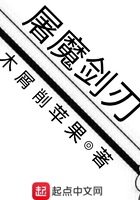卷着一身风尘,推着那辆迟暮穷途的摩托车,失魂落魄地,回到并不缤纷的某间彩色屋子。
一推门,外婆呆滞地守在窗前,向远方抛出一道绵长目光。
桌上剩下的饭菜还摆在原来的位置。那个背影揪了介之初的心一下,他拍拍手掌的灰,边收拾着碗筷,边念念叨叨。
“多老的人了,家务也不知道做,唉。”
“回来了,”沉思中的外婆明显有几分慌促,扭过头来,连忙拉直脸上的皱纹,换上一副略微得意的精神笑容:“留着给你锻炼锻炼呢。”
“真谢谢您了,这么照顾我呀!”
“唷,瞧我这记性,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吧?”外婆表现出一种意料之中的恍然大悟,扶起额头嘀咕着,弯腰就在菜篮子里一阵东翻西找。
“过生日咦,要给臭小子煮个鸡蛋,越长大越不听话……”
“哎老太太,你老糊涂啦,要煮也晚点再煮吧,”介之初拿起抹布,背过身去擦着桌子,看不清什么表情:“再说,我也不喜欢吃鸡蛋。”
“鸡蛋营养高着呢……”
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天,平常却是特殊的一天。恍惚飘过。
天色彻底暗了下去,介之初放轻脚步溜出了门,踩着那几道锈迹斑斑的铁架楼梯,爬上了挂满星星的天台。
这里长满了繁盛的孤独。风不会从耳边划过,而是贴着脸颊说起悄悄话,不肯离开。
就像介之初的世界,永远都是蓝色的。
他和往常一样,抬脚步入只属于他自己的这方天地,潇洒如是。
双手插兜,仰头漫不经心地瞥了瞥天空,眨眨眼,将视线揉软,险些溢出丢人的落寞。
鞋底在泛青的水泥板面上毫无章法地摩擦了几下,挪到天台边沿,双手托腮,目光再次迷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但杂乱的思绪并没有陷入困境。而是四处蔓延,蛊惑着脑海构筑出一幅幅虚妄的可怕画面。
更可怕的是,也同时牵扯出了虚妄背后那露出了一点点马脚的真实。
当介之初意识到这一点时,他骇然失色。
这个夏夜的晚风变得异常冷冽。如利刃剜肤。
咬紧牙根拔回视线焦点的同一瞬间,一双手悄无声息地,从身后拍了左肩一掌,吓得他魂不附体。
“我去,闹鬼啊!”一声长嚎,腿打着颤栗连退了好几步,才敢回头扯开半条眼缝。
定睛一看,顾一和反背着一只手,另一只困惑地僵在半空。
介之初莫名感受到一份突如其来的尴尬,干咳了几嗓子,故作镇定状挺直腰板:“干嘛呢,魂都差点被你吓跑了,还好我胆大!”
“叫你了,都没反应,”顾一和愣了愣,噗嗤一下,笑得空前绝后:“我看看,吓尿了没哈哈哈……”
介之初恼羞成怒,抬脚踢出那招对决过无数回合的飞毛腿,顾一和顺势转身,轻松躲过。
下一秒,藏在背后的那个纸盒从右手掌心划出一道弧线,飞了出去。
诡异地摔出了一盏白色台灯。
顾一和连忙扑上去,捡起心疼万分地抱在怀里。
“怎么,你近视这么严重了啊,还点着灯才看得见路?”
“还好没摔坏。”
“哟,用来追女孩子的?”
话音未落,顾一和摇摇头踢开那个本来精心装扮过纸盒,神色颇有些失望地递给了他:“喏,给你的生日礼物。”
“本来想整点仪式感的,谁知道被你一脚给踢出来了……”
看着顾一和撅起嘴委屈巴巴的样子,介之初心里一时过意不去,摊开两只手掌,摆出一副深表遗憾的神情:“要不,你重来一遍?”
“滚。”
“就算出场方式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不过,哥哥我还是挺感动的,感动坏了!”他接过那盏貌不惊人的台灯,上气不接下气地哽咽着,差点洋葱就涕泗横流。
转身扭过头去,眼角一斜,碎碎念道:“这台灯有什么用,还不如直接给点钱……”
“你说啥?”
“好台灯,好兄弟,没齿难忘!”
顾一和环抱双手,傲娇地点了点头。心底却不免想着,要是有一天介之初知道,其实这盏台灯是自己买来感觉不太喜欢,转念一琢磨,索性就送给他当礼物,并打算以此为借口重新买一盏更心仪的台灯时,不知道他会有多崩溃。
想着想着,他笑了出来。
也许介之初更加嫌弃那盏台灯的同时,会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口气,悔恨地大喊,原来顾一和这小王八蛋一点都不蠢。
想想就开心。就在介之初皱起眉凑过头来,纳闷着顾一和为什么又没由来地傻笑时,楼下传来了外婆极具穿透力的声音。
“臭小子,鸡蛋要凉了!”
两人如临大敌,麻溜地爬下天台,顾一和见势不妙转身想逃,被介之初捉小鸡般一把逮住,拖进了屋里。
“一和你也在啊,来来,尝两个生日鸡蛋。”
这一晚,介之初的十六岁生日,以两人翻着白眼慢嚼细咽,艰难噎下外婆飞快剥完的十几个白鸡蛋而告终。怎一个惨字了得。
拍着胸口摸黑离开之前,顾一和在那层透明的夜色里,被半个蛋黄卡在喉咙,终究还是没对介之初说出那句“别担心,一切肯定会好起来的。”
他宽宏大量地安慰自己,“还好没说,怪怪的,有点肉麻。”
入睡之前,介之初看了看摆在桌角的那盏发出微微光亮的台灯,轻轻按灭开关,想着等顾一和真的搬走时,一定要好好道别。
一场久违的香甜的未知的疯狂的梦,随之而来。第二天掀起被子,拉开窗帘,正午的阳光异常刺眼。
外婆说,顾一和来过,走了。
把所有家具和整个童年一齐搬离景间镇。
介之初跑出门时,甚至没有发现,外婆整张脸溢满藏不住的忧心忡忡。
他只是在想,顾一和那个一根筋,肯定觉得自己没心没肺的睡得那么死,根本就什么都不在乎。
失落与惭愧交相侵蚀之下,关于父母的忧惧一同席卷而来,织成一张大网,铺天盖地。
失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突然消散,一种是一步一步,眼看着从身边走远。介之初在他十六岁的第一天都经历过了。
他束手无策。
“外婆,我爸妈是不是死在海里了?”
说出口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他不停告诉自己,不可能的,就是雨大了点,来不了就回去了而已。
并坚信到底。装作看不见外婆眼里的绝望和掩藏绝望的苍白无力。
“瞎说什么呢,你这孩子……”
从那之后,介之初扫去了心里那份无端的臆想,当作什么事儿也发生,还像以前一样吊儿郎当四处逛荡,不时和外婆斗嘴。
只是好多个深夜,他都孤零零地趴在天台上,眼神涣散。抬头看天,数星星,对着港湾前那座很多年也没有亮起过的灯塔发呆。
循环往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下去,一天比一天没意思。
那段时间,消沉的思绪如同一团团杂乱的黑色线条,紧紧缠绕在脑海里,搅得他常常失眠。
而有时一闭眼,各种怪诞画面和成片成片的阴影就扑了过来,回旋盘踞,将他整个身子吞噬殆尽。像梦,又不是梦。
心情总是很糟糕,提不起精神,对什么都没了兴趣,包括那辆旧摩托。
外婆时而敷衍时而夸张地笑着,像以前一样贬损自己时,介之初也再没有反驳过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很没出息,一无是处那种。
他把自己困在一只密封的笼子里,彻底陷入了忧伤这滩泥潭。
一点儿也没挣扎。
看厌了一成不变的星星,这场梦也该做到尽头了。
介之初想要最后再做一遍那些以前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绕着小镇边缘最长的那条公路狂奔,比如在大海里游泳,比如骑摩托。
于是他挑了一个阳光热烈的午后,重新骑着鼓捣过被冷落了许久的摩托,以景间镇为中心转圈,再拧紧油门冲进大海里,游泳。
出门之后,介之初特意返回去取了一把伞,一把透明雨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担心下雨吧。
今天没下,明天也会下的。
他有预感,自己这一次应该要游很久。
孤独地飞驰在那条烟尘俱灭的公路上,阳光毒辣,晃得他睁不开眼。绕完了两圈,心潮平静地冲向大海那个方向时,他灵机一动,并不熟练地腾出左手来,撑起了那把雨伞。
滚烫密集的金色光线立马就被隔得老远,似乎连地上影子的上半身也变得透明,凉快极了。
摇摇晃晃地骑到那片海滩前,介之初左右环视,随意一瞥,看见前面几米之外闪过一道陌生身影。
他不禁好奇地想,景间什么时候来了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仔细再想,难道眼花了?
抬眼再看去,手一抖,摩托车轮拐着一条歪歪扭扭的轨迹线,眼看就要撞上了那条单薄的浅蓝色长裙。
危急时刻,介之初没记得扔下手里的伞,单手使劲一拽,连人带车倒在了路边。算是躲开了,但没拉住甩飞的车尾,还是碰到了裙摆,带过一串黑烟。
女孩吓了一跳。不是惊吓,是那种被打破了沉思的突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