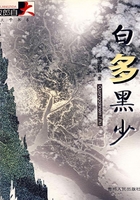我又接到了娘的电话。娘说:小影儿啊,你快回来吧,你爸得的是尿毒症,晚期。
那天,我游走在街上,因为接到娘的电话,我让我的双腿得到了休息,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站在了张大姐面前,我说:你知道我和宁老师的感情,你也对我不薄,可不可以借我些钱,给我爸换肾。
张大姐说:如果宁老师在,我可以借你,可惜他不在了。他在他是我的主心骨,他不在别人是我的主心骨。如果他是我的主心骨我可以借你,而另一个主心骨和你没什么感情,所以我不能借你。再说,宁老师的死,和你有关,你要是不和他打什么麻将……
这时,张大姐眼里含着泪,接着化成了愤怒,直视我的眼睛让我退缩着。
现在,老宁的死已经全是因为我。先是张大姐这么认为,接着其他老师也这么认为。他们说,如果我不勾搭宁老师打麻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来。现在,我也这么认为,如果他不天天打麻将,小胡与张大姐的事就可能不会发生;如果他们的事不发生,宁老师就不会砍小胡,也不会输掉他所有的钱。
老宁的死还有其他避免的可能,如:老宁的爹妈如果没生过他,或者小胡根本不存在,抑或是我不存在。当然,这些解释都比较牵强。
现在,老宁就是我害的。张大姐愿意这么认为,张大姐的朋友们愿意这么认为,我在学校基本没有什么朋友,有一个已经死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事实。
最终,我逃跑了。逃跑时,张大姐的愤怒化成了四个字:什么东西。
我逃到了校长室。
推开校长室的瞬间,校长正笑咪咪地望着我。
校长说:你的事以前有人跟我提过,最近你们教研室出了不少事,少了两个教学编。按常理讲对你应该照顾,毕竟是本校的学生……
我抽出一支现买的玉溪递了上去。
校长摆了摆手,从桌上摸出一盒软中华,抽出一支,把烟咀在水杯里醮了醮,吹了两口点上。他说:可是,听老师们反映你老也不按时上班,最近还经常请假。你说这样给你个教学编,大伙也不能服啊。你的事儿得开党组会的时候研究一下……
我说我不是要这个,我是想借钱。借二十万,给我爸换肾。
“二十万?”现在,校长又转移了话题。“你爸得的什么病?”
“尿毒症!”
“你爸不是本院教职工,借出去没法儿说。”
“那别人怎么能?”
“别人……”
“校长……那是救命钱……”
校长站了起来,“你去下财务处,先找孙处长说下情况,然后让他打个报告给我,拿到党组研究!”
我低着头,含着泪,感谢着领导的关怀,感谢着校长笑盈盈地将我送出门。我轻轻把门带上,弯腰系踢开的鞋带。门里传来阴声阴气的声音:孙处长啊,一会儿体育教研室有个老师要去你那儿借钱,咱这情况你也知道,最近钱打不开点儿,这口儿再开是不是不好?还有,老师对他反映也不好……
我缓慢地站起,再一次推开校长室的门。校长刚放下电话,和蔼地望着我:“怎么回来了?快找孙处长说去,要下班了。”
我脸上的泪还没有干,我跪在了地上,我的膝盖砸在了地板上。
“校长,那是救命钱……”
校长已经站起,他没有扶我,而是拎起衣架上的风衣,径直推开了门。他的腿迈出房间的瞬间,我回身抱住。
“别这样儿,我还有事,你找孙处长说去!”
我的手被踢开,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跌撞着站起,蹒跚着走出房间,又疯了般向脚步声冲了出去,大吼着:“为什么别人能帮,我不能帮?”
没有人理我。
“为什么别人能帮,我不能帮?”
没有人理我。
“为什么别人能帮,我不能帮?”我向楼梯吼着。
没有人理我。
“校长,你给我说!”
现在,有人理我了,楼道里传来阴声阴气的声音:“因为你不像老师!”
我又坐在了地上。接着,我又站起,狠狠踢向走廊窗子上的玻璃。“老子不干了!老子不他妈受你管了!”
我吼着,随着爆破声,我追逐着。
办公楼外,我被人拦下。
校长送了我四个字:“什么东西!”接着狠狠地摔上了车门。
我离开了学校,走在街上,我的心里没有了锣音,只有愤怒。愤怒又产生了力量,那歌声再次在我心里响起: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我擦干了脸上的泪痕,心里刻着愤怒与自信。
现在,我的手在空气中甩了甩,掏出老宁送的手机,给蒋艳打了过去。
蒋艳说有事?我说有,你在哪儿?在家!问清了地址,我说你等着!蒋艳说有事电话里说。我说不行,你等着!
我挺直了胸,坐上一辆出租车。我想,此刻我的脸只能用坚毅两个字形容。
我打电话给张大姐,我说,骚老娘们儿,我不在学校干了!接着我挂断,又打给王宇,我说,我不在学校干了!接着,我关了机。
我大踏步走进蒋艳的高级公寓,敲开蒋艳的门。现在,蒋艳就站在我的对面,一件宽松的睡袍遮着她丰盈的身体。我板着脸弯腰摆正褪下的鞋,洒脱地站直身体,绕过一脸茫然的蒋艳,坐在了沙发上。
“有事?”
“有!”我拿起茶几上的空杯,自己接了杯水,猛然一口干掉,接着又倒了一杯。“蒋艳,你坐过来!”
“哈,你又中奖啦?”
“你坐过来!”我压抑着想吐的冲动。
蒋艳勉强地坐在我旁边。
我又喝了口水:“蒋艳,我郑重地和你说,我想娶你!”
“娶我?”
“对!我不在学校呆了,我想和你出来做生意!”
“做生意?”蒋艳的眉毛竖了起来。
“对!这次我不骗你!我是认真的!”
“叶……呵呵……叶明影……哈哈哈,你笑死我啦!”蒋艳狠狠地拍了下大腿,“你怎么这么愁人啊?”
“别笑,我是和你说正经的!”我依旧板着脸。
蒋艳的手又赏了大腿一个巴掌,“哈哈哈……哈哈哈……叶明影,你咋那能开玩笑呢?你真有病……。”
“你笑啥?我和你说正经的呢!”我的眉毛也立了起来。
蒋艳继续笑着,前仰后合:“叶明影,哈哈哈,我有男朋友啦啊!”
“什么?谁?”
蒋艳站了起来,扭动着腰肢,头不停在空气中甩着。“哈哈哈,全来啊……”
“什么?他能跟你?”
蒋艳不笑了:“叶明影,你说啥呢?”
“他能……跟你吗?”
“全来啊,咱同学来啦。”蒋艳大咧咧地喊着,接着回身敲了敲卧室的门。
门开了,卧室里走出只穿一条短裤,打着哈欠的赵全来。“明影啊,来了啊。要不干了啊?不干也好,当个老师有啥出息?对,你得做生意,做生意好啊,你那脑袋冲,干啥都能行,要不咱俩合股干点啥?对了,你不是写书写得好吗,当作家也不错啊……”
我站了起来。
“别客气,坐坐坐!”赵全来行使着主人的热情。
我没有坐下,奔向了鞋。我弯着腰,用力地弯腰,尽量让脸靠近地面。这个过程很长,我好像很久都没有穿上鞋,我穿了很久,在提上第二只鞋的瞬间,挤出了这样几个字:“我爸病了,急需要钱。”
“啥病?”
“尿毒症……”
“啊?透析就行吧?不对,重的得换肾,这可不少钱啊……”赵全来叹了口气,“明影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到学校去借,学校这事儿能帮的,再说,估计你这为人,和学校领导也能混得不错……”
“学校不借……”
“刚才他说过不在学校干了嘛!”蒋艳帮我否定着赵全来的提议,“那……你找朋友借借……”蒋艳的声音。
我的眼睛仍看着地面,摇了摇头:“我没有什么朋友……”
“唉——男人要是连爹妈都救不了,最可悲了……真够难为你的……”赵全来同情着我。
我的泪水涌出,现在,我穿好鞋了。我站起,依旧低着头,缓慢地下了楼。
楼上窗子传来赵全来的喊声:“明影啊,我再给你出个主意,你把你的肾换给你爸,这种血缘关系的成活率高……”
我对着地面,轻声说了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