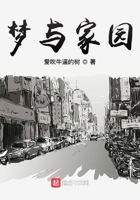萧容翻身下床自己穿上衣服,又默默无言的将滑落在地的衣衫递与云妨。她强忍身子的不适,平静的着好衣衫。
萧容背对着她,忍不住回首道:“可你昨夜分明为他人所害,我定要查出是谁。”
云妨系好衣带,拂了拂宽大的水袖,冷然颔首道:“殿下不必费心查了。我心中早有答案是何人害我。”
在还未见到陈景州时,她就已经了然于心了。
萧容眉眼一沉:“是谁!敢下这样卑劣的手段。”
云妨自然是恨的,她也不打算替二房兜着,屈膝一礼,道:“昨日午间,我二婶母忽然着人来请,说是酿了我最爱吃的梅花糕,要我去一趟她的别苑。”
她顿了顿,萧容脸色一沉,挑眉问:“所以?你当真去了?”
云妨自嘲的笑笑,点头道:“是我轻敌了,原想着在府中,她们应该不至于会动什么手脚。却没想,原是我活得太碍眼。令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
萧容不理她的自负之言,双眸狠戾一瞪,道:“罪便是罪,从不问缘由。待证据确凿之日,我必取了她们首级!”
只要想到昨夜陈景州看着云妨痴迷的模样,他内心里的野兽就开始狂啸。一切都太万幸,要不是他去得及时,许多事恐怕都再扭转不回。
云妨答应他回到姜府就着手去查,欲走时,萧容又道:“昨夜的事,我不会说出去。只要你不愿想起,我也不会再提。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吧。”
她转过去的身子一僵,“我也不会对殿下做出恩将仇报之事。”
萧容强忍心中不舍的痛楚,命粉衣和紫衣将云妨好好送回姜府。他则亲自去了一趟侯府。
却是老侯爷出来相见。“殿下这连日来找景儿,可是有什么要事?”
萧容现在一想起陈景州昨夜的模样,心里就团起一股愤怒的火焰,可是老侯爷年事已高,且不知情,他只好强忍怒意搪塞道:“无甚大事,舅舅宽心罢。”
下人及时来回禀,说小侯爷昨夜彻夜未归。
老侯爷喝退下人,严肃道:“这小崽子!快要娶妻的人,怎还如此不知检点!当真失礼!”
老侯爷是太后的亲兄长,自小萧容便知道,这个舅舅年轻时也是个十分严厉之人。
知道事情真相的也只萧容一个,而眼下,他是不会说的。
于是起身告了辞,可刚出了前厅,就见陈景州一脸憔悴的走了过来,在抬眼瞧见萧容的一刹,脸色更显苍白。
“你这家伙,夜不归家,跑到哪里去了!”萧容还未开口,老侯爷就指着他呵斥道。
陈景州还未彻底醒神,便讷讷不知该如何开口,萧容淡然道:“舅舅息怒。我同景州谈会儿吧。”看了看陈景州,又道,“咱们到你书房去说。”
老侯爷素喜檀香,陈景州便耳濡目染也跟着爱上。
于是书香气息极浓的书房里,檀香的气味沁人心脾。而此刻,没有人的心里是平静的。
“从小我便知道你,不是这样轻浮的人。说说吧,是怎么回事。”萧容也毫不客气,背着手便开门见山道。
陈景州颓颓的寻了把最近自己的椅子乏乏坐下,眼下的两团乌青十分明显。“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表哥若要到皇上面前告发我,那我也只能悉听尊便了。”
他倒是想得开,连解释都懒得了。
萧容心里也清楚,他和云妨两个人都是被人陷害的,那人是想顺水推舟真的促成这两人的好事。
然而他气就气在,陈景州居然也不深思熟虑一番,这么轻易便落入圈套。
“你以为你这样破罐破摔,我就能饶过你?云妨是被人陷害的,你会不知道?”萧容眉间一拧,语气更显深沉。
一听到那个名字,陈景州空洞的双眼才稍微有了点弱光,“被害的?是谁,是谁要害她?!”
萧容冷笑:“你且说昨夜是谁要你去那鬼地方的,不就知道了。”
陈景州眼中弥漫出困惑:“昨夜?是云妨递来书信,约我前去的啊!否则我又怎会这么爽快赴约呢!”
“那又是谁让你喝下的春酒!”萧容胸口一痛,低吼道。
陈景州噌的站起身:“是那妈妈说云妨设下了门槛儿,要先喝一壶酒以表诚意,方可上楼相会!”
萧容愣怔片刻,忽然凶神恶煞上前拽起陈景州衣襟,咬牙道:“你个痴儿!云妨为人如何你难道不清楚?!她怎么会约你到那烟花酒巷相会!又怎会想出这些低俗的法子!你连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清楚,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要娶她!”
陈景州涣散的双眼瞬间聚了光,他第一次动手推开萧容。“是,我没资格。如今犯下这样卑鄙的罪,我连仰慕她的资格都没有了!但你呢,就快做别人的夫婿了,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我!”
表兄弟两人彻底争红了眼。
“但我至少了解她。而你只是青睐她的皮相,根本不知道她要的是什么。”两厢冷静了半晌后,萧容平静道。
陈景州再次跌坐回椅子上,扶着前额,似已然疲累到虚脱:“是,你说的都对。你走吧。明日我自会去皇上面前请罪,错责我也一并都揽了。反正到最后,云妨也不会嫁给我的,从头到尾不过是一出戏罢了。”
他声音逐渐低沉,含带了许多无奈和失落。
萧容睨着他,“此言何意。”
陈景州却仿佛不想再多说,“你亲自去问她吧。”
出了侯府,萧容直奔昨夜的那家青楼。白日里的生意,比昨夜的都好。妈妈眼尖的发现了萧容,想上前又不敢,只好唤了一个姑娘上来招呼。
萧容却掐住那女子的脖子往上一提道:“把这的老板娘叫出来!”
那姑娘从没见过好看的人发这样大的火,也被吓了一跳。瞪着圆眼就去找老鸨。
很快,老鸨佯装轻松的挥着帕子招呼了过来:“哎哟,这位爷,今日可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