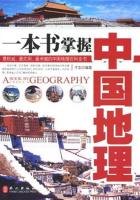二月,寒冬过去,春意渐渐萌芽,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柳树开始抽出碧绿的嫩芽,不时有流莺掠过细嫩的枝芽,留下一连串清灵的叫声。
就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一道战报八百里加急送入姑苏城——齐国来袭!
齐国这一代的君王乃是齐景公,幼年登基,在位五十余年,一直致力于壮大齐国,力图光复齐恒公的霸业, 称霸中原。
多年来,齐景公一直在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调转枪头来进攻吴国。
战报传来的时候,齐国已经越过边境,直指吴都姑苏,情况极为危极,齐国乃是大国,国盛兵强,远非当初的越国所能相提并论;夫差不敢托大,立刻召伍子胥与伯嚭等人入朝议事。
就在议事之时,又一封战报送入朝堂,其内容令夫差心头更加沉重,据战报所奏,边境吴军仓促应战,准备不足且士气低落,遭到了惨败,死伤无数。
“大王。”在一番沉寂后,伍子胥率先站出来,”老臣愿领兵出战,挡齐国虎狼之军。”
夫差颔首道:“相父用兵如神,军纪严明,自是这次领兵的最好人选。”
“大王过奖,老臣虽略有能力,但最关键的还是将士们的士气,士气振则无往不利,以一挡十;士气不振则诸事不顺,到时候老臣纵有三头六臂亦无济于事;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将士们的士气。”
夫差深以为然地道:“相父所言甚是,不知相父可有什么提升三军士气的法子?还是说……相父希望本王亲征?”
“大王乃是万乘之尊,岂可轻易冒险。”伍子胥连连摇头,随即道:“老臣倒有一个提升士气的法子,只是不知大王是否愿意一用。”
夫差不假思索地道:“但能提升士气,本王自然愿意。”
伍子胥正要开口,一直冷眼旁观的伯嚭突然道:“相国大人所言的办法,该不会是指处死越王勾践吧?”
见心事被道破,伍子胥也不否认,仰头道:“大王久居宫中,不知军营之事,将士们一直对大王不杀勾践一事有所不解;想当初好不容易打下越国,眼瞅着就可以将越国并入版图之中,开拓我吴国霸业的第一步,可大王却听信小人馋言,既不杀勾践,也不全面接收越国,实在是寒了将士们的心。”
伯嚭皮笑肉不笑地道:“这可是巧了,我前些日子也刚去过军营,将士们都在称颂大王宽宏仁和,乃是有德之君,与相国所言恰恰相反;不知是我与相国遇到的士兵不是同一拨,还是有人借题发挥,颠倒黑白?”
伍子胥冰冷肃杀的目光漫过伯嚭,“你这是在指责老夫?”
伯嚭笑意不减地道:“我只是实话实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相国自己清楚。”
伍子胥冷哼一声,朝夫差拱手道:“大王,不杀勾践,士兵不气,士气不振,恐怕难抵齐国大军,还请大王立刻做出决断。”
“大王!”伯嚭不甘示弱地道:“正因为齐来袭,所以才更不能杀勾践。”
“哦?”夫差饶有兴趣地道:“这是为何?”
“不杀勾践,则越国上下感恩于大王,可助我们共同抵御齐国大军;可若是杀了勾践,恩就变成了仇;若换了平日也就罢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是齐国来袭之际,一旦与越国反目,吴国就会腹背受敌,置身于水火之中!”伯嚭一口气说完这些,犹不罢休,厉声道:“听着相国刚才那番言语,我真是怀疑,相国究竟是真为吴国着想,还是想毁了吴国毁了大王!”
“放肆!”伍子胥气得浑身发抖,须发皆张,若此时他手中有一把刀,必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伯嚭,“老夫对吴国对大王忠心耿耿,你这个卑鄙小人竟敢如此诬蔑老夫,实在该死!”
“真心还是假意,相国心里最清楚。”伯嚭知道刚才那番话得罪死了伍子胥,但他与伍子胥早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又何惧再多一些。
“哼!”伍子胥狠狠瞪了他一眼,对从刚才起就没怎么说话的夫差道:“大王,老臣愿意拿项上人头保证,只要勾践一死,老臣一定击退齐国,保我吴国安稳!”
听到这话,夫差眉头微微一皱,伯嚭最擅察言观色,当即指着伍子胥道:“你这是在威胁大王!”顿一顿,他又冷笑道:“若吴国与大王真出了什么差池,你伍相就算有十颗百颗脑袋也不够砍的!”
伍子胥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论口舌之利,自己不是伯嚭的对手,故而也不争这一言长短,只与夫差道:“请大王立刻下令!”
夫差原本虽然倾向伯嚭,但还在犹豫,毕竟伍子胥说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可伍子胥这番强势的言语,顿时激起了他的逆反之心,将他心中的天平彻底逼向了伯嚭那边。
这些年来,他被伍子胥管得太多了,从行军打仗到治国之政,乃至于自己的终身大事,伍子胥都要插上一脚,实在令他反感;若非在立后一事上,他执意不允,恐怕这会儿伍榕已经成了吴国的王后。
见夫差久久不说话,伍子胥不悦地催促道:“大王……”
“好了。”夫差打断他的话,沉声道:“本王仔细考虑过了,太宰说得确有道理,此刻杀了勾践,等于是将越国置于敌对之地,万一齐越两国联手,对我吴国大大不利,所以……勾践不能杀。”
夫差既考虑到伯嚭所说的话,也考虑到越国是夷光故国,多方权衡之下,方才做出这个决定。
伍子胥并未意识到自己无形中犯下错,看到夫差站在伯嚭那一边大为生气,“小人误国,大王怎可听信小人之言,勾践必须得杀!”
夫差徐徐转着右手拇指上的玉扳指,不知在想什么,在伍子胥又一次催促后,他淡然道:“若勾践死后,越国如太宰所言的起兵造反,甚至与齐国勾结,该当如何?”
“老臣绝不会允许他们伤吴国一分一毫!”伍子胥的毫言壮志只引来夫差一声轻笑,“有雄心是好事,可也得量力而为,凭相父一人之力,如何抵挡两国军队?哪怕勉强让你挡住,也必定伤亡惨重,反而给了别国趁虚而入的机会。”
伍子胥被他说得无言以对,但还是不肯罢休,“可是……”
“好了。”夫差不耐烦地道:“此事到此为止,相父回去好好操练士兵,随时准备迎击齐军。”说罢,他大袖一挥,“退朝”。
公孙离正等在府中,看到伍子胥怒气冲冲地回来,小心翼翼地问道:“相国大人何以生这么大的气,难道大王不同意您领兵?”
提到夫差,伍子胥既生气又痛心,“大王现在越来越糊涂了,再这样下去,吴国早晚败在他手里。”说着,他将朝中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公孙离听完之后,也是愤愤不平,“伯嚭小人,整日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懂得行军打仗,否则上次怎么会在越国惨败逃窜,也不知大王受了什么蛊惑,竟然这般听信他的话。”
伍子胥冷声道:“大王糊涂,老夫可不能跟着糊涂,否则怎么对得起先王的托付。”
公孙离为难地道:“可是大王心意已决,想再回心转意,怕是很难了。”
“不管怎么说,老夫都不能坐视大王犯糊涂事。”伍子胥沉声道:“趁这几日还在召集兵马,好生想一想,看有没有什么法子让大王悬崖勒马。”
“是。”公孙离恭声答应。
第二日,公孙离匆匆赶来相国府,与伍子胥一阵密谈之后,离开后,公孙离悄悄来到关押着死囚犯的大牢之中,逗留许久方才离开;至于他谈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没人知道。
当天夜里,城中好几户宅屋遭到破坏,甚至有人受伤,据受伤的人称,那些人手臂上都有一个刺青,是一个“越”字。
夫差得知后,命人搜捕,结果在一间破屋中找到了他们,果然如伤者所说,手臂上都有一个“越”字,经过审问,他们也都承认自己越人;之后,更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一封齐国的书信,据信中所言,越国与齐国早已经勾结在一起,只等齐国军队抵达姑苏之后,越国就会起兵攻击吴国后背部,形成两边夹攻之势。
夷光替太王太后诊完脉回来,看到夫差正拿着书信出神,走到他身后,力道适中地替他按着僵硬的肩膀。
夫差醒过神来,握一握夷光的手道:“回来了。”
“嗯。”夷光柔声道:“大王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
夫差没说什么,只是将信递给了她,“你瞧瞧。”
待得看完信后,夷光道:“大王信吗?”
“本王不知道,你呢?”夫差摇头,在夷光面前,他不需要隐瞒什么。
夷光似笑非笑地道:“我是越人,大王就不怕我会偏着越国吗?”
“本王相信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深刻的信任,令夷光心中一暖,轻声道:“我不敢说一定是假的,但确有几分可疑。”
夫差饶有兴趣地道:“何以见得?”
“大王前日刚说了不杀越王,昨日就突然出了这样的事情,大王不觉得太过巧合了吗?还有,我记得昨夜没有月亮,天色那么黑,那些被袭击的百姓怎么就能清楚看到他们手上的’越’字呢?”
夫差若有所思地道:“你是说……这一切都是有人刻意安排的?”
夷光欲言又止,夫差看到她这样,道:“此处没有别人,你有什么话只管说。”
“嗯。”夷光轻轻点了点头,道:“若是可以,我想见一见那几名被抓到的’越人’。”
“好。”夫差当即点头答应,带着夷光微服出宫来到关押那些人的牢中,总共有五人,身形或高大或短瘦,不尽相同。
狱卒喝令他们抬起右手,果然手臂上都刺着一个“越”字,夷光隔着牢门道:“你们是哪里人氏,为何要与齐国勾结?又是谁派你们来的?”
那几人只是看了夷光一眼便又别过头去,一个字也没说,夷光也不生气,只是命狱卒打开牢门。
狱卒为难地道:“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虽然加了手铐脚铐,但还是凶悍得很,冒然打开,恐怕会对姑娘不利。”
夷光将目光投向夫差,后者道:“本王在,护卫也在,他们翻不出风浪来,你只管开就是了。”
见夫差也这么说,狱卒只得掏出钥匙开了门,别看夫差虽然话说得轻松,实际却是十分紧张,紧紧跟在夷光身边,寸步不离。
夷光盯了那五人片刻,忽地道:“你们不是越人。”
听到这话,五人面色皆是变了一下,虽然很快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并未逃过夷光的眼睛。
夷光扫了一眼他们露在袖子外的刺青,对狱卒道:“去打一盆水来。”
“是。”狱卒动作倒快,不一会儿功夫便打来了一盆干净的水,夷光自袖中取出一个手指头大小的瓶子,倒了一些白色的粉末在里面,待得化开后,她道:“把这水抹在他们的刺青上。”
那五人神情一变,戴在手上的手铐发出轻微的响动,看向夷光的眼里多了一丝悍意。
夫差将这一切瞧在眼里,朝身后的几名护卫使了个眼色,护卫会意,拔出腰间俩刀横在那几人颈间。原本蠢蠢欲动的几人感觉到颈间的森寒,顿时安静了下来,不敢再有妄动。
随着狱卒将水抹在那五人的刺青之下,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原本清晰的刺青渐渐变得模糊,到最后完全消失,只化做一滩青色的汁液。
别说狱卒,就连夫差也看得目瞪口呆,“怎么会这样?”
夷光淡淡一笑,“这是千年沉香树的树汁,凿取之后加以特殊的药物,就会变成青色,抹在身上水洗不去,经久不褪,犹如刺青一般。”
听到这里,夫差哪还会不明白,这五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勾结齐国的越人,而是刻意假扮,借此挑起吴越两国之间的纷争,“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