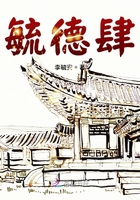待他说完,哈赤塔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挂在脸上,像是万分心寒,又像是难以置信,又像是彷徨无奈。乌木丁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在千变万化,像是戏台子上的变脸一般,正要开口说话。不料哈赤塔抬了下手,示意他不要出声。
乌木丁只好缄默,干坐在对面。桌子上的油灯灯芯歪了,乌木丁找到一根细竹条轻轻挑了挑,灯焰变大,屋子里又亮堂了许多。对坐的哈赤塔像是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好一阵子,他的目光才缓缓转移到手中的信纸上。目光刚刚落到了信纸上,立时大吃一惊!因为他在清洗名单上的头一行头一个,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状元街西头的仙雅客栈内,苏沫茶一人坐在一间客房里的床头,神色倦怠。门被推开,穆硕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托盘里放着两样小菜和一碗白米饭,还有一碗清汤,端到了她面前。
苏沫茶口中吐出了几个字:“我吃不下。”穆硕轻叹了一声,将托盘放到圆桌上,也坐到了床头轻轻地拥她入怀。苏沫茶幽怨地道:“你是没进牢房里看到,我二姐一个好好的美人,遭受了‘炮烙之刑’,已经成了一个废人。而今连站都站不稳了。就算我能够将她救出来,她还有意志活下去吗?”
穆硕叹道:“小茶,估计你救不出她了。”苏沫茶疑惑地抬头望着他。穆硕道:“我已收到可靠消息,八爷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兵部左侍郎揆叙、礼部郎中王鸿绪、大理寺少卿马尔齐哈等三人已经被劝服,准备反水揭发胤禩、胤禟的罪行。这三人都是八爷党集团的心腹要员,肯定知道不少机密之事。只要他们的折子一上达天听,胤禩、胤禟还能不倒台吗?你二姐揭不揭发已经不重要了。”
苏沫茶残存的最后一丝营救紫蝶的希望也随之破灭,说道:“我二姐就是太傻,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都告诉她了,九皇子在派人刺杀她,可是她仍然无动于衷。竟然还求我设法让九皇子去牢房里见她最后一面。”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穆硕叹息道,“你二姐这么好的一个人,堪称才貌双全,可惜遇人不淑。偏偏爱上了人称‘毒蛇’的九皇子,迟早会被这条毒蛇咬一口的。”苏沫茶一想到二姐现今的遭遇,忍不住落泪道:“看我二姐现在的情形,估计也没有几日活头了。昨儿我见到了九皇子,跟他提了二姐想见他的事。他只说了‘本贝子爷没空’几个字,随后扭头就走了。你说得对,我二姐真是遇人不淑。她都快要死了,他却连见一面都不肯。没想到恋人之间竟然可以绝情到这种地步?”
穆硕哼哼一声,道:“这位九皇子还迷糊得很呢。他现在正全力自保,指望着皇上念在兄弟手足的份儿上,可以放过他一马。他自然不肯去天牢里看一名罪犯了,免得又落人口实。倒是听说廉亲王已经看开,如今已经不理朝事,在府中等着屠刀落下的那一刻了。”
二人陷入了沉默之中。穆硕伸手轻轻抚着她的小腹部位,关切地道:“小茶,你现在是有身孕之人,万不可为这些事动了胎气。你要知道有些事你我都无能为力。而今主子正在全力料理年羹尧的事,我也不能在关键时刻请辞。等年羹尧一倒台,到时候主子必然很高兴,我就趁势说我俩的事。然后我们就离开这座紫禁城,远走高飞。”
苏沫茶望了他一眼,问道:“倒年的事很快会有结果吗?”穆硕点头道:“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主子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京城后,主子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了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不法’的种种罪行。主子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如此年羹尧岂非凌驾于朝廷之上?’因此,主子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反而升任他做了左都御史。这个蔡珽自然感恩戴德,如今已经成为朝中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干将。一大批‘倒年’的官员聚拢到了他身边。你看吧,不出两个月,这位年大将军必然轰然倒台。”
堂堂威震西北的年大将军如今落到了如此尴尬的境地,不免令人唏嘘。苏沫茶忧虑道:“我们的事你要从速办理。眼看着主子处理政敌和这些有功之臣,已经杀红了眼。我看着都心惊肉跳的。再不走,只怕祸事就降临到我们身上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穆硕叹息了一声,道,“没有主子的点头,就算走到了天涯海角,依然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少时,穆硕起身端来一碗甜汤,坐到她身旁道:“来吧,好歹吃几口。就算你不饿,你肚子里的小东西还饿着呢。”苏沫茶点了下头。甜汤里是珍珠大小的糯米丸子,还有糟水,上面漂着一层鸡蛋花。穆硕用勺子舀着一勺一勺送到她嘴边,苏沫茶张嘴吃了下去。穆硕哄着道:“这就对了。无论遇到什么烦心事,饭还是要吃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嘛。”吃了七八口,穆硕再舀起一勺送过去时,苏沫茶就摇了头,不想再吃了。
穆硕将剩下的几勺甜汤吃了,故意道:“你还别说,味道做的不错。甜而不腻,糯米丸子滑溜溜的。”苏沫茶取出手帕擦了擦嘴,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担忧地道:“近来不知怎么的,在宫里总是睡不好觉,常常到半夜里不自觉地就惊醒了。总是梦见一大群凶神恶煞的侍卫手持血淋淋的钢刀向我冲了过来。这可是凶兆啊!”穆硕也只能拿言语宽慰她:“小茶,你想多了。听说有了身孕的人都爱胡思乱想。梦都是反的,哪来的什么凶兆呢。”
苏沫茶忽然想起了什么事,转而望着他道:“穆硕,能不能动用一下你山西那边的粘杆侍卫去我义父家里一趟。我义父回家都这么久了,我给他去了好几封信,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义父的老家也没什么人了,我担心他老人家一个人出什么事。”穆硕一怔,随即掩饰了表情,说道:“好!等我回到总坛里就去帮你打听一下。你呀,现在还是少操心,养胎要紧。虽然才一个多月,但是日常也要格外注意。”
苏沫茶点了下头,依旧是面带忧虑之色。穆硕有心让她的心情好起来,故意道:“小茶,你说腹中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苏沫茶显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反问道:“那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呢?”穆硕托腮,认真地思考了一下,道:“男孩或女孩都好,最好是来个双棒儿。来个龙凤胎,那就皆大欢喜了。”苏沫茶没好气道:“贪得无厌!一个就不得了了!还想要龙凤胎?”
穆硕轻抚着她的小腹,道:“我这真不是贪得无厌。你不知道,我与我弟弟年纪也都老大不小了,迟迟未能成婚。都没给穆延家族添个一男半女,我阿妈、额娘早就天天念叨了。如果真是龙凤胎,那两位老人家该高兴坏了。”说罢忽而面色阴郁起来,像是有什么难解的心事一般。
苏沫茶轻抚了下他的脸庞,关切地道:“穆硕,你怎么了?脸色突然这么差?”穆硕愣了下,道:“没事。只是忽然想到我弟弟巴图。”苏沫茶疑惑道:“想你弟弟了?那就去见他嘛,怎么这种表情,看着怪吓人的。”穆硕一只手搭在她的胳膊上,轻轻摩挲着她的手指,说道:“我这个弟弟从小就跟我不对味儿,叛逆得很,而且心思极重。进了粘杆处后,我为了他的长远考虑,一直冷落着他。可是他却权欲熏心,一心只想着往上爬,多次主动请求办一些危险的差事。因为获得了主子的赏识。然后三五年一个台阶,直至左佐领的高位。成了整个粘杆处里的二号人物。”
苏沫茶说道:“他既然加入了粘杆处,自然就想要往上爬呀。就像进了官场一样,谁甘心一辈子当个芝麻小官呢。当了知县就想着知府,当了知府就想着巡抚总督了。你弟弟这么做,也无可厚非。”穆硕摇了下头,说道:“我是看他身上的气场不对,对权力的热衷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做人野心太大,不是什么好事!你看这个年大将军不就是的,他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听说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他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大清国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主子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主子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主子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主子认可。由此可见,他年羹尧的野心有多大。他已经不满足于当朝廷封他的抚远大将军,而是把自己封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