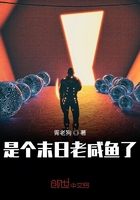军阀混战时期,在高原苗疆的十万大山里,有一个长武小镇,镇头的清水河和镇尾的藻泽地将它完全与世隔绝开来,这种封闭的环境在这乱世之中,也享得一份安宁。
很多人为了躲避兵祸,纷纷来到这长武镇谋生活,求出路,使得这个很小的镇甸扩大了两倍有余。
人口的激增,无数的商人也开始来到这里寻找商机,渐渐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铺,其中最多的便是那医药铺子,十万大山里的药材资源是最丰富易得的。
凉风习习,夏日长武镇显得是格外的凉爽,即使在晌午最高温的时刻,大街上也不同于其他地方冷冷清清,码头上的的劳工依旧在卖力的干着体力活,毕竟长武镇与外界的联系主要还是以水运为主,码头便是最佳的讨口场所。
这天,码头的管事好不容易落得清闲,躺坐在藤椅上休憩,用着一柄破蒲扇盖在脸上,遮住阳光,显得非常惬意。
“请问你们这里招还找工人吗?”
忽然,一道声音打断了正在藤椅上休憩的管事,好似这美好意境被破坏一般,他不耐烦的抬起头,打量一下眼前这找事做的人,年纪不过十五六,身材比较瘦弱,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腰间别着把破柴刀,背上背着个烂竹篓,跟个逃荒的一样。
“滚滚滚,你们这种逃荒的老子见多了,每天不来十个也来八个,做事不卖力,吃饭最积极,上个月招了两个,老子亏了两个铜板,别来惹老子晦气,老子这可不是善堂。”那管事本来被吵醒就心有不悦,这下见得眼前这邋遢少年满是嫌弃。
这管事直接出言不善,令得少年颇为不喜,出言反驳道:“不要便不要,得瑟什么,老子还看不上你码头搬货的工作。”
说完,走到装有货物的麻袋旁,脚尖轻轻一挑,将一麻袋货物踢出一条弧线稳稳的落在货船上,在那甲板掸起点点灰尘。
这管事被吓得目瞪口呆,那麻袋货物他是知道的,里面虽然装着风干的药草,但是那么大一袋,少说也有上百斤,这一脚下去得多大的力气。
做完这一切,少年面色不善的看了那管事一眼,慑得他翻身从藤椅上滚了下来,连声叫喊着:“你别乱来啊,我可有这个……”
说完在手中比了一个“八”的手势,意思自己有枪。
“哼!”少年狠狠的瞪了工头一眼,知道这管事明显是吹牛的,不过也没多为难与他,愤愤的提了提背上的背篓,转身离去。
“凭我的能耐,混口饭吃怎么这么难?”
少年人正是黎展,自从赤老头死了以后,便从那大山深处摸索着走了出来。
跟着赤老头这些年,黎展倒是学了不少东西,认字、苗医、武术、巫蛊术还得了半部《巫神志》。
成年那天,不知道赤老头从哪儿给他弄了目前这身行头送给他,本来这套衣衫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走出深山的过程中遇到几次危险,这身行头没能保得住。
黎展本无意入世,但赤老头临终前告诉了他的身世,并且叮嘱他一定要找到另外半部《巫神志》,不然难活过二十八岁,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他不得不跋山涉水来到这十万大山通往外界的唯一聚集地—长武镇。
可当他走出来,便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啥都没有,连饭都吃不起,更别说找劳什子《巫神志》,也许书还没找到,自己就先饿死了。
没办法,为了生计,只能先到处找事情做,填饱肚子,可他发现没有那么好融入当下,就这身不讨喜的乞丐装便让自己今天屡屡碰壁,招人白眼。
“咕咕!”黎展摸了摸又在抗议的肚子,满面的愁容,再不找到事做,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不远处的包子铺里传来阵阵香气,黎展感觉魂儿都差点被勾了去,整个人随着香气被勾引到包子铺旁边。
包子铺的老板见到黎展,跑到摊子前面摆了摆手说道:“要饭到别处去要,别妨碍我做生意。”
“谁要饭,真是狗眼看人低,就这破包子给我还不稀罕。”黎展争了争嘴,目光紧紧的盯着那冒着热气儿的大蒸笼,依依不舍的离开。
“砰!”一声响起,由于看着蒸笼,失神走过了地儿,黎展一头撞在了块木牌子上。
抬头看去,那是一块长武镇的告示牌,上面张贴着五花八门的告示,有被砍头的,有招兵买马的,还有通缉的,这些都不是黎展所关心,他的目光都被一张招募告示深深吸引。
这告示是悬济堂发出的,需要招募一名有经验的苗医。
这悬济堂可没这么简单,长武镇的药铺这么多,悬济堂在他们中是顶尖的,好多别的医馆治不好的疑难杂症,他们都能治好,所以生意不错,坐诊大夫一直不够用,这才不断的在扩招。
看到这张告示的瞬间,黎展心想终于有事做了,苗医这种活儿,赤老头可是倾囊相授的,就赤老头的医术在苗医中起码算是顶尖的了,以前在山林中碰见一只奄奄一息的怪鸟,给他吐两泡口水就给治好了,自己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可是有相当大的优势。
揭下告示,黎展兴冲冲的来到悬济堂,刚踏进堂内,还没开口,一枚铜子就稳稳的落进背后的竹篓里。
黎展解下背篓,捏着里面的铜子,不解的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钱给你了,可不要妨碍我们医馆做生意啊!”向着黎展背篓抛铜子的悬济堂伙计提着药壶头也不回的说道。
“等等,你把我当什么了?”黎展闪身挡住伙计的去路,“我可不是要饭的,我是来应招当坐诊大夫的。”
伙计用劲狠狠的扒拉挡住自己的黎展,生气的说道:“什么?我没听错吧,就你也是大夫?就你这年纪?你这模样?你说你是来应招的?你配吗?你要是大夫,那我柳小六不就是神医了!走吧,趁我现在还客客气气和你说话。”
一连几问,问得黎展有些发懵,赤老头不是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吗?怎么这世上之人,皆是以貌取人?
其实这也不怪那叫柳小六的伙计,悬济堂有个规矩,一个大夫配一个伙计,说是伙计,其实和学徒没什么两样,在大夫身边待久了,多多少少能学点不错的手艺。
现在这悬济堂就柳小六一个闲置下来的伙计,说白了,悬济堂这次招募,就是给他选师傅了,等了两三天,等到这么个年纪和自己相当,衣衫不整,脏兮兮吊儿郎当之人,任何人看来都是在消遣自己。
如果黎展知道柳小六心中的想法,肯定会叫屈喊冤,自己行头差不假,但是吊儿郎当这从何说起,嘴里含草那是饿急眼了,从背篓里拿出根茎吮着点甜味解饿。
正因为不知道,黎展也误会了,开口就怒斥柳小六:“狗眼看人低!”
柳小六闻得这声斥责,也没理会黎展,只是朝着医馆里面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嘟哝着:“真晦气,遇到个要饭的也就算了,还是个神经病,口气比人大,呵呵,当大夫,下辈子投个好胎吧。”
“你……”黎展听到那柳小六嘟哝之声,正要开口说点什么,悬济堂门外传来凄惨的哭声。
黎展第一个走向门前,柳小六紧随其后。
来到门口,黎展便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怀中报这个六七岁的孩童,跪伏在地上哭泣“呜呜呜,救救我们娘俩吧。”
黎展下意识的迎上前去,欲要看看二人是何症状,却被柳小六将他身子蛮横的扒拉到一边,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接着那柳小六一脸为难迎向那对母子,还未开口,那妇人便说道:“柳小哥,求求你家大夫快帮我的健儿看看吧,他已经昏迷好几天了,茶饭不进,我这为娘的都快担心死了,他爹去参军好几年了也没有个音讯,我娘俩在家无依无靠……”
话未说完,柳小六便打断了妇人的话,面容苦涩的说道:“春姨,不是我们不帮你,医馆里所有的大夫都看过了你们的症状,都是瞧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
就在几人哭闹之间,周遭开始围起了不少人,指指点点,不知道在说什么。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担心影响生意,柳小六快步上前,拉起春姨的手想将她们母子二人领到悬济堂内再做打算。
谁曾想,春姨认为柳小六想撵他们走,用力挣脱他的手,赖在地上,死活不肯起身,并扬言“别想驱赶我们,今天你们要不把我的健儿治好,我们娘俩就死在你们悬济堂门口,让别人好好看看。”
“诶!你这不是耍赖嘛,你不会是别的医馆安排过来的吧?”柳小六面露疑色。还瞟了眼一旁的黎展,心想这两人是不是别的医馆喊过来整悬济堂的,一个所有大夫都治不好的病症,怎么轮到这乞丐就这么积极。
“我哪里耍赖了,我是短你们钱了还是怎么的?从头到尾都是你们见死不救。”
春姨一口咬定就是悬济堂见死不救,妄图逼他们施救,但是她越是这样,柳小六就越是怀疑她和黎展的关系,索性抱起双手,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怎么了?”恰在这时,一道爽朗的声音从人群的后方响起,柳小六抬眼一望,只见一头戴方巾,单肩挂药箱的中年男人缓缓朝着大门走来。
“哎哟,毛大夫啊您来了?今日找到药了吗?”柳小六见着来人,献媚的迎了上去,赶紧帮毛大夫提拎药箱。
毛大夫一脸不悦的别过身子,质问柳小六“怎么不将病人引到堂里去,留在外面哭哭闹闹的成和体统。”
“不是我不领进去,而是我们悬济堂所有大夫都看过了,都……都无能为力。”
“哦!我来看看。”毛大夫闻言,直接走上前,认真观察这对母子的症状。细细把脉并询问病情。
“咦!这病……”毛大夫面露难色。
见到柳小六如此敬重的毛大夫都是这般神态,春姨忐忑的问道:“怎么样?”
毛大夫摇了摇头,也不言语。
春姨看到毛大夫都如此,整个人犹如晴天霹雳,天旋地转,晕倒在地。
毛大夫连忙上前,一把扶住春姨,对着柳小六吼道:“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快叫医馆里的大夫出来,救人要紧!”
不一会儿,医馆里的其他大夫鱼贯而出,陪着柳小六一同出来和毛大夫搭手施救。
“嗝!春姨手中的孩子打了个嗝,一阵可见的暗红色的雾气从他口中呼出,一阵腥臭的泥土气迅速向周围扩散,那味道就像是数不清的蚯蚓缠裹着是一样的。”
施救的医生纷纷以袖掩面,周围的人闻到这味道退出几大步,远远的避开这对母子,有一个老农拉的耕牛无缘无故的烦躁,鼻子喘着粗气,眼珠子血红,要不是它的主人死死的拉住它,说不定它就直接冲向人堆,顶伤围观的几个人了。
“毛大夫,您说这不会是瘟疫吧?”柳小六在后面掩面提醒到。
围观的人听到瘟疫二字,霎时间骚乱起来,纷纷往后退去,叫骂声和哭喊声不绝于耳,乱做一团。
正当毛大夫准备训斥柳小六的时候,在他们不远处响起洪亮的声音“谁说这是瘟疫,我还以为你们悬济堂多大本事,让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