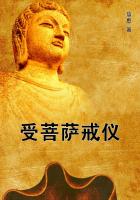晚上十点,诺尔大楼内人群开始散去。大家看起来都欢欣鼓舞的,仿佛刚刚亲身体验了某种大彻大悟。几分钟前,从希尔演讲的楼层传来热烈的掌声,莫德雷德以为鼓掌的不可能是记者。他一定是搞错了。
他不再坐在人行道上。那样的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要是警察过来让他离开,那可不得了。十点一刻,汉娜和她随行伙伴,其中包括亚历克,出现了,几个人聊得正欢。好一会儿,她才看到莫德雷德在马路对面招手,便立刻收起脸上的笑容。
“你给我——给我走开!”她边喊着,边用手背轰他走,“我现在是真的不想见到你!以后,我会听你跟我解释你到底中了哪门子邪,或许明天——也或许下礼拜,明年,十年以后!因为我可能真的需要那么久才愿意跟你讲话!”
他耸耸肩。“我道歉。”
“可问题是你一点儿歉意都没有。”
他不打算跟她争论自己是否后悔这件事。他当然不后悔了,为什么就该后悔呢,他刚刚很可能救人一命。可是,天哪,他竟然说出了口。他尽力了。
“好吧,”他说,“不过你这么做很愚蠢,连解释都不要我解释。”
“你让我们特别难堪,约翰!你还是不明白么?在所有人面前!我们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他们还是会嘲笑我们的!除非你可以走遍伦敦让每个人都认为你的所为超级理智,根本不可能!”
“好吧。那么,我再次道歉。”
“你活得现实点儿好吗!”
一辆出租车在她面前停下,横在他们之间。她打开门,让丈夫和三个朋友上车。亚历克俯身消失在他视线之下前,偷偷望着他一笑,仿佛在说“地狱之怒火都不及[26]哟”。
“朱莉娅在楼上,”汉娜恶声恶气地说,“正等着你呢。”她俯身钻入车内,“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
他在诺尔大楼入口处站了足足五分钟,根本挤不过还在散场的人群,人群散尽,他便进入大楼。一个约莫三十岁、高大儒雅、身着晚装西服的男人抓住他的手臂。保镖?真是的话,现在出现有点儿迟了啊。
“你不就是撞倒摩根·史密斯的那个人吗?”他说。
“摩根·史密斯是谁?”莫德雷德回答。
“戴眼镜、下巴留胡子的男人。顺便说一声,你还欠他一副新眼镜。”
“是的,好吧,是我干的。可我是想救他的。嗯,确切地说,不是他。是查普曼·希尔。那个跑掉的男人,他把我推开是因为我告诉他说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那样把你推开,我猜,一定是想干什么大事。”
“一点不错。”这跟莫德雷德预计的对话内容不大一样。但还是开始朝他想进行的方向发展。
“那你想要怎样?”那个男人问道,“你回到这里,为的是什么?”
“我妹妹在上面。她叫朱莉娅·莫德雷德。小说家。”
他放开莫德雷德的手臂。“你是朱莉娅的哥哥?当真?你能证明吗?我是说,有身份证明吗?”
“罗迪,让他上来,”楼上传来朱莉娅的声音。他们同时抬头望向楼梯平台。她扶着楼梯扶手站在那里,神情忧郁。朱莉娅双颊凹陷,鼻子小小,眼距较大,一对天蓝色的眼睛透着紧张。“他真的是我哥,而且他不傻。如果他说那人是准备捣乱的,几乎可以肯定那人就是来捣乱的。我哥很可能帮了咱们免于一场悲剧呢。”
“我也这么觉得,”罗迪说。他握了握莫德雷德的手,“罗德里克·皮斯霍尔姆。我欠你一杯酒。”他看看朱莉亚,又看看莫德雷德,“我先走了,给你们留点私人空间。”
罗迪离开时,莫德雷德走上台阶。朱莉娅领着他经过空荡荡的讨论场地,来到一间无窗的小房间,房间还没莫德雷德家的卫生间大,里面面对面摆着两张翼状靠背椅,还有一幅镶框画,画上是雨天的本尼维斯山[27]。一盏枝形吊灯悬在天花板上,但灯光昏暗。墙壁是赭色的。
她吻了他的双颊后,抱了抱他。“我最近心里可难受了。”她说。
他记得:他该装作不知道她会在这儿。他这样假装下去的话,也许还能从某种程度上帮他挽回与汉娜的关系。
“我不明白,”他说。“你来诺尔大楼干什么?你又是怎么认识罗德里克的?我的意思是,他是什么人?”
“我先拣重要的跟你说吧,”她说。她示意他坐下,“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但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尽管问,但我有点被你吓到了。”
“我不明白你说‘吓到你了’是什么意思。”
“首先,你突然从这儿冒出来,还是在所有人都已经回家之后。然后,你把我带进一间僻静的房间,还告诉我说你有几件事要问我,然后还有罗德里克的出现,最糟的是,你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你心里一直都‘可难受了’。”他大笑一声,“那我应该有什么感觉?这可绝不是‘意外的团聚’这一通常情况下算作开心之事该有的开场白。还是我漏掉了什么?”“咱俩的相见并不是意外。”
“哦?”眼下,他感到自己完全掌控了局面。
“是我让汉娜带你来的。”
“我懂了。唉,很不凑巧,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场。会还没开始我就离开了。”
“我听说了。还有——还得谢谢你。不光我要说谢谢。这也是查普曼的想法。你现在在那儿是大红人。”
“既然如此,或许你可以让他给汉娜挂个电话,因为她现在气得不行。她说我在整个伦敦面前丢了她的脸。嗯,等一下……”
“怎么了?”
“你叫他‘查普曼’。”
她涨红了脸。“那就是他的名字啊。”
“我还以为他叫‘查普曼·希尔’。你是受雇于他,还是怎么着?我猜肯定是。当然了,这样的话,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但想必你不是真的需要工作。你的第二部小说就快出版了,不是吗?《卫报书评》说这本书的出版是‘2015年文学日历上最令人期待的事件’。”
“是。”
“那这又是为的什么?搞研究?”
“约翰,你记不记得,去年,咱们都在格拉斯顿伯里[28]的时候,我们都得知你爱上了一个中国女人,我们还盘问过你呢?”
这时,轮到他脸红了。“有点儿印象。”
“你当时是爱她的,是不是?”
他咽了下口水。她总是像这样搞得他心里不爽。以前,他俩的谈话也曾让他心里很痛苦。“我无可否认。”
“你还爱她吗?我是你妹妹。我以一个对你深切关心的妹妹的身份问你。别跟我说少管闲事。”
他轻声一笑。“我也没打算这么说。”
“那么……?”
“现在好多了,我想是吧。”
“你其实很痛苦,对不对?你心里很难受。”
他大笑。“他们都说,‘分享相似的经历,负担也能减半’。是,我想我的确心里不好受。我努力摆脱这种感觉。我努力不表现出来,可是,你说的没错。我爱过那个女人,我依然爱她,我想,我大概会永远爱她吧。”他隐约生起气来,“不要再问问题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令他惊讶的是,她突然哭着走过去坐在他的膝盖上,仿佛时光倒回二十年前。她搂着他痛哭流泪,把头埋进他的臂弯里。他感到自己也应该做出相似的反应,但竭力忍住了。他希望罗德里克不要在这个时间闯入。他同朱莉娅在同一屋檐下,宛如回到婴儿时代。天知道这是怎么了。
她起身擦了擦双眼,坐回自己的椅子上。“我爱上了一个人,约翰。大概就像你当初那样吧。也许更糟。”
“我猜,他抛弃了你。”
“可以这么说吧。但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人是不是罗德里克?”
“我就知道你可能会这么说。不是,是查普曼。”
“老实讲,他给我感觉还真是那种玩儿玩儿就算的人。单单从我在媒体上看到的来说。他的表现无不透着赤裸裸的自恋。”
“你这么讲不公平。他写了本书。很有创见呢。”
“《占星术士》吧。写的大概就是他自己。这难道还不是自恋么。”
“‘大概’。也就是说你没看过。”
“没,既然我知道了他对我妹妹不好,我也就不打算看了。”
“我就当你没说过这话。我就直说吧,我想让你帮我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大笑。“我?维基百科怎么不行吗?”
“我是认真的。我不会把你弄来的情报当作他用,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我碰巧知道,虽然你一直都跟我们说你是‘卖机械零件的旅行推销员’,但这并不是你的工作。你在泰晤士大楼上班。鉴于你频繁出国,我想象,你是间谍。”
他深吸一口气。“你凭什么说我在那儿上班?”
“我注意到你并没否认。”
“我是在否认啊。我猜,你是看到过我从泰晤士大楼里出来,于是断定我在那儿上班。真是就好了。”
“是。要是我真看见你连续一整周每天早上差十分九点进去,下午五点离开的话。而我确实看见了。我一直在暗中监视间谍。”
“我?还是跟我长得像的人?”
“哎,我刚说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嗯,我不是间谍。总之,让一个私家侦探去堵已经跟你分手的人可不妥。就算我是间谍,我也不会去干。有时候吧,你只能靠时间来治愈。”
“不是这样的。他是跟我分手了,但他说他爱我,而且永远不会爱上别人。”
“哇,棒——极——了。你还真信他?”
“信。”
“我不明白。你是个小说家。想必,你对人性有一定的了解吧?我想说,尤其是男人。再具体点儿:自恋的男人。”
“我写的不是那种小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大部分作品重点在于写作的过程。不是‘剧情’、‘人物’等等现代主义出现前的所有那些分文不值的东西。再说,这个跟我讲的没什么关系。我恰好知道他没说谎。”
“有什么根据么?”
她大笑。“我就是知道。”
“我想咱们还是别继续这个话题,先稍作暂停,好让你在脑子里重放你刚说的那些断言。假装你是局外人,问问你自己:‘这几句话会跟我怎样的印象?’之后,我想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很难理解你。”
“我知道你觉得我傻,约翰。不要否认。你以为,因为我是专业小说家,就一定对这个世界全然不知;而只知道怎么借鉴文学作品中一成不变的典型来塑造自己作品的人物。我甚至对你的看法无异议。我觉得这样想也没错。但这事儿,我敢肯定。”
“权且把话题继续下去,你想要我调查他的什么?不用回答。我来告诉你。‘他是不是背着你跟别人约会呢’。我不想由我来告诉你,但几乎可以肯定,他确实有了别人。他结束了跟你的关系,你怀疑他在跟别人交往。这种情况下,结论不容置疑。”
她笑着“哼”了一声,仿佛对于让他结束发言,她很满意,但她又知道他还没有说完。
“换一种说法,”他继续说,“如果是他提出的分手,从道义上讲,他甚至没责任忠于你。他开始和别人交往,也没什么可疑的。不存在欺骗,也不存在背叛。他一直都很坦诚。也许你心里很受伤,但除非你有订婚戒指,或者他给了你什么实质的承诺,或者你怀孕了,不然我觉得耿耿于怀对你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好吧,为求你安心,我没怀孕。”
“那真是太好了。”
“虽然我试过。”
他大笑。
“你觉得很震惊么?”她问。
“请注意,朱莉娅。‘我’试过而不是‘我们’试过。”他开始感到不安。谁会想到,他的小妹妹竟会沦落到这般境地?一个男人的情感奴隶,还不是随便什么男人:而是一个虚荣自负的男人。当她最终走出这段感情,会觉得自己当初真是堕落。
但她可能走不出来。这种事情通常都是精神疾病的外在表现。她可能会开始跟踪她的心上人。她也许会被告上法庭。《卫报书评》会作何反应?反响大概不错。他们就喜欢“文学郡”里患有心理疾病的艺术家。这才证明这些艺术家的真实性。
跟她好好讲,她恐怕也听不进去。天啊,简直是一团糟。该如何是好呢?最好先带她离开这栋楼,远离希尔。她有所好转之前,不让她见到他。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约翰。”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不会去做的。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我的解释糟透了。我看出来了。我把你吓坏了。”
“对你,我不会撒谎的,朱莉娅。我很担心。担心你。”
“咱们接着你不久前提到的事情说,”她说,“之前你说,‘我要查他什么?’我之所以没打断你,是因为,我以为那样你就可以把你想说的一股脑儿都说了,然后咱俩可以重新开始谈。可我现在看出来了,那就是个错误。那样不过是加深了你的成见。”
“不早了,我想,也许——”
“我觉得他没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我们之间没别的。真是的话,就更好了。我会伤心欲绝,但我知道心碎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怎么从中恢复。狂工作,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多找人陪,给自己时间。这并不难。但不是,问题是,我爱他,他也爱我,而且我敢肯定,有人想要他的命。”
莫德雷德听到自己的嘟囔声。“要他的命?”
“看你这反应,你知道点儿什么。”
“猛推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身份的第一判断,也是我最认同的,并不是杀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你本来觉得他是什么人?”
“准备来起哄的,也可能是来扔鸡蛋的。”
“他的伞呢?你怎么处理的?”
眼看着她的拳头就要打过来。“我——我不知道。我肯定是在出去的路上,把它放在走廊的什么地方了。”
“罗德里克说你没有。”
“坦白讲,我当时脑子很乱。我并不知道我把那伞怎么样了。”
她笑了。“你可得想出个更好的说辞啊,约翰。咱们再重新过一遍今晚发生的事,好不好?因为你可以说你不记得,但我当然是坐在很有利于观察的位置。”
眼下,她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危害降到最低?该死的,怎么一下子从她的情事说到这事儿了?因为她哄骗他,让他产生错觉,感到安全,当然,还诱使他全情投入。
“首先,”她说,“你接近那个人,然后说了些什么。他朝你的胸前来了一脚,便离开了。有人——是个女的:我不知道是谁,但早些时候,你确曾向她招手,但她刻意没理会,所以我猜你们一定认识对方——她过去抓住那把伞。但她还没来得及将其偷走,你便从她手里抢了过来。那之后,你才离开。而当你走到外面时,你检查了下那把伞。之后你叫了出租车。你走的时候带着伞,但四十五分钟后你回来时,手上却没有那把伞。这意味着你把它放在了什么地方。但鉴于你最先为得到那把伞所做的一切,到了外面你对它的关注度,还有你刚骗我说把它留在了走廊的事实,你不可能是随随便便把他丢在了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我一直透过楼上的窗户盯着你呢。话说到这儿,你刚跟我说的那些话,有没有你想再考虑考虑的?”
他大笑。“……也许吧。”
“好主意。”
他站起身来,将双手插进口袋,又大笑了几声。
“有什么那么好笑的?”她问。
“我刚还以为你有什么心理疾病,觉得让你待在精神病院可能会更好。现在,我改主意了。是,你可能是智胜了我,但至少你没事。总而言之,这是最最最好的结果。”
“我很感动。”
“你想要我做什么?当真要我找出谁要杀他?”
“可以从这方面开始。你想想,约翰。真选党也算大党派了,几乎和独立党[29]一样的规模。而且,支持它的人群非常特殊: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如果有人杀死他们的领袖,就不算谋杀,而是暗杀。也很可能是企图干预英国民主之举。”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诸如此类的事情,正是英国特工情报机关应该会感兴趣的。”
“跟我想的一样。我同意。不过——”
“你并不是英国特工情报机关的一员。明显不是。之前,是我完全搞错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跟他……”
“跟他把我甩了有什么关系。事情不是那样的。你看啊,我十分肯定他知道有人想杀了他。他提出分手,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对我更好。他爱我。他不希望杀手当着我的面把他杀死。”
“你跟他提起过?”
“没有详细正式地谈过。他非常不情愿说起这个。而且,当然了,既然他跟我分手了,这事也就不关我什么事儿了。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有什么理由使得有人要他死吗?他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据我所知没有。”
“你觉得他知道是谁要来杀他么?”
“我猜他肯定知道。”
“之前有人企图杀他么?我的意思是,假设今晚真的是冲着他来的?”
“我在的时候没有。但我知道他认为会有。不止一次。他认为自己一定会死。”
“既然如此,难道他不该躲起来么?”
她讥笑道,“你可以尝试这么跟他说,看他什么反应。”
他打了个哈欠,然后看看手表。十一点半。“我一两天后给你回复,但我不会做出任何承诺。你住在哪里?”
“住家里。汉普斯特德[30]。”
“我陪你走回去吧。”
“不用了,约翰。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如果你更愿意在我那儿将就一宿,也可以。”
她耸耸肩。“为什么不呢?好的。”
“好极了,”他告诉她说,“就像小时候一样。对了,我家有《哥斯拉》。”
她笑了。“今天就算了,谢谢。咱们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