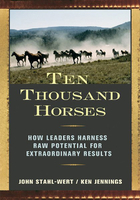永寿殿此刻却是一片宁静,窦太皇太后正做着到上林苑乘凉的准备。
许昌等人的到来,令窦太皇太后大吃一惊,一时间心绪大变。
“陛下是从何时不再早朝的?”
“大概已有十数日了。”
“你等为何不禀告哀家?”
“陛下说,他忙于其他军机要事,之后会亲自禀奏太皇太后。”
“你等啊!真是榆木脑袋!”
窦太皇太后一下子跌坐在榻上,苍老的脸顿时阴沉了,“太后知道此事么?”
她本以为自己可以放权,却不想才多长时间不管了,形势就紧张成这样……
她心中一阵动摇。
“臣已让庄青翟去问了。”
窦太皇太后不由分说,转脸厉声下令:“速传王太后来见!真是好一手掩护,都不要朝政了么?”
“诺!”
窦宇一转身便匆匆离去。
太皇太后将一腔怒火撒向面前局促不安的大臣们。
“你等拿着朝廷的俸禄,却整日浑浑噩噩,不思为政之道,有愧先帝之托!
你瞧瞧!陛下已经数日没有早朝,你们竟匿情不奏,不知所以,该当何罪?”
许昌脑中嗡嗡繁乱,回道:“陛下说,他要闭门读书……”
“哀家什么时候只要他闭门读书而不早朝了?你等就没有发现陛下近来有什么异样么?一个顽皮皇帝一群木鸡臣子,这……哀家气啊!”
太皇太后越说越气,问着话就流下了泪水,伤心地自言自语道,“启儿呀,你当初怎么就选了这个冤家呀!你说适时放手,可这种情况,叫母后怎么放手?”
伤心归伤心,生气归生气,眼前的难题她却不能不去面对。
她能辅佐文、景两帝,垂帘刘彻,经历的风雨何其之多,现下立马有了考量。
“你等都是陛下的近臣,怎么对他的行踪一点都不知道呢?还有……那东瓯国的使节来了几日了?”
“大概六七天了,他正等着陛下的召见呢!东瓯国已经断粮,他们拖不了多少时日,正盼望着朝廷早日出兵。”
许昌道。
石建小声提议道:“依臣看来,太皇太后还是见一见使节吧!”
“胡说!”
太皇太后心下一凛,打断了石建的奏议,喝道,“煌煌大汉,皇帝在上,哀家再打理国政,传扬出去,成何体统?”
正说着,王娡王太后脚步匆匆,就在包桑的陪同下到了。
太皇太后一听见王娡的声音,怒火就从心底烧起,喝道:“快说!陛下他到哪里去了?”
王娡对此事茫然不知,如实答道:“陛下不是在宫里吗?”
“哼!你们是成心合伙欺骗哀家是不是?”
太皇太后闻言怒极反问道。
王娡感到很委屈,她这些天是确实不知道儿子的行踪。
她问过包桑,可包桑就一句话,陛下在未央宫中读书,不见任何人。
她凭自己对儿子的了解断定,彻儿不见臣下,必有重大的举动,但不至于到了荒废朝政的地步,这于理不合。
好在包桑就在身边,他一定知道陛下的行踪,于是王娡大声问道:“包桑!陛下究竟到哪去了?”
“这……启禀太皇太后、太后,陛下正在未央宫读书呢!”
“大胆!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
太皇太后由于盛怒而发出断断续续的喘息声,“身为黄门总管,不悉心伺候陛下,已属大罪,如今又隐情不报,其心可诛!”
“太皇太后,奴才真的……”
包桑双唇嗫嚅,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作为每日不离刘彻的中人,这几个月,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皇帝排解烦恼,他希望陛下等待时机,重新崛起。
因此,当他被传到永寿殿时就打定主意,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说出皇帝的行踪。
“奴才真的不知道……”
“哼!看来你今日成心要与哀家作对了。”
太皇太后冷哼一声,让一殿人都毛骨悚然,“哀家从侍奉文帝起,还没人敢如此大胆。来人!让包公公清醒清醒。”
“太皇太后,奴才……”
“拉下去!”
太皇太后没有任何心软和动摇。从殿后传来包桑凄厉的惨叫:“太皇太后饶命啊!哎哟!啊!”
许昌、石建和石庆第一次见太皇太后对一个中人动如此大刑,一个个心都悬着,暗暗打量着太皇太后。
她脸上掠过一丝冷笑,问道:“众卿以为如何?太后以为如何?”
包桑的每一声惨叫,都牵动着王娡的心。
倒不是她的心承受不了,当初对栗姬动手的时候,她的冰冷和残酷丝毫不逊于眼前的这位老太婆。
只是如今她心里明白,太皇太后的刑罚,虽然打在包桑的身上,实际上是指向她和刘彻的。
王娡的思维急速运转着,在寻找解救包桑和自己的办法。
她在太皇太后问话的时候,就已想好了应对的辞令:“母后息怒!包桑隐情不奏,是罪当其罚。”
“你真的这样认为么?”
“一个黄门总管,死何足惜?只是……”
“只是什么?”
王娡顿了顿,竭力使自己说话的语气平和:“只是只有他知道皇帝的行踪,若他毙命,皇帝便无可寻找,而东瓯国急待朝廷发兵,这岂不误了大事?还请母后三思。”
太皇太后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这一阵她只图发泄心中的愤怨,却忘了还有这一茬事在等着。
不论怎样,她是不能出面去接待使节的。她不能出面,王娡自然更不能替代刘彻去应付局面。
想到这里,她命令道:“把包桑带上来!”
包桑已被打得皮开肉绽,脸色惨白,汗水和泪水搅在一起,往日尖细的嗓音也变得十分微弱:“奴才谢太皇太后、太后不杀之恩。”
太皇太后不满道:“难道你现在还不肯说么?”
王娡知道,这话只有自己来问,才能消除太皇太后心中的郁气。
她走到包桑面前轻声问道:“公公这是何苦呢?如今南国战事吃紧,东瓯遣使求援,十万火急,公公隐瞒皇帝的行踪,岂不要误了朝廷大事?
不仅太皇太后不能饶恕你,就是皇帝知道了,你也怕难逃责罚。公公还是赶快说出皇帝的去处,也免得让哀家难堪。”
许昌也在旁边催促道:“快说!陛下究竟在何处?”
包桑抬起头,望了望王娡,断断续续地说道:“陛下……以平阳侯的名义……出宫去了。”
“你可知他现在何处?”
“自那日丞相要见陛下,奴才就让骑郎公孙敖到京畿各县寻找,最后一次听说陛下是在户杜两县交界处,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河水岸边的湖县。”
太皇太后听罢,声音愈加沉重了,叫道:“看看!看看!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荒诞嬉戏到如此地步,成何体统?”
王娡见状,忙劝道:“母后息怒!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皇帝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