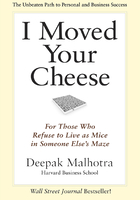这座灯火辉煌的豪宅,不知某人闯了几次,如今她已轻车熟路,里头所有通道她已经绘成一幅地图。因此,飞白如入无人之地,轻易避开守卫点。
才发现,灯火兴旺的深处,异常明亮。只见,此处花香四溢,粉色繁盛。这么冷的天看到这奔放张扬的花粉情色,如同冰块掉进沸腾的水里,融化了寒冷,如此美丽,让人忍住移动的脚步,静静驻足享受风儿拂动员粉嫩。
粉色花瓣下,一抹玲珑娇俏的身影在花下穿梭,笑声不断,她像一只误闯花丛的精灵雀跃地在每朵鲜花人闻闻,却不忍心动手摘下娇嫩烂漫的花苞,风扬起的青丝俏皮地跟在她背后轻舞飞扬,还夹着几片柔柔的花瓣。似乎感觉出空气中细微的质变,女孩猛然回头,睁睁地,对上了屋檐上斜趴着的安飞白。
安飞白想不到精灵突然就发现自己,心里闹突,还以为这女娃子纯真简单,不料却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她看错人了,都被人家发现了,难道还愣愣地让人家在下方用无比“纯真”的眼神射杀死么。她大有一副“你能耐我何”的大义秉然,“咻”地一跳,在空中翻个漂亮的跟斗,轻飘飘地着陆。
哇,从天上飞下来耶,会不会是武侠小说里所描述的那种身怀绝技的夜行女侠呢,亦或是神话故事里绘声绘色的仙女姐姐,哇哦。太好玩了,嘿嘿,得想个法子把她留下来玩几天,长年四季都囚在这园子里,比猿人还猿人了她。某女在心里盘算其中的可行性。
呃!远看不知道近看吓一跳,这哪门子精灵啊。简直就是一脸的搪瓷娃娃,而且是那种打不得骂不得含在嘴里怕融着,捧在手里怕摔着,非常符合安飞白欺恶怕乖的那一型。逃。这是她常常脚底抹油落荒而逃的基本作战方案,按照常理推论,这种性格的人十之八九会像橡皮糖那样死缠烂打,直到她挥起白旗宣布战败。
“啊,你别走!”搪瓷娃娃啥都不太会,似乎就这水灵灵的大眼睛好使,好死不死老能洞穿他人的内心,也要死不死碍着安飞白的道“你敢现在就走,我就大叫一声‘刺客’,那时触报警线量你今晚插翅难飞。”
什么?搪瓷娃娃,形容她这恶质的小魔女身上,简直畸形,过分高攀了她咧。基本上她安飞白没放几人进眼里,这具肉体的主人虽然成年,只可惜动作和言语跟不上年龄的脚步对不上号,基于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低调路线,本想着轻轻地我来了,正如我轻轻地走,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打算,她认栽一回,喧嚣为宁静化干戈为玉帛,她就同这奶娃女过几招,直捣主题“奶娃女,有什么条件说出来听听。”
柳生三之吉走进她,微嘟着樱红的粉唇,像个淘气的孩子,“你真是无趣,这么快戳穿人家,一点不好玩嘛。”哇,近看这冷傲的仙女姐姐,美则美矣,可美得缺少温度,怎么办呢?
好玩?谁陪她好玩了,要玩她安飞白玩的可是人命,出个漏洞的话估计走出名真一郎的地界后自己不是半死要么也是半身不遂了。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这种事说了没个准的,这娃也不是管自己是哪票子人捏,硬把自己押这儿。飞白不喜欢杀人,但只要有人碍了她的计划,成了传说中的眼中钉内中刺,杀人么她绝对连眼睛都不会眨巴一下的。估摸这娃还不知自己碰上是啥狠角色,敢情她大小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习惯了,呼风唤雨也腻了,连她这飞檐走壁的夜行人让她撞上抓来差遣差遣,虐待虐待?
某女可能也是没被人虐待过,一个劲地热脸倒贴冷板凳也不嫌被动,大约脑子里让人灌输过一道名为”察言观色”的程序。”仙女姐姐,你别走,你从哪里进来的。”这莫大我园子里,日日夜夜只有鲜花的寂寞陪伴,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个人,直到有一天她从书上读到一句话,它说: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既然孤独寂寞是别人拿来惩罚自己的脆弱,为何要哭着眼板着脸让别人奸计得惩,看自己笑话,于是乎,从那天起,她秉着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的真理,用柔软的微笑卸掉别人对她的防备,让人误以为她是一只被剪了爪子温顺的小猫咪,其实认真注意,那笑意总带着纯纯的若有似无的冷然萧瑟。
听听这话,安飞白真觉这孩子被人保护得太好,没心没肺应了声“从外面来的。”得,这话等于白说,某女不依,睁着渴望的水晶珠子发挥好奇宝宝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双手配合着交叉抵在下巴俨然一副“大爷你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的乞丐相,很明显,这丫头知道来人吃软不吃硬的毛病。
忍下嘴角抽搐的举动,咬咬牙“札幌。”安飞白还机警地四处瞄眼,就怕行迹败露了出师未捷身先士卒,那叫一个冤家得了。
柳生三之吉安慰她道,“放一百个心,就算我今天死在这,明天估计也不会有人发现。”意思是,我是个被人冷落的主儿,根本没人注意到这里。
戒心哪是她一两句话就放下的,飞白的心和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有什么条件你赶快开出来&8226;”她没时间在这女娃瞎耗,事关重大,时机难寻,一旦错过,时不再来,何况她又是名真一郎这边的人,指不定飞白前脚一走,她就派人过河拆桥了。
风力有变大的趋势,细碎的雪花来自远方洒遍大地,柳生三之吉打个“哈欠”,颤抖着纤弱的腰身猛吸鼻涕,“天越来越冷了,进屋里谈行么?来嘛,我一个手无傅鸡之力的柔弱小女子,又不能把仙女一样的姐姐你怎样怎样!我保证只问几个问题,然后让你走,我公平吧!嘻嘻……我也觉得。”整个过程都是她自说自演,而安飞白自始至终一脸高深莫测凝视柳生三之吉,冷冰的气场所到之处气温急事下降。柳生三之吉也不生气,半拖半拉把人推到暖烘烘的房内,室内因为炉火燃烧正旺,这温差让她圆溜溜的眼眯成一条细线,“嗯……好舒服。”
人奔到炉边在其旁蹦蹦跳跳,不一会儿水嫩细致的脸蛋染上两面三刀片绯红的浮云,模样好不幸福惬意,那么活泼怜人,朝气蓬勃。天灵盖闪过一道光,安飞白懵了,自己怎么就肯乖乖跟她来了,甚至让人怀疑刚才是不是被那啥啥啥给附身。
人刷地一下子,寒着眼看她“闹够了没,我可没那闲工夫跟你大小姐玩。”话完手已经搭在门把上,“你敢踏出这个房间一步我马上喊出来,看你还走得了不。”
点降唇,双手把势在必得握于胸前,一副胸有成竹“你能奈我何“的嚣张拔扈的千金大小姐样撒沷。“姑娘,你我素不相识,何必处处咄咄逼人,若我要走就算天罗地网我一样不费吹灰之力离得开,只怕到头来,姑娘受罪不轻。”
“这么神?既然仙女姐姐如此盖世神功,那就试试看,你走吧!”柳生三之吉在赌,赌她肯定不会走出去,因为她明白这个陌生又神秘的女子对自己多少有几分忌惮,才致使现在被她牵着鼻子走的位上,对她迟迟没有出手。
于是出现下面一段,我问你答的对白……
“仙女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丸美。”
“哇,好有个性的名字哟,跟你很相配,你爸妈真有眼光。”
寒了,这跟眼光扯上啥关系了?“自己取的。”
某女脸僵。“姐姐今年贵庚?”
“秘密。”
“好吧,虽然我知道年龄是所有女性忌讳的问题,我小人不计大人过,跳过这个问题,那你结婚了吗?”
“没有。”
“姐姐你来这里要找什么东西么?”
“无可奉告!”
“姐姐……”
姐姐……柳生三之吉左一句姐姐右一句姐姐,叫得好不亲密,难道她里塞的是浆糊而不是脑汁,以为这一叫就能够移走飞白心中的大山,未免太过幼稚吧。
她那些个无聊的问题,活脱脱的像几百年没见过人影,一骨碌的全往飞白这边倒。她当飞白是知心姐姐啊,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
腰腹的软件已经雪亮雪亮指在咽喉正前方,“我让你闭嘴,听到没有。”眼睛被耐心磨得怒火喷发,飞白真想一刀结束这聒噪的小女人。
没碰上真刀实枪的柳生三之吉,早就吓白了脸,凄楚楚的泪水哇啦啦滴泪,湿透了无辜的脸蛋,无声的委屈,她很少笑,无论是吉桑面前还是那些派来服待她的仆人,她从来不轻易把自己愁苦表现在脸上,压抑成了家常便饭。许久以后,她以为自己再也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悲哀,甚至眼泪都忘了怎么让它流出来,因为没人懂得怜惜,更没有人了解她内心真正的需要。这座金笼里的每个人,活得一丝不苟,从上到下容不得半点差池,如若不然,一不留神即使小如鸡毛蒜皮的事,也是从重处罚。微笑,是她生存焉最尖锐的利器,保护自己,装作白痴,故作天真。
而今,十几年来。盼得一人,怎教她不心潮激荡。吉桑一定不知道他自诩密不透风的王宫里,漏洞开始。柳生三之吉相信,神仙一样的丸美绝对走得进,也出得去。
安飞白最爱不了这种人了,眩然欲泣的眼神已经够我见犹怜了,让美人哭泣成汪洋大海更是罪加一等,心里愧疚得紧“好了好了,别哭了,我错了还不行么?”
闻声她的眼泪更加放肆了,猛如塌了坎的洪水啊,越来越猛。终于发现,寻觅许久的东西,原来就是被人关心呵护的感觉,隐约中,希望之光照亮我心感受被爱后,柳生三之吉再不想独自守着这华丽丽的冷宫。她要飞,借助丸美的力量飞出金丝笼,飞离吉桑的魔爪,飞到最爱的正佑哥哥身边,回想那会儿正佑哥哥,虽是对自己冷冷淡淡,自己只是跌破脚指,他也会蹲下来帮自己哈哈气,抱在怀里安慰自己。记忆中那张脸却早已模糊不清,人海茫茫中如何下手找人,思及此,悲伤便掀起疼痛的泪水,越来越难受,思念呵,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幸福,它能够将人的思念撕扯着填满心房,捣碎了融入血液里,发酵着渗入骨髓,奔腾着汇成河流。“丸美姐姐,我可以求你件事吗?”柳生三之吉哽着咽下泪找回声音。
“三之吉,你要知道,我可能没你想像的那么好!“叹着气,注定的事她认命了,逃不掉的,不妨坐下来将事情解决,帮得上不上,尽力就好。
“不,你等我说完,带我离开这里吧!既然你要本事独闯这儿,没有过人的本事那不可能,我知道接下来你要办正事,好,我让你走,我会等,等到你来接我走为止。”
安飞白狐疑地看她,衡量她的可信度,此等关键时刻多一个人多一份担忧,她誓不轻易动用耗掉功力,以防计划中多出武力打斗储备力量。
唉!罢了,这麻烦怕是赖定她,吃定她心软了。“你这丫头,好吧!我答应你,可我也是有条件的,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我的指示,不可擅自主动乱了马脚,知道没有。”
柳生三之吉听了笑颜逐开,“好,我听你的,咱们拉勾!”
摊上这麻烦精不知道是福是祸!算了,走一步是一步现在。
浮上半空,视野扩散整个豪宅,飞白目光定在偏僻幽静处的樱园,若不是异乎常人,根本看不到那萦绕氤氲的淡蓝气场,一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困惑间,待到一处庭院,飞白发现它的装饰与外面的堂煌富丽格格不入,它朴实无华,安然恬静,在这充盈危机的地方神秘且和谐,不怀疑它的危险性,靠近它,似乎被它吸引是件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
“什么人!”随着声音,一道金属光线掠过眼前。只见一抹高大的身影从月色中慢慢走来,浑身散发着淡淡阴寒冰冷的气息,高大身影背光而站,长发垂在背后,飘逸洒脱,碎碎的刘海盖了下来遮过睫毛,在清冷的月光映衬下,是他那凛冽桀骜不驯的眼神,细长的单凤眼,高挺的鼻梁下是两片紧抿的薄唇,有人说嘴唇薄的人最是冷酷无情,不知道是真是假。这样的外貌和神情,第一眼,就让人觉得他太锋利,有一种混世已久的尖锐锋芒。
挥动藏于腰腹的软剑,安飞白迅速破开空气,舞动灵蛇般的长剑挡住那来势汹汹的剑身,“哐当”,刀剑碰撞的清脆声音,摩擦闪动火光,被剑气震摄连连后退几步才刹住了脚,这人有两把刷子,终于遇到一个可称为对手的人了。
激动,与被打败的心情急速化成攻击的剑,心无旁鹜人剑合一进入战斗。
对方只一眼看她,一抹玩味的笑容抑制不住浮上他冰封的脸庞,“完美的终结者?你来了。”虽是疑问句,他明白,这就是等待的人,心中非常肯定。
安飞白一怔,面色不改,怕是心里狠下杀人灭口的念头,不料这陌生人就看穿自己的身份,如果说名真一郎身边多的是这么强的忠心仆奴,必须见一个杀一个“你怎么知道!“
他邪邪地笑着,“这个世界没什么我不知道的,若想知道答案,用我们的方式决斗吧!赢了我再说不迟……”未等他说完。安飞白展开猛烈进攻,招招扼进对手要害。反观他的动作,似乎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猎人与猎物间玩弄的游戏,这更激起安飞白燃烧的火气,不断变换招式,想弄乱对方沉稳的步法。
像是漫不经心似的封杀住房她所有进攻,他这种封杀并不是平常所见的用剑去格挡,而是往往在安飞白要出招的同时,随手一剑削向她的手腕,咽喉,胸部等要害部位,逼得安飞白不得不守或被逼后退,如果是一般的剑手,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发起反攻,可是他却像懒得动一样一步不移站在原地等待安飞白下一次的进攻,身在场中的安飞白更是郁闷难当,每次刚发起进攻,他都会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要害附进,这种有力无处施的强烈压抑差点让她吐血,气得急火攻心。
剑势忽然一变,剑路变得大开大合。犹如在千军万马中撕杀一样,局势变得空前惨烈,带起的剑风刮得人两颊生疼,这已经不是剑法了,更像是至刚至阳的刀法,在气势涨至最猛的时候,一剑飞出,只见寒光一闪,那把剑直直插入一棵大树上没至刀柄。好深厚的内力。
安飞白拄剑半跪在地上拼命地喘着气,败得十分狼狈,她知道她输了,输得很彻底。
双手握于身后,他仍旧笑得风轻云淡,好似刚刚那场打斗不曾发生。“当你进攻别人的时候,你本身就会暴露自己的虚实,虽说进攻是最好的妨守,但如果不是攻其必攻之处,那么自身就会很危险。想当然攻守合一是许多追求武道的人想要达到的境界。”教训完毕,他颀长的身影借着月光罩住她,俯身审视,挑起安飞白尖俏的下巴。轻佻地说“看来看去,我真的不知道它说你最终会结束我‘完美落幕’,你拿什么来跟我比?”
被击败并没有让她觉得羞耻,偏偏他的轻浮之话对安飞白的努力全盘否定,这是变相侮辱,“你,到底是谁?”
“呵呵……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哦,其实我也不清楚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为谁而生?但我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多亏了这双手及顶上的脑袋创造的呢,轻轻掐指严重的就是消尸灭迹,尸骨无存的下场。卑微的人类给你取了个名,叫创始神&8226;唉,其实,它给我的代号是:完美。”
我的天啊!万物的创造神,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来得让人措手不及。
不多时,眼前那名似是从冰川动漫里走出的男子眨眼间已立于跟前,笑得邪肆狂妄“让我猜猜,你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嗯……”他妖孽的眼睛直射安飞白恐惧的灵魂,迷离中绽放诡谲多变的七彩光环。安飞白大脑顿时觉得麻木空白一片,身体已被神秘力量操纵不能动弹分毫,只是几秒钟,却仿如一世光阴之久,她虚脱地垂下软绵无力的身子,全身的支撑似被抽空,躺倒地面微微抽搐弯曲着。
摄魂法?神的力量,她拿什么与之抗衡,投降?这不是她的作风,不战而败最是可耻的。可是,在神面前,她那丁点法力,与班门弄斧有何不同,怎么办?怎么办?
完美一直在笑,从头到尾。“黑煞之子,怎么跟它联络上了的?这女孩倒有两下子,能得千万幼灵相助,黑煞从旁推波助澜真不简单,但,那又如何,他倒要看看,这点姿色的人类是如何将我结束重回轮回。
他喜欢有挑战的东西。“我在想,想把黑煞之子救出去,你将如何突破重重关卡。”
气势上败下阵脚,安飞白心有不服,高傲地仰起头。“就算一切的一切都被你玩弄股掌间,这个世界总会出现奇迹,你别高兴太早。”
“奇迹?”似听到一个笑话。完美手捧腹笑出眼泪,“奇迹的出现总得有人给它出现的机会,非是所有人都能创造机会。幼稚的人类陷入困境了,总想着开上掉下扭转乾坤的馅饼,哪有那么多这种不劳而获的果实,这世上的奇迹都是经过我无常的喜怒哀乐下逃生的产物。”
安飞白脸色一阵一阵惨白,面无血色。完美无动于衷,历尽风霜生离死别太多,再可怜的人已无法勾动心弦。骨子里毫无半点怜香惜玉的因子。或许可以这样做,万年寿命太长,能找到顺手的玩物也很难得,“事情也是有转机的。”她倏地抬头,露出喜悦的光芒。“一命换一命,用你至亲至爱的生命来换黑煞之子的自由,很划算,考虑一下吧。”
划算?划算个头!看他把生命当游戏的态度,他不是神,不是从天堂降生的圣洁的神,他是来自肮脏的地狱腐肉烂泥。他不配作创始神,是恶魔!生命之于他贱如臭水,不,她做不到这般摧残这美好的花花世界。
恰逢此刻,木门嘎吱一响,有人!安飞白警觉顿生,趁其分神瞬间腾跃而上,消失在黑色夜幕中。
不对,气氛紧绷着松软的气流,那也只是一小会。那张印在孩提时代的脸孔,仍是那样空而无物,时间似乎已经停留在那张无暇的脸上,衣袖飘飞,说不出的仙风傲骨,神圣不容置喙。似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风华绝代,在其身上无法摸索岁月的足迹,神游已止,儒凌云缓步上前,叩首膜拜,“老师,正佑回来了!”
绷紧的容颜漾起一抹非是人间的微笑,似极寒的冰雪地带从厚冰迸出的一朵妖艳的鲜花,美得摄魂。皓月当空雪花乱舞,今,注定卧膝长谈,解万千迷茫。
“老师,正佑有很多未解之迷须向您请教,老师您会给正佑一一解答一如往昔么?”在他面前,儒凌云从来都是奉如天,信如神,以是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成了他为人处世的标准,纵使恩师从不告知他的真名,儒凌云也识得大体不敢多问,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只是一个幼小迷茫的孩子。
完美淡笑如初,我知你要问何。“你且说与我听便是。”
“在中国,我遇上了一个特别的女孩子,她某些方面,跟您非常相似。”
见相伴多年的小正佑长大了对自己如幼时不卑不亢,神的虚荣和自满在胸间结成一堆。“你且说说她如何特别之处,又与为师所在相同之处。”难道正佑发现了什么?这孩子很机灵,就算发现了什么也会自个埋着一一探求答案,但,那又如何?
“老实说,除了老师以外,我以这世上再无能人异士,可偏偏身边发生太多超乎想像的事,她太行踪不定,又太难捉摸,空手接住急速飞行的子弹反身以手助推轻轻弹开子弹就把人枪杀,尽管她走得很低调,比如跟某些非人类的对话却让我敏锐察觉不能忽视。奇怪的不仅仅如此。还且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子,以她的名义在黑道立足了一片不容小视的地界,多少帮派也愿意卖她面子,但那个不是她,我知道,可跟她却有关系,近段时间来那名女子销声匿迹不问江湖,她的手下个个忠心耿耿为她守着地盘,而非陷入群雄无首之地,这般团结同仇敌忾,岂乃一般能能为之。”他毫不隐瞒一一把心中的困惑尾尾道出,因为这世上能帮他解答的只有恩师一人,唯有信他。
带他领到屋内,完美示意他稍安勿躁,坐在一旁,完美自己热了两杯普耳茶,名贵的普耳过他的手,又是另一种味儿了。久违的气味让儒凌云内心的躁气缓缓散开,恩师问题举手投足间便使人安神定气,跟着他的周围总尝不到人间的种种苦涩和压抑。
“来,多年不见,尝尝为师亲自泡的茶。”递一杯到儒凌云面前,完美也拿起一杯,轻轻吹动清香绥动的消气,小口小口呷饮,饮茶是一种道,可饮出一条养生之道,茶有不同道亦不同,类似人间的种种,如生老病死,如离愁别绪,如双喜临门等等百味人生,透茶观人,别有一番寓意。
儒凌云自小被他训得有样学样,恩师的茶艺也日益精湛,道亦有长,只不知到了另一个层次了,自己自是谦卑再顺承。“我已见过她了。”完美轻声哼着。
“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的事情。”说的太快,也太大声,失了平日的内敛,不怕什么,儒凌云担心的是两人若出什么碰撞,想恩师下手不知轻重,安飞白受伤是肯定的。
“勿需操心她,为师自有为师的道理,想来,她一定瞒着你来的,不只一次了,我看见她出现在名真一郎这儿。搞不好她比你还熟悉这里的机关暗道,就在你来之前,刚好她前脚一走,过过招了,别着急,她绝对是完好无损的。看得出你对她用情至深,为师哪里舍得让你难过,不得不提防的是,她接近你的目的。”
原来她常常背着他做这些事,可没有理由啊,丸美不认识父亲,更跟自己无过仇怨,她为何这样接近他,利用他,为什么?他的一片痴心被她糟蹋成这样,难怪之前她受的那伤,肯定是硬闯机关时留下的,当时他就怀疑了,可却查不出个所在然来,后来只能作罢,想到她动人的笑,凌云内心抽痛,盈到眼眶,阵阵灼痛。
望进正佑眼里深邃的悲伤,完美视而不见,说:“为师所识不仅如此,刀子不是一般的人类,半个神算了吧!天赋予她的另一个称号是‘完美终结者’,知道字面的意义吧,美丽的结局,上天给她这个名字,意思却是针对为师。为师不能伤她,也伤不了她,终有千般不愿,斗胆跟天斗,我终会落败,只怕下场不得往生,伤她助她自由天意决择,尽我本职,功德圆满是福祉尽头,魂得长安,气得生生不息,为师必然败在她之手也是天安排的劫数。正佑是个好孩子,看为师的脸色办事从不违抗,舍得,忍得,值得,今日,是对你最后的一番肺腑之言,为师有预感,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你要一一纳进你的记忆,若为师做了什么情非得已的事,那也是为你今后着想。”也是为我着想,他在心默默说出。
儒凌云见恩师一副交待后事的神色,他也跟着绷着神经,点头应允。
“你要问我女孩叫丸美对吧。为师的原名也叫完美,不过为师的是‘完’完全的完,很巧合对么,其实一切冥冥都已命中注定,摒弃人类的视角再看我们两人的,常理无法推论,科学不能研究,都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的我们这一类型的都不能得到人间的爱,善始无善终,正佑很喜欢这个叫丸美的女孩吧,你也别怪她跟着他也是因为动机不良,天的旨意是,你的存在必有你存在的必要。不为自己,只是我们这一类型的营养品,切莫怨天尤人。她只会给修行带来困扰和阻碍。你身上有一样东西,能让她重拾所失,不择手段也可以理解了。”
果然是,他不配得到爱么,没有母亲,也不得至爱,上天真真只把他当工具一样玩弄来,玩弄去了,心已经冷了,他不再追逐天边的明月,上天有自己的安排,他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好累,真的好累,顺着它的意思走下去吧!“这又跟名真一郎扯上什么关系?”
“此事为师不便与你透露,天机不可窥探,我也不能,你回去后,怎么表现,看自己了,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为师也不在。”他也该有所准备了,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了不是长久的办法。
那个叫腾豫虔的孩子怎么还没动静呢,该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