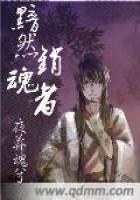六个月后
埃玛睁开双眼。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被观察了多久。康拉德·卢夫特教授坐在他最常坐的椅子里,双手放在肚子前,带着沉思的眼神和一脸惆怅的表情。
“好些了吗?”他问。开始埃玛不知道康拉德,即她“男闺蜜”,是什么意思。之后她看到床边的小桌上放着药片。那是她被关进法官指定的精神病院的封闭病房后,医生给她开的药。
紧急情况用药。
倘若她醒来后有疼痛感。
她伸展一下埋在医院专用被子下的四肢,同时想借助两肘从病床上坐起来。但她太虚弱了,所以不得不又回到枕头里,揉一揉眼睛。
也难怪在来的路上她一直没醒,看来是药的作用。仅仅这些药片的副作用就能让一头最强壮的大象倒下,何况她还服用了其他镇静药。
醒来后过了一会儿,她才渐渐认清周围的情况。尽管以前在这间办公室里呆过很多个小时,埃玛现在却有一种陌生感,但又没有像在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呆的封闭病房那么陌生。
或许是因为康拉德把他的刑事律师事务所装修了,才会有这么奇怪的感觉,但埃玛对自己的解释并不确定。
完全陌生的不是这个房间,而是她自己。
新的颜料和刚打蜡的胡桃木地板的气味还回荡在空气中,有几件家具的位置变了,但基本上还是十年前她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样子。那时的她穿着运动鞋和牛仔裤,懒洋洋地坐在沙发里。如今她穿着睡衣,躺在一张高度可调节的、被放置在办公室几乎中央位置的病床里。床头稍稍翘起,这样她能看到康拉德的书桌和它身后的落地玻璃窗。
“我猜,我是你第一个被抬进事务所的当事人。”埃玛说。
康拉德微微一笑。“我曾有几个不能亲自来的当事人,所以只能我过去。但你在医院里拒绝和任何人联系,就连医生也不行。我只好从法官那里申请了例外。”
“谢谢。”埃玛说。尽管她早已心灰意冷,觉得现在的生活里已没有任何事值得她感激,即使当下被允许离开她的牢房。
她的确拒绝在医院见他。她不想被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样子,如此病态、颓废,像动物一样被关着。这样的侮辱是她无法承受的。
“你还是那么高傲,我亲爱的埃玛。”康拉德尽管摇头,但眼神中并没有丝毫的不赞同,“你宁可自愿去蹲监狱,也不让我去看你。但其实现在的你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的帮助。”
埃玛点点头。
“您和律师的谈话至关重要。”离开医院前,精神病科的医生和警察对埃玛说。现在他们在事务所的接待室里等待,之后负责把埃玛送回医院。
律师。
一个多么奇怪的词。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个词源自古英语的“权力”一词。康拉德真的有权力决定她的命运吗?她的老知己、老朋友,尽管用“老”来形容一个爱运动的、几乎拥有运动员素质的五十八岁的男人并不合适。埃玛在上医学院第一学期时就结识了康拉德。当他第一次介绍自己时,埃玛就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之后她才想起为什么。原来她父亲和康拉德·卢夫特曾为同事,并且——尽管效力于不同的事务所——合作处理过一些案子。这些都刊登在埃玛阅读的报纸上。
然而促使埃玛和康拉德相识的案件是无法公开的。
埃玛的前任男友,贝内迪克特·塔恩豪斯,有一次喝多了,接着在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骚扰了埃玛。康拉德经常在这家咖啡馆吃饭,那天他正好撞见这家伙对埃玛的猥亵行为,并坚决阻止了他。他把名片递给埃玛,表示愿意为她提供法律帮助。埃玛确实需要他的帮助,因为她前男友后来被发现是个跟踪狂。
埃玛当然也可以找自己的父亲。但如此一来,她无非把瘟疫换成了霍乱而已。尽管埃玛的父亲和这个贝内迪克特一样,从不用武力解决问题。但这些年来,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狂怒,以至于他的脾气变得越发恶劣。令埃玛欣慰的是,自从她搬进学生公寓后就再没怎么联系过父亲。至于她母亲是如何与他在同一屋檐下相处的,对埃玛来说还是个谜。
在针对贝内迪克特的长时间法庭诉讼过程中,两人成了好朋友。一开始埃玛以为康拉德对她的兴趣是另有所图的。事实上,尽管年龄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她还是被康拉德那带有父亲角色的魅力所吸引。至今康拉德仍把他那引人注目的下巴藏在精心打理的络腮胡子下。他还喜欢穿深蓝色,量身定制的带双排纽扣的西装,并配上一双纯手工制作的布达佩斯皮鞋。他的鬈发比以前短了,但仍能盖住他高额头上的发际线。埃玛太理解为什么这位刑事诉讼律师会受那么多年纪较大的贵妇们的青睐。她们可不知道,康拉德尽管喜欢和女人打交道,但她们都不可能在他性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自从成为朋友以来,埃玛一直守护着康拉德身为同性恋者这个秘密。
就连对菲利普她也守口如瓶。当然,这其中也有她自己私下的用意。菲利普恐怕自己都说不清,有多少次因为自己的外表和魅力而得到好处。比如一位娇小可爱的女服务员向他提供餐厅里最好的位置,或者在超市的结账队伍中,他总能得到最甜美的微笑。
所以埃玛觉得保持这个秘密挺好的,尤其当康拉德时不时打来电话约她一起吃早午餐的时候,看到她丈夫嫉妒的样子。菲利普大概认为,她也被暗恋着。
康拉德需要保守这个秘密,以维护他作为一个强硬律师的形象。他甚至还常在公开场合向俊俏的法学系女生们献媚。“宁可当个永远没能力建立情感关系的单身汉,也比一个法庭上的娘娘腔要好。”他曾这样向埃玛辩解自己的故弄玄虚。
可想而知,当他解释自己只处理刑事案件,而非离婚案件,并且他的专业方向只针对那些能引起轰动的、经常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案件的时候,那些已经做好投身艳遇准备的、精心打扮过的寡妇们是多么失望。
埃玛的案件正合他的口味。
“谢谢你愿意帮我。”埃玛说。这番客套话只是为了填补她的沉默。
“再次帮我。”
在跟踪狂案件后,她第二次成为康拉德的当事人。自从酒店那夜后,她成了一个疯子的牺牲品,一个之前已经在酒店诱惑了几个女人并剃了她们的头发的连环杀手。
……然后他如同野兽般地强奸了她们……
但是对于埃玛来说,后来在精神病院里的几个小时也不比被强奸好到哪里去。在她还没完全清醒的时候,她的身体又一次被陌生人侵犯。她再次感觉到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深入她的阴道,还有其他的东西,一些能帮助采集证据的东西。但最难以忍受的是一个满头灰发、面色冷漠的女警官向埃玛提的问题:
“您在哪里被强奸了?”
“在禅宗酒店,房间号是1904。”
“那里并没有这个房间号,斯坦恩女士。”
“已经有人这么跟我说了,但这不可能。”
“是谁办理了您的入住登记手续?”
“没人。房间钥匙卡就在我的会议文件夹里。”
“在酒店里有人看见您了吗?一个证人?”
“没有,我是说,有的。一个俄罗斯女人。”
“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俄罗斯女人的房间号?”
“不知道。她是个……”
“什么?”
“没什么,当我没说。”
“好吧。您能描述一下作案人吗?”
“没看清,当时太黑了。”
“我们没找到打斗留下的痕迹。”
“我当时被麻醉了。至于被什么麻醉的,你们可以通过验血找到答案。我感觉到了针刺。”
“作案人是在进入之前还是之后剃了您的头发?”
“您指的是在他干我之前还是之后?”
“我理解您现在的情绪。”
“我看您不理解。”
“那好,但我不得不再问您一个问题。作案人用了安全套吗?”
“有可能,倘若您没有找到精液。”
“我们也没找到任何阴道损伤。您经常更换性生活对象吗?”
“我怀孕了!您就不能换个话题吗?”
“那好。您是怎么去公交车站的?”
“什么?”
“维滕堡广场的公交车站。您就是在那里被找到的。”
“不知道。我肯定还没清醒。”
“也就是说,您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被强奸?”
“那个疯子剃了我的头发。我的阴道到现在还火辣辣地疼,就好像被野兽疯狂地捅过一样。要不您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所有问题的反问。
埃玛回想起菲利普叫了出租车回家,然后把她放到沙发里的情景。
“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埃玛点了点头,叫他去卫生间的柜子最里面找一个卫生棉条,一个大号的,一个在血流量很大的时候才会用到的。还在出租车里的时候,埃玛就知道下面流血了。
他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哭。
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提起孩子。
第二天,埃玛为这个未出世的孩子点了根蜡烛。现在这根蜡烛早就烧尽了。
埃玛朝着手掌空咳了几声,把康拉德的办公室扫视了一遍,想让自己从这不堪的回忆中走出来。
与天花板同高的壁柜墙里摆放着真皮装订的联邦法院审判书,还有康拉德最喜爱的叔本华的作品。但这壁柜比埃玛印象中要矮一些,或许是因为新刷的油漆吧,这个颜色使整个房间显得小了些。当然了,那张坚实的大书桌仍旧在几乎呈正方形的玻璃窗前。晴天的时候,透过这扇玻璃窗能远眺大万湖,甚至能看到施潘道。但今天只能勉强看到湖畔小路,上面有三三两两顶着大雪和透骨的寒冷来散步的人。
突然埃玛感觉到康拉德站在床边,把手温柔地放在她的胳膊上。
“这样你能舒服些。”他边说边抚摸着她的额头。
埃玛闻到他剃须后用的爽肤水的香味,闭上眼睛。最近这几个月,只要一想到被男人触摸,她就觉得恶心。但康拉德可以用双臂把她的身体从病床上抱起,放到壁炉前的沙发上。
“这里舒服多了。”他一边说,一边让埃玛半坐半躺在柔软的沙发里,还细心地给她盖上奶白色的羊绒毛毯。
就像康拉德所说,这样的确舒服多了。埃玛觉得很安全,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康拉德在她对面的一圈靠背椅中找了个位置坐下。现在他们之间隔着一个玻璃茶几。她脚底下就是那张圆形的白色长毛地毯,黑色的边就像是一道用毛笔沿顺时针方向留下的越来越淡的画痕。但从上往下看,它更像一个匆忙中画下的圆圈。以前埃玛特别喜欢坐到这个圈里,然后看着壁炉发呆。尤其是当他们一起在这里享用埃玛带来的寿司时,她就觉得特别惬意。在这里,他们能毫无顾忌地谈论情感、失败、自我怀疑。在这里,康拉德给予埃玛的人生指导和建议,是她这辈子都渴望,却不可能从自己父亲身上得到的东西。
这圆圈的黑色逐渐褪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某些黑色部分变成了褐色。
时间能摧毁一切。埃玛陷入沉思中,她的脸感受着壁炉带来的温暖。即便是这样的温暖,那曾经和康拉德在这里共度时光的惬意,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当然了,这次来访的性质毕竟和以往有本质区别。
这一次要谈的是件性命攸关的事。
“萨姆松还好吗?”
“它很好。”康拉德回答。埃玛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对付动物是很有一手的。在她被关的这段时间里,把她的狗托付给康拉德是最好的选择。
酒店之夜过后没多久,菲利普送给埃玛一条黑眼睛、雪白毛色的爱斯基摩犬。
“一条拉雪橇的狗?”当她第一次从菲利普手中接过牵狗绳的时候,惊讶地问。
“它能把你拉出来。”菲利普说。他是说把埃玛从所陷入的“困境”里拉出来。
现在,萨姆松迷失了方向。而且就目前情况看,接下来它得继续和女主人分离一段时间。
或许永远分离。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埃玛问,但暗地里希望康拉德说“不”,然后站起身,把她一人留在这里。
康拉德当然没有这样做。
“好的。”这世上最好的倾听者回答道。这是一名记者在一篇人物报道中对这位明星律师的形容。或许这也是他最大的优点。
有些人能读懂字里行间的意义。但康拉德能够听出弦外之音。
正是由于康拉德这方面的能力,使得他成为能让埃玛敞开心扉的极少数人之一。他知道她的过去、她的秘密,也知道她超乎寻常的想象。她告诉了他有关亚瑟和心理治疗的事。通过心理治疗,至少埃玛相信,她摆脱了自己想象的朋友和其他幻觉。但今天她并不肯定是不是这样。
“我不行的,康拉德。”
“你必须行。”
几十年的下意识习惯——找一缕头发,然后缠在一根手指上,但现在却不行了,因为她的头发太短。
已经过去快半年了,她还是不能习惯,曾经的一头浓密长发就这样没了。但现在毕竟重新长了六厘米。
康拉德如此迫切地看着她,使她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别处。
“否则我不能帮你,埃玛,至少不能在发生了这么多事的情况下帮你。”
不能在已经死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我懂。
埃玛叹了口气,闭上眼睛。“我应该从哪里开始?”
“从最可怕的地方开始!”她听到康拉德的回答,“回到你的记忆里,回到你最心痛的地方。”
一滴眼泪从埃玛的眼角流出,她再次睁开眼。
她把目光聚焦在窗外,观察一个男人牵着条哈巴狗沿着湖畔小路散步。那狗好像张着大嘴,想方设法用舌头接住飘落的雪花,但毕竟距离太远,埃玛不是很肯定。但她肯定自己更愿意呆在外面,和这牵哈巴狗的男人在一起,用脚踩那厚雪,此时她的灵魂深处比雪还要冰冷。
“好吧。”她说。尽管她并不理解继续这样的谈话有何意义。就算她挺过了今天,接下来的日子也没意义,况且她现在并不觉得自己会挺过这一天。
“我只是不理解这有什么意义。我在被询问的时候,你也在场的。”
至少在第二次询问时康拉德在场。第一次只有埃玛一人,后来当负责提问的女警官疑心越来越重,而埃玛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个证人,而是个被告人的时候,她要求自己的律师在场。当时菲利普还在拜仁州执行任务,他得通宵跋涉赶回柏林,而康拉德,埃玛的“男闺蜜”,一点半就到了医院。
“当时我在你的引导下回答问题,后来我在笔录上签字时你也在场。你知道理发师在那一夜对我做了什么。”
理发师。
媒体竟然用这么平常的词,就好像把一个剥女人皮的男人仅仅称作一个坏蛋而已。
康拉德摇头。“我不是指酒店的那夜,埃玛。”
她顿时紧张地眯起眼睛,因为她知道康拉德接下来要说什么,但她祈祷是自己搞错了。
“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不知道。”埃玛撒谎。
他当然想谈谈那个快递包裹。除了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不。”她再次拒绝,但语气比刚才弱了一点。
“埃玛,我求你,倘若要我为你辩护,那你就必须把三个星期前的那天,在你家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不要有任何保留。”
埃玛闭上眼,要是这沙发的软垫能永远把她的身体吃掉就好了,就像食肉植物用叶子把飞虫吞食掉。可惜这都是她的幻想。
看来她没有别的选择了,只好用沙哑的声音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关于那个快递包裹的故事。
以及自从酒店那夜之后就开始的恐惧。和包裹一起,这恐惧也来到埃玛的家,来到一栋处在胡同最里面的、带着乡村风格木栅栏的小房子前,它来敲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