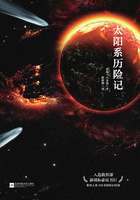提金斯发现这个年轻女人对这件事——赋予女性投票权——根本上的兴趣比他所认识到的要深得多。他没什么心情和年轻女人说话,但他回答的时候也绝非敷衍了事:
“我并不这么想。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手段,但你们的目的很愚蠢。”
她说:“我猜,你不知道格尔蒂·威尔逊,现在在我们家床上的那位,正在被警察通缉,并不仅仅因为昨天的事,而是在一串信箱里都放了爆炸物。”
他说:“我不知道……但这件事做得很恰当。她没有烧掉我的什么信,否则我可能会被惹恼,但这不会影响我同意她的做法。”
“你不觉得,”她真诚地问,“我们……妈妈和我……可能会因为窝藏她而受重刑?这对妈妈将会是无比可怕的霉运,因为她是个反对派……”
“我不知道刑罚的事,”提金斯说,“但我们最好尽快把那个女孩从你家转移出去……”
她说:“哦,你会帮忙吗?”
他回答:“当然,不能给你妈妈惹事。她写出了十八世纪以来唯一值得一读的小说。”
她停下来,真诚地说:“看。别做无耻轻薄的人,说什么投票不会给女人带来任何好处。女人过得太糟糕了。很糟糕,真的。如果你见过我所见过的那些景象,你就知道我不是在胡言乱语。”她的声音变得很低沉,眼里含着泪水。“可怜的女人真的是这样!”她说,“小小的不重要的生物。我们必须改变离婚法。我们必须得到更好的待遇。如果你知道我所知道的,你也没法忍受。”
她的感情让他感到恼火,因为它似乎建立了一种兄弟般的亲密感,而他现在并不想要这种感觉。除了在熟人面前,女人并不展示她们的感情。他干巴巴地说:
“我敢说,我没法忍受,但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所以,我可以!”
她带着深深的失望说:“哦,你是个讨厌鬼!我不应该为说了这话求你原谅。我不相信你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你只是出于无心。”
这又是一个西尔维娅式的控诉,提金斯又皱了皱眉。她解释道:
“你不知道皮米里科军服工厂工人的事情,不然,你就不会说投票对女人来说没用了。”
“这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提金斯说,“我收到过关于这件事的公文,我记得当时想,没有比这更明确表明投票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的迹象了。”
“我们不可能在说同一件事。”她说。
“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他回答道,“皮米里科军服工厂在威斯敏斯特的选区。陆军副部长是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上次选举的时候,他需要的多数选票是六百张。军服工厂雇佣了七百个男人,每小时一先令六便士,所有这些男人在威斯敏斯特都有选票。这七百个男人写信给陆军副部长,说如果他们的薪水没有涨到两先令,他们就会在下次选举彻底投反对票……”
温诺普小姐感叹道:“啊,那么!”
“所以,”提金斯说,“副部长炒了这七百个每小时拿十八便士的男人鱿鱼,雇了七百个女人,每小时十便士。投票权给这七百个男人带来了什么好处?选票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吗?”
温诺普小姐想了想,提金斯为了阻止她指出他的错误[1],飞快地说:
“现在,如果这七百个女人得到了这个国家其他被不公对待、努力劳作的女性的支持,威胁副部长,烧了他的邮筒,把他乡间住宅周围的高尔夫球草地上的草都剪了,下周她们的薪水会涨到半个克朗[2]。这是唯一直截了当的办法。这就是封建系统的运作办法。”
“哦,但我们不会剪高尔夫草地的,”温诺普小姐说,“至少W.S.P.U[3]前两天刚讨论过,认为任何这么不正派的事情都会让我们太不受欢迎。我本人倒是支持。”
提金斯哼哼道:“真让人恼火,看到女性一旦进了议会就像男人一样一头糨糊,害怕面对直截了当的事情!……”
“顺便说,”女孩打断道,“你明天不能把我们的马卖了。你忘了,明天是周日。”
“那我就得周一卖了。那么,”提金斯说,“封建系统的问题是……”
刚刚结束午饭——那是一顿很不错的午饭。冷羊肉配新鲜土豆和薄荷酱,用柔滑得像亲吻一样的白酒醋做的薄荷酱,波尔多红葡萄酒很好入口,波特酒比那还要好。温诺普夫人已经又能雇得起已故老教授的酒商了……温诺普小姐亲自去接了电话……
这小屋毫无疑问是栋便宜房子,因为它很老,宽敞而舒适。但也毫无疑问,她们在这些低矮的房间上花了不少力气。餐厅四面都有窗子,一根大梁贯穿屋顶。餐具是在减价的时候买的,玻璃杯都是老雕花玻璃做的。火炉的两旁各是一把单人扶手沙发。花园里,小径铺着红砖,种着向日葵、蜀葵和深红色的剑兰。花园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花园门很结实。
对提金斯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努力。这个女人,几年前一分钱都没有,在最悲惨的情境下,以收入最微薄的方式[4]维持生计。这代表了曾经付出的多少努力啊!这难道不代表现在的努力吗?还有个男孩在伊顿读书……这是愚蠢但勇敢的努力。
温诺普夫人坐在他对面那把单人扶手沙发上,了不起的女主人,了不起的女士。她很有精神,横冲直撞,但是有些疲惫,像一匹疲惫的老马,需要三个男人才能在马厩前面的草坪上给它装上挽具,像牡马一样迈开步子,却很快就慢下脚步。她脸色疲惫,真的,红扑扑的脸颊气色不错,但皱纹有些下垂。她可以舒服地坐在那里,丰满的手上盖着黑色蕾丝披肩,从她大腿两旁垂落下来,就像任何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了不起的女士一样悠闲地坐着。但在午饭的时候,她说她过去四年每天都写上八个小时——直到今天——一天都没有耽误。当天是周六,她没有社论要写。
“啊,我亲爱的孩子,”她对他说,“我太佩服你了,除了你父亲的儿子我不会佩服任何人。甚至连……都不。”她说出了她最尊重的人的名字。“这是事实。”她加了一句。不过这样,即使在午饭桌上,她也深深地陷入了不切实际的论调中,说了不少错得离谱的话,大部分都是关于公共事务的。这都意味着了不起的履历。
他坐在那里,咖啡和波特酒放在身边一张小桌子上。这间屋子现在是他的了。
她说:“我最亲爱的孩子……你有那么多事要做。你觉得,你今晚真的要带女孩们去普利姆索尔吗?她们又年轻又不为人着想。工作更重要。”
提金斯说:“距离并不远……”
“你会发现挺远的,”她幽默地说,“从谭德顿过去还有二十英里。如果你等到十点月亮落了才走,五点之前就没法回来,就算不发生什么事故……马的状况还好,不过……”
提金斯说:“温诺普夫人,我应该告诉你,人们在说我和你女儿之间的闲话。讲得很难听!”
她把头转向他,有点僵硬,但她只是回过了神。
“呃?”她说,然后道,“哦!那个高尔夫球场的事情……那一定看起来很令人怀疑。我敢说,你为了把他们从她身上引开,和警察之间肯定也闹得不小。”她深沉地思考了一阵,像个老神父。
“哦,你会没事的。”她说。
“我得告诉你,”他坚持说,“这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我想我不应该在这里。”
“不在这里!”她叫起来,“为什么?除此以外,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你该去?你跟你妻子合不来,我知道。她一直性格都不太好。除了瓦伦汀和我,谁还能把你照顾得这么好?”
在这一记尖锐的重击下——因为,说到底,提金斯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如他对妻子的名声来得在乎——提金斯有些尖锐地问温诺普夫人为什么说西尔维娅性格不好。她有点不满,带着困意说:
“我亲爱的孩子,没什么原因!我猜测你们之间有些分歧。这是我的观察。然后,既然你很明显性格不错,那就一定是她性格不好。就是这样,我向你保证。”
提金斯松了一口气,他的固执又复苏了。他喜欢这个家,他喜欢这个环境,他喜欢它的朴实节俭、家具的选择、光线从一扇窗子射到另一扇窗子、辛勤工作后的倦意、母女之间的关爱。实际上,还有她们二人对他的关爱。他下定决心,如果他可以的话,不要坏了这家女儿的名声。
正派的人,他认为,不会做这种事情。他有些介意地想起他和坎皮恩将军在更衣室的对话。他似乎又看到了那裂纹的洗手池放置在精制的橡木架子上。温诺普夫人的脸色变得更灰了,鼻子勾得更弯了,有些可憎!她时不时点点头,要么是为了表示她在听,要么就只是困了。
“我亲爱的孩子,”她最后开口说,“把这种事扣在你头上真是太可恨了。我可以看出来。但我似乎一生都浸在谣言丑闻里。每个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女人都有这种感觉……现在它不再重要了。”她用力点得头都要掉了。然后,她开始说:“我不觉得……我真的不觉得,我能在你的名声这件事上帮忙。我如果能帮就会帮的,相信我……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得维持这个家,得喂饱我的孩子,送他们去上学。我不能把我的脑子都用来想别人的麻烦事……”
她突然清醒了过来,从椅子里一站而起。
“但我是个多么讨厌的人啊!”她说,突然地,蹦出的语气腔调和她女儿一模一样。随后,她穿着有维多利亚女王气质的披肩和长裙,飘到提金斯的高背椅后面,弯下腰抚摸了一下他右边太阳穴上的头发。
“我亲爱的孩子,”她说,“活着是件痛苦的事。我是个老小说家,我知道。你在那为了拯救一团糟的国家努力工作,把命都要送了,不管不顾地把你个人名誉丢在一边……迪兹[5]在我们的一次招待会上亲口对我这么说的。‘我在这里,温诺普夫人,’他说……然后……”她迟疑了一下,但她又努着力说,“我亲爱的孩子,”她轻声细语着,弯下腰来,把头靠近他的耳朵,“我亲爱的孩子,这没关系,这真的没关系。你会没事的。唯一要紧的是把事做好。相信一个活得非常艰苦的老女人的话。‘辛苦钱[6]’,像海军里说的那样。听起来像虚伪的说教,但这是唯一的真理……你会在那其中找到慰藉。你会没事的,或者你不会。那就得看上帝对你仁不仁慈了。但那没关系,相信我: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7]”她又陷入了其他的思考。她为新小说的情节感到不安,很想回去继续思考这件事。她站着盯着那张照片,早已褪色褪得很厉害了,照片上是她丈夫,留着连鬓胡子,衬衫胸前的部分尤其宽大,但她继续带着下意识的温柔抚摸着提金斯的太阳穴。
这让提金斯一直坐在那里。他很清楚他眼里有泪水。这温柔他几乎承受不了,而他心底里其实是个非常直率、简单、敏感的人。当他在剧院看到温柔的爱情场面之后,总是会双眼含泪,所以他避免去戏院。他两度想应不应该再试一次站起来,虽然这几乎超越了他的能力。他想要静静坐着。
抚摸停下了,他挣扎着站起身来。
“温诺普夫人,”他看着她说道,“这完全正确。我不应该在意那些蠢猪怎么说我,但我在意。你对我说的这番话我会考虑,等我记在脑子里……”
她说:“是的!是的!我亲爱的。”然后继续盯着照片看。
“但是,”提金斯说,他牵起她戴着连指手套的手,带她回到她的椅子里,“我现在担心的并不是我自己的名声,而是你女儿瓦伦汀的。”
她陷入高高的椅子里,像个气球,然后放松了下来。
“瓦尔的名声!”她说,“哦!你的意思是他们会把她从访客簿里划掉。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她仍然长久地陷在思考中。
瓦伦汀就在房间里,悄悄地笑了笑。她刚才去给那个杂务工送了午饭,仍然被他对提金斯的称赞逗得发笑。
“你有了个仰慕者,”她对提金斯说,“‘给那个该死的马肚带打眼的样子,’他继续说道,‘就像个了不起的老叨木鸟敲着一棵空木头!’他喝着一品脱啤酒,边喘边这么说。”她继续叙述乔尔的古怪有趣,这很吸引她。她告诉提金斯叨木鸟[8]是肯特方言里的绿背啄木鸟,然后说:
“你在德国没有朋友吧?”她开始清理桌子。
提金斯说:“有,我妻子在德国,在一个叫罗布施德的地方。”
她把一摞碟子放在一个黑色、上了漆的托盘里。
“真对不起。”她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深深的悔恨,“都赖天才的电话机聪明的蠢劲[9]。那我收到的一封电报就是给你的。我以为那是关于妈妈的专栏的事。电报通常带着的都是报纸名字的缩写,也挺像提金斯的,那个寄电报的女孩叫作霍普赛德。看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我以为是跟德国政治有关,我想妈妈会看得懂的……你们俩不会都困了吧,有吗?”
提金斯睁开眼睛。女孩站在他正前方,从桌子那边走过来的。她拿着一张纸,上面是她抄下来的消息。他眼前一片模糊,字都叠在了一起,消息是这样的:
“得。但确保接线员跟你一起来。西尔维娅·霍普赛德 德国。”
提金斯向后靠着,长时间盯着这些字。它们看起来毫无意义。女孩把纸放在他的膝盖上,走回了餐桌。他想象女孩在电话里和这些无法理解的字句纠缠不清的样子。
“当然,如果我有点脑子,”女孩说,“我应该知道,这不可能是关于妈妈的专栏的留言。她从来不在周六收这种电报。”
提金斯听到他自己清楚、大声、一字一顿地宣告:
“这意味着我星期二要去我妻子那里,带上她的女仆,跟我一起去。”
“幸运的家伙!”女孩说,“我希望我是你就好了。我从来没踏上过歌德和罗莎·卢森堡的故乡。”她托盘上托着一大堆盘子,桌布搭在上臂上,走开了。他隐约地意识到,她在那之前已经用一个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把面包屑刷干净了。她干活十分迅捷,一直在说话。这来自做女佣的经历。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士需要花上两倍的时间,而且如果她试着说话的话,话一定会漏掉一半。效率!她刚刚反应过来,他要回到西尔维娅身边,当然,也是回到地狱!那确实就是地狱。如果一个恶毒而高超的魔鬼……虽然魔鬼当然很蠢,把焰火和硫黄当作玩具。可能只有上帝才能,正确地设计出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如果上帝希望(谁也不能反对,只能希望他不要这么想!)为了他,克里斯托弗·提金斯,这么设计,深不见底的永恒里充满着令人疲惫的绝望……但上帝已经这么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惩罚。为了什么?既然上帝是公正的,谁知道,在上帝眼里,他犯下了什么罪恶,需要重罚?……那么说到底,上帝可能在惩罚性方面的罪过是毫不留情的。
他们早餐室的图景突然重新回到了他的脑子里,深深地烙印在上面,还有各种黄铜的、电气的玩意,煮蛋器、烤面包机、烤炉、热水壶,他讨厌它们愚蠢的无效率;一大堆一大堆的温室花朵,他讨厌它们带着异国情调的蜡色!——他讨厌的陶瓷镶板和镶在画框里的蹩脚的照片——当然,确实是真货,我亲爱的,苏富比认证过的——照片上是微微发红的女人们戴着假的盖恩斯伯勒帽子,卖着鲭鱼或者金雀花。一件他讨厌的结婚礼物。赛特斯维特夫人穿着睡裙,但戴着巨大的帽子,正在读《泰晤士报》,永远在急急地翻页,因为她没法静下来读任何一页。西尔维娅来回踱步,因为她没法静静地坐着,手上拿着一片吐司,或者把手背在身后。她很高,肤色白皙,像典型的道德败坏的德比冠军马一样优雅,充满活力。世代近亲繁殖只为一个目标:让某种类型的男人气得发疯……前后踱步,叫着:“我厌倦了!厌倦了!”有时候,甚至把早餐盘摔在地上……还有说话!永远在说话,惯常地,聪明地,说些蠢话;令人愤怒地常常说错,穿透力强得可怕,高喊着求人驳斥;一个绅士得回答他妻子的问题……他的前额一直感受到压力,保持坐着不动的决心,房间的装饰似乎在烧灼他的心。就在那里,现在朦胧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还有他前额上感到的压力……
温诺普夫人正在跟他说话。他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之后回答了什么。
“上帝!”他对自己说,“如果上帝惩罚的是性的罪恶,他确实是公正而难以捉摸的!”因为他和这个女人结婚前就发生了肉体关系,在火车车厢里,从杜克里斯来的路上。一个美得十分奢侈的女孩!
她当时肉体上的诱惑去了哪里?无法抗拒,稍稍向后倾,乡下的风景疾驰而过……他心里说,是她勾引了他。他的头脑说,这是他的主意。没有绅士会这么去想他们的妻子。
没有绅士会想……老天有眼。她当时一定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他过去四个月里一直在和这个念头抗争……他知道他现在已经跟这个念头抗争了四个月。麻木了,就沉浸在数字和波浪理论里……她最后的话是,她最后说的话:夜深了。她穿着一身白色,走进化妆室。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最后的话是关于孩子的……“假设”,她开始说……他不记得剩下的部分,但他记得她的眼睛,还有她摘下长长的白手套时候的动作……
他正在看着温诺普夫人的火炉,他想这是个品位上的错误,真的,夏天还把木头留在火炉里。但不然,你夏天要怎么对付一个火炉。在约克郡的小屋里,他们用涂了漆的小门遮上火炉。但这也很拥挤!
他对自己说:“老天!我中风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试了试他的腿……但他并没有中风。他想,那一定是刚才的思考中的痛苦对他的头脑来说过于剧烈,就像有些生理上的剧痛感受不到一样。就像秤一样,神经没办法测出超过某一个数值的量。然后,它们就没感觉了。一个被火车轧断了腿的流浪汉告诉他,他试着站起来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但随后痛觉又回来了……
他对仍在说话的温诺普夫人说:“请你原谅。我真的没听见你说了什么。”
温诺普夫人说:“我在说,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他说:“我真的非常抱歉,我刚才就是没听见这句话。我只是陷进了一点点麻烦,你知道。”
她说:“我知道,我知道。心思到处跑,但我希望你能听着。我得去工作了,你也是。我说,茶点之后,你和瓦伦汀会走到莱伊去拿你们的行李。”
他用力想着,因为在他心里,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愉悦:阳光照在远处金字塔形状的红色屋顶上,他们从长而斜的绿色山丘上向下走。上帝啊,是的,他想要室外的空气。提金斯说:
“我知道了。你要保护我们两个。你会蒙混过关的。”
温诺普夫人相当冷静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我要保护的是你!(这是你的原话!)对瓦伦汀来说,她给自己挖了坑,她非跳不可。我已经跟你说了一遍了,我没法再重复了。”
她停下来,然后,又费了点气力说:“被从蒙特比的访客簿上划掉,”她说,“这并不让人愉快。他们开很有趣的派对。但我这么大年纪已经懒得管了,并且他们因想念我而说的话超过我想念他们的。当然,我替我的女儿遮风挡雨。当然,我支持瓦伦汀,无论艰难险阻。我会支持她,如果她和一个已婚男人住在一起,或者有了私生子的话。但我不赞成,我不赞成这群妇女参政权论者。我鄙视她们的诉求,我厌恨她们的手段。我不认为年轻女孩应该和陌生男人说话。瓦伦汀跟你说话了,看看这给你造成了多大困扰。我不赞成。我是个女人,但我找到了自己的办法,其他女人如果愿意或者有这么多能量也可以。我不赞成!但别以为我会出卖任何妇女参政权论者,个人也好,组织也好,我的瓦伦汀或者任何其他人。别以为我会说一句值得被人传播的反对她们的话。你不会传播。或者指望我会写一个字反对她们。不,我也是个女人,我站在我们女人这边!”
她精力满满地站起来。
“我得去写我的小说了,”她说,“我今晚得把星期一的连载通过铁路寄走。你可以去我的书房,瓦伦汀会给你笔、墨水、十二种不同的笔头。你会发现屋子里都是温诺普教授的书。你得忍受瓦伦汀在小厅打字的声音。我有两个连载,一个在誊录,另一个在写手稿。”
提金斯说:“但是你呢!”
“我,”她叫起来,“我会在卧室在我的膝盖上写。我是个女人,我能这么做。你是个男人,得要有坐垫的椅子和一个庇护所……你感觉能工作吗?那你可以干到五点。瓦伦汀那时候会去泡茶。五点半你会出发去莱伊。你在七点可以带着行李和你的朋友还有你朋友的行李回来。”
她蛮横地用这么一句话让他闭嘴。
“别傻了。你朋友一定会更喜欢这间房子和瓦伦汀的饭菜超过小酒馆和小酒馆的饭菜。而且他还可以省钱……这不是多出来的麻烦。我猜你朋友不会告发楼上那个可怜的支持妇女参政的小女孩。”她停了一下又说,“你得确定你能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然后驾车把瓦伦汀和她送去那个地方……这件事很有必要,因为那个女孩不敢坐火车,而我们在那里有熟人,从来没跟妇女参政权论者有过牵扯。那个女孩可以在那里躲藏一段时间……但如果你来不及完成工作,我就自己送她们去……”
她又让提金斯闭嘴,这次是果断地。
“我告诉你了,这不是多出来的麻烦。瓦伦汀和我总是自己铺自己的床的。我们不喜欢用人动我们的私人物品。我们住在这一块得到的帮助比我们需要的还多出三倍。我们喜欢这里。你给我们添的麻烦可能是额外帮了忙。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也可以找用人。但是瓦伦汀和我晚上喜欢单独待在这间屋子里。我们很喜欢对方。”
她走到门边,又飘回来,说:“你知道,我没法把那个不幸的女人和她丈夫的事从我脑袋里忘掉。我们都得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然后她开始叫了起来,“但是,老天,我让你没法工作了。书房在那边,穿过那扇门。”
她匆匆穿过另一个门廊,毫无疑问,她走过了一个走道,喊着:
“瓦伦汀!瓦伦汀!去书房找克里斯托弗。现在……在……”她的声音消失了。
注释:
[1]这一错误可能是因为一九一八年之前英国女性都没有投票权,所以副部长炒了这七百个男人的鱿鱼等同于丢了七百张选票,同样会失去他的席位。
[2]克朗是英国的旧币,半克朗等于两先令六便士。
[3]W.S.P.U即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是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缩写。
[4]指温诺普夫人以写作为生。
[5]指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两度出任首相。
[6]原文是“Hard lying money”,指给需要忍受特别恶劣的天气和工作环境的水手发的奖金。
[7]出自《圣经·申命记》。
[8]原文为“yaffle”,是一个方言词汇。
[9]即电话因为通话质量不好容易造成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