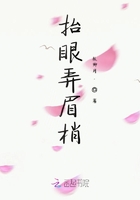武昌的巡抚公馆内堂一片混乱,这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个武昌的大小官员,长毛兵临城下,官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外边的战事和个人的前途打算,堂子里一片嘈杂之声;坐在最里面的是湖北巡抚胡林翼和两江总督曾国藩,看着这样的场景二人也不时摇头。
就在这时,堂外的一声叫喊打破了喧嚣,“总……总督大人,巡抚大人,汉阳、汉口遭长毛偷袭,失守了!”门外一员遍体鳞伤的湘军将官跪倒在地上,大声喊道。
闻此消息,堂内顿时炸开了锅,刘蓉狠狠地拍了几下桌子,堂内才勉强恢复了安静。
曾、胡二人也是大惊,门外跪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负责汉阳防务的湘军将领张诗日;张诗日是曾国荃的部将,之前随曾国荃部进入安徽,负责留守太湖,后来曾国荃兵败三河,太平军大举反攻,张诗日守不住太湖,只得退回湖北,奉命负责镇守汉阳,而现在,满身是伤的他正狼狈地跪在堂外谢罪,身上的血水还在滴滴下落。
“冯逆的主力不是在东湖吗?怎么又跑到江北去了?”曾国藩愤而起身责问道。
“回大人,江北的英酋趁我军主力驰援东湖之际,率贼众进犯,镇守汉口的副都统巴扬阿和左翼的孙振铨‘宝字营’临阵溃逃,我军势单力孤根本扛不住陈逆的进攻……”张诗日委屈地说道,“大人,汉阳守军已全军覆没,卑职本想以身殉国,是手下们拼死将卑职救上小船的。”
“长毛真是阴险至极,此次进犯多路配合,必是有备而来。绿营的人也真是不堪大用!”胡林翼愤愤地说道。
“老帅,汉阳和汉口丢失,武昌很快就会变成孤城一座,您看是不是?”曾、胡身旁的赵烈文开口道。他的意思是劝曾国藩尽早离城避难。
“我军败了吗?长毛只不过是侥幸得手罢了,我们在东湖还有两万五千人,加上城内的将士也是五万多人,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本督相信武昌可守。”曾国藩说道。尽管曾嘴上这么说,但场下众人却都连连摇头,对防守武昌毫无信心。
“老帅,我军水师已败,长江制水权已失,再守下去怕是也希望无多,”赵烈文低声说道,“老帅,您一定要三思啊,困死在这里根本不值得。”
曾国藩满脸无奈,他把头转向老朋友胡林翼,胡林翼说道:“涤帅,您是湘军的主帅,也是这支力量的支柱,只要您不出事,我湘军就有未来和希望,现在冯逆下了决心要打破武昌,这是想聚歼我军,涤帅您要是留下就正合了长毛之意啊!”
刘蓉突然开口问道:“胡公何知冯逆下决心要攻武昌?”
胡林翼没有答话,曾国藩也没追问,只是说道:“贶生,这个时候本督走了你怎么办?本督得留下与你共赴国难,要不天下人如何看我曾国藩?”
胡林翼一听赶紧又开始劝,其余的幕僚们也七嘴八舌地说着撤退的理由,曾国藩难敌众口,只得表示再做考虑;其实他的心里未尝没想过逃走,但碍于面子和名声,他不愿背负丢弃老朋友的骂名。
心乱如麻的曾国藩登上黄鹤楼,江北的烽烟还未消散,太平军的旗帜已经插进了汉阳和汉口;是留是走?曾一时拿不定注意。就在这时,突然江面上几艘太平军火轮船轰鸣着驶过,速度之快,前所未见。这让曾国藩大吃一惊,长毛竟有如此利器,想到这些顿时胸口疼痛颤抖不已,一旁的亲兵见状赶紧将他扶了下来。
曾国藩愤懑地提笔在日记里写道:“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他暗暗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湘军也用上这样的装备,他想重建湘军,但眼下被困武昌却什么都做不了,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这个想法终于又一次涌上了心头。
就在武昌城东北的东湖要塞聚集了五六万等待决战的人马之际,江北陈玉成和江南黄文金两路人马同时进军,黄文金部汇合江西的朱洪音部,先后拿下了通山、崇阳、通城、蒲圻四地,切断了武昌粮道;陈玉成则趁我在东湖与湘军主力对峙时,在江北对汉阳和汉口两座重镇发动了攻势。
汉阳城东筑有木城,西门也有炮垒,南门有外壕,还构造了包括龟山在内的外廊直至汉水河边,汉口城也筑有土垒配合防御,两地守备不可谓不严密;但陈玉成部发起进攻后不到半个时辰,毫无防备的汉阳、汉口守军即全线崩溃,陈玉成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汉阳和汉口。拿下了汉阳、汉口,武昌城三面被围,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
“殿下,英王部下求见!”侍卫喊道。
我摆摆手,很快一个身材魁梧的太平军将官走进账内,行礼道:“卑职俱天安邱远才,奉英王殿下之命,特来拜见城王千岁殿下。”
我示意他免礼,邱远才是陈玉成麾下的一员大将,受陈玉成委派乘船特来面见我,只见他开口说道:“城王殿下,英王已经挥师拿下了汉阳和汉口,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军随时可以发兵拿下武昌城。”邱远才说话时,脸上透着骄傲之情。
我瞧了他一眼,心想这个陈玉成也真敢夸下海口,武昌的城防岂是汉阳和汉口可以比较的,又有曾国藩亲自坐镇,重兵守卫;不过转念一想,陈玉成也算是少年英雄,谁人年少不轻狂?所以我好奇地问道:“一江之隔,不知英王打算如何进取武昌?”
“这个殿下可以放心,英王殿下说到做到;东湖防线的两万多妖军让您无法前进,只要我们从背后取下武昌,则这支妖军必定崩溃。”邱远才信心满满地说道。他这是在替陈玉成向我征求进攻武昌,陈玉成这是要夺打武汉的头功啊。
“英王这段时间连败江北妖军,一举夺取汉阳、汉口,屡立奇功,但连日作战将士们不免疲惫;再说曾妖头本人就在武昌城内,武昌必不好打,不如先行围困,待武昌守军困乏再攻也不迟吧!”我一脸怀疑地说道。其实我是故意这么说的,武昌城里城外尚有五万湘军,硬打免不了巨大的损失,虽说围困是上策,但谁不想早点拿下这座华中重镇,陈玉成他想打武昌就让他来打好了,无论他成不成,我都正好保存实力等最后与曾国藩决战时将其歼灭。
“殿下您是信不过我们?”邱远才有点不高兴,说道,“英王殿下说如果您不同意,他就当众立军令状,必取武昌。”
我看着他,说道:“好吧,既然英王有此信心,本王也不好再说什么。不知英王殿下打算哪天进攻,需不需要水师支援?”
邱远才一拱手,道:“殿下,英王有令,我军明日卯时攻武昌,主攻鲇鱼套,待我军进城后,英王想请城南的黄主将配合进攻。”
“这个好说,我一会儿就联络黄文金。”我说道。现在我的人马被阻在东湖以东,算是参加不了攻城战了,但同时我也牵制了相当数量的守军,为攻城部队减轻了不少压力。
“为什么这么急于攻城?” 我又问道。
“回殿下,英王说这一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军这段时间一直势如破竹,如果停下与妖军拉锯就会有损锐气,所以主张急攻;英王殿下还说,乙卯五年他就参与过进攻武昌,对这里尤其是鲇鱼套一带极为熟悉,说这里适于奇袭……”邱远才没再说下去。
说来历史上陈玉成与武昌还真是有缘,早年就是在进攻武昌的战役中展露锋芒,后来他为解安庆之围攻打武汉,却被外国人给“劝退”。不过现在尽管武汉被清政府划为通商口岸,但时候尚早,这里还没有发展起外国势力和租界。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同意了陈玉成的请战计划,同时命令城南的黄文金集结人马,随时准备配合进攻,而我的人马则继续对东湖要塞施加压力。
整个晚上我彻夜难寐,陈玉成的战斗力我心里清楚,但这次毕竟不同寻常;于是我索性披上衣服,走出大营来到江边,让手下人叫来了一艘小木船,准备乘船去上游看看在江北的他要如何攻城。
木船悄悄行至汉阳鹦鹉洲,只见已有大队太平军在岸边集结,他们也看到了远处的我,我立即打出“城殿”的旗帜示意,对面则打出了“英王”的旗帜。
只见他们从后面陆续搬出大批木筏,为首指挥的那个不是别人,正是陈玉成,只见他身着素服,他的部下大约五六百人也都轻装上阵没穿甲胄;很快他指挥手下们迅速放下木筏,大队人马乘着夜色下了长江向着对面的鲇鱼套驶去,整个过程居然十分安静,只有江水声在耳边荡漾。
就在这时邱远才也出来了,他在鹦鹉洲上集结了更多的人马,他们蓄势待发准备渡河,我知道这是陈玉成的后续部队。
悄悄渡过长江的陈玉成和他的几百死士汇集到了武昌西城门下,几个身手矫捷的战士像施展轻功一般三两下便徒手爬上了城楼,城上巡逻的清兵还在打着哈欠时便被他们放倒,不一会儿城上就扔下了绳子,越来越多的战士顺着绳索快速登了上去。
见此情景我心里大惊,这陈玉成这次真是神了,神不知鬼不觉就钻进城去了,守备武昌的清军居然没有一点反应。我见状赶紧让水手将船驶回东湖大营。
武昌攻城战一触即发,随行的周国贤似乎还没看够,听说我下令驶离,他不解地问道:“殿下,我们回去干什么?”
“武昌城破已是旦夕之间,现在正是痛击湘军的好时候,我们的人马岂能不管不顾?”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