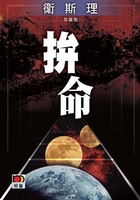在很多人眼里,798是艺术的代名词,是文艺工作者的天堂,各地文艺青年来京,不到798转一遭,简直枉来此地,简直是凡夫俗子。可在某些极端文青看来,798不过是三流艺术家向非艺术类人群献媚的地方,那里满墙的颜料,不是赤裸裸抄袭西方某个大家,就是将自己的情人深情描述一百遍,这些不要脸的破玩意儿,也就蒙蒙学理科的姑娘,内行人看在眼里,真叫个揪心。
极端文青对待798的态度,像极了北京大妈对待王府井的态度,北京人谁去王府井消费啊,那分明是蒙外地人的地方,北京人自己买衣服有动物园批发市场,吃小吃有护国寺和鼓楼大街,想追个时髦干脆去新光天地,那才叫真洋气。同理,极端文青们光顾798,只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给外地老同学做导游,一种是和非艺术类姑娘约会。
冬日的画廊,我身边的理科姑娘上来就要我解释啥是当代艺术。这是她和文艺青年约会的路数,她喜欢对我这种准极端文青的出身及爱好评头论足,并以此为引子一点点奚落文艺青年的阴暗,仿佛全天下我们这样的人都咬舌自尽了,她这样的女白领才能恢复学术界与无聊界的地位。
我站在一幅裸女图旁酝酿了两分钟,说:“当代艺术源自生活。”她说:“完啦?”我说:“可不完了。”她说:“还以为你要大吹一番呢,你们学艺术的不都挺高调的吗?”我说:“不是所有人都高调好吗?其实艺术哪儿有那么高深,就是你们这些人把艺术给神话了,艺术也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映现而已。”她说:“你这是变相高调,‘艺术源自生活’的后半句是‘艺术高于生活’,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还映现,你看看这些画,哪些是映现生活的?都是故意夸大和扭曲生活的,还有这一张,你看,赤裸裸地意淫大胸。”我说:“小声点儿,人家这个画家是女的。”她气势不减:“我就说嘛,她肯定没胸。”
她接着说:“那你给我说说古典绘画和现代绘画的区别。”我反将一军:“你先说你怎么理解的。”她说:“我觉得现代绘画就是大家比赛谁画得不像,就跟毕加索一样,早期画得挺好看,后来越画越像儿童画,为什么啊?难道就为了个返璞归真?”我说:“嗯,这么说吧,用你能理解的说法来讲,古典绘画就是写实,画得越像越成功,后来照相机出来了,画家没饭辙了,开始加大主观处理成分,过程跟现在的修图软件差不多,淡化客观事物,加入更多个人思想的表达。个人思想表达到极致时,开始扭曲和纠结。就和人生一样,一开始都是清纯的、质朴的,后来开始欺骗与自我欺骗,最后觉得什么都是唯心的。我这么说你可听得明白?”她说:“真扯,你这种观点发到网上肯定招来一堆骂。”我说:“这年头在网上说什么不招人骂?可总得有人说呀,何况艺术本来就没什么标准,没你们学生物科技的那么呆板。”她睁大眼:“哎呀,你还拽起来了,我们学生物科技的怎么呆板了?你再说一个试试看。”我说:“我的意思是学生物的严谨,比艺术严谨……好吧,我刚才扯的那些确实招骂。”
画廊门口,她清了清高跟鞋尖上的尘垢,顺便谈起艺术圈的丑陋,主指男女作风问题。她说:“你承不承认你们学艺术的都很乱。”我说:“不能叫乱吧,应该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她说:“嚯,这个也能理性看待,你们要理性能胡来吗?”我说:“我是说理性分析这种现象。我问你个问题啊,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她望着我说:“你不会说是性吧?”我双手摊向她:“是姑娘。”她眉头紧锁,表示不解。我说:“艺术家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是姑娘,姑娘是世间最美的事物,是艺术家灵感最好的源泉,所以你看毕加索爱了一辈子姑娘,也画了一辈子好画。”她说:“你们离了姑娘就不会画画啦?说那么多不还是个色吗?女人也有当画家的,她们难道也像你们男人一样靠着下半身才能搞创作吗?说好听点儿,你这是泛性论,说难听点儿,就是个色。”我说:“其实女画家也……”她说:“欸,欸,你看你看,下雪了。”我说:“好吧,下雪了。”她说:“你们文青下雪了会出来玩吗?”我说:“文青也是人啊,为什么下雪不能出来玩!”
她不依不饶:“我不明白,性对你们男人真有那么大魔力吗?你看啊,你们平时讲笑话讲这个,画画时画这个,还经常凑在一起看这种片子,哪个小姑娘冲你们乐一下,你们恨不得立刻把她赶上床,你说你们是不是这样?”我笑起来,说:“干吗非得说这个?”她说:“你看,你还笑,笑就证明我没说错。”我说:“我笑是没见过你这样的,你一个名牌大学出身的大姑娘在大街上聊上床,还真有你的。”她说:“我也没说性不对啊,只是你们男人分明就是下半身动物,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一遇到下半身,立马投降,什么坐怀不乱、清心寡欲,都是瞎扯淡。”我说:“我从生理角度辩护一下这一点啊。你也知道,男人性欲最强的年龄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女人是三十岁到五十岁,对吧?所以你不能只站在一个立场上说话。”她说:“就算是这样,也不公平,哦,我们女人最好的年华都给了你们这帮禽兽享受,我们自己想用的时候你们又不理我们,找小姑娘去了,有些干脆还不举了……”我抬眼看看身边的路人,凑近她耳根说:“今天是我娘亲的生日,咱能不能不说这个?”
“那结了婚呢?你们这些学艺术的结了婚也不怎么安分。”她顺理成章地聊到婚后出轨,亮出撒手锏。
说实话,我被难住了,这种既聪明又残忍的姑娘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她不知道男人被问是否出轨就跟女人被问是否爱钱一样尴尬,稍有不慎,就会被戴上虚伪的帽子,可我又不能过分真诚,否则我和她的关系很可能就此夭折。
我鼓足勇气,站定说:“现行的道德体系下,出轨是错,这无可辩驳。”她说:“那为什么现在婚后出轨的男人那么多,大多还是有文化的人?明知是错,还背着家人在外面乱搞,这是为什么?”我说:“大概是空虚吧,不过也有不乱搞的,你别总把男人看成一个德行。据我所知,很多搞数学理论和宏观物理学的男人就守身如玉,他们钻在实验室里捣鼓半辈子,对他们来说,屋外有一个老娘儿们就够烦了。另外,男人也会成长,年轻的时候不可能真正理解幸福和性的关系,就好像很多玩摇滚的承认,直到自己有了女儿,才真正开始尊重女人,你们应该给男人一点儿信心。”
她瞟我一眼,瞟得我心里发毛,我望着她说:“是这个理吧?”她说:“好吧,放过你了。”我说:“嗯。”
雪开始下大,呼呼地往眼睛里钻,我提议去路边的咖啡馆躲躲,她嫌咖啡馆人多,坚持要我陪她散步。我站在路灯下给她整理帽子,发现整条街道就我们两个人,她噘着嘴巴看我,像地主家的二小姐看佃农家的大儿子。
我拍着她背后的雪说:“刚才咖啡馆门口的那个男生一直偷看你,你得意吧?”她说:“哪个?”我说:“就背红包那个,你看你看,进去了。”她说:“就那个啊,你看错了吧,人家怎么会看我?我今天裹得跟个企鹅似的。”我说:“不不,您盛装之下难掩春色。”她笑着推我一把说:“去你的!”我说:“还走吗?”她说:“走啊,难得有这么好的雪天,得好好跟你聊聊。”我帮她拎起包说:“得,走吧。”
她说:“刚才我问你出轨的问题是不是很过分?让你有点儿难堪。”我说:“不不,您拿捏得恰到好处。”她说:“你少装,我知道你们男生都爱面子,听不了女人问这些尖锐的问题。”我说:“可你还是问了呀,这说明你是真心想听我的看法。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才问这个,已经很仁义了,我,我很感动。”她说:“是吧,你看我也是读过书的人,别以为就你们文科生懂礼数。”我点头如捣蒜:“是的,是的,那依照您的路数,下面是不是该考察男人责任心、事业心之类的啦?”她说:“哇,你好聪明,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样的男人才算有责任心。”
我心里猛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面不改色地说:“责任心啊?”她说:“是啊,责任心,你怎么理解的?”我说:“我理解的责任心,就是豁得出去吧。你也说了,男人都爱面子,如果他肯为了你舍弃那些面子,那他就是对你负责任。”她沉默了五秒钟,说:“这个答得不错。”我说:“你呢?像你这样的职业女性是怎么分辨好男人与坏男人的?单纯以责任心分辨吗?”她说:“那不一定,有责任心的男人不一定都是好人,有些人对自己人过分地照顾,也意味着对别人冷漠,这种人其实也属于自私的。”我说:“比如愚孝,你们女人都讨厌这个。”她说:“这算一个,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总之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那算不上好人。”我说:“女孩子能看到这一点,很难得。”她说:“你什么意思,你这是看不起女人了?”我说:“不是,我是说很多男人都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们文青吗?”她说。我问:“为什么?”她抬头望着前方:“不是说文艺不好,只是太文艺的人总有股子清高,总觉得自己品位特高,别人都是俗人,就他们雅,这股子劲儿特别让人讨厌。”我说:“你说得有道理,很多人确实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不限于文青吧,应该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她说:“怎么讲?”我说:“嗯……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在多数文青眼里,只有文艺才是高端的,因为他们自信找到了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在多数理科生眼里,只有科技才是高端的,因为他们自信掌握了科技就掌握了人类的未来;在多数商人眼里,只有金钱才是高端的,因为他们自信获得了金钱就获得了能力和地位;在多数律师眼里,只有法制才是高端的,因为他们自信法制是规范人类文明的第一利器,等等等等,这就是价值通病。”她说:“你说的这些不能代表全部,只能代表一部分狂妄的人,我承认这样的人有,而且不少,但你不能否认你们文青这类通病最严重。”我说:“我承认我也沾染了这类通病,但我比较看重人性。说到底,真正左右这个世界的,不是什么艺术,不是什么科技,不是什么法制,不是什么金融,而是人,也就是人性,你看看好莱坞拍的那些描述未来的科幻片,科技、法制、经济发展到极致后,最后博弈的对象,还是人性。”她笑起来:“以人为本哈,挺老土的,不过也挺实在,唉,人真是种复杂的动物。”我说:“是啊,所以咱们不能用一种方式去定义别人,比如说我是个医生,我看人习惯性地以身体机能为标准,可身体以外呢,我懂的不一定比人家多。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别人,只能证明自己的狭隘、片面和无知。”她睁大眼睛,吐出一口气说:“说真的,要不是和你聊天,单单就接触你这个人,还真以为你就是个精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