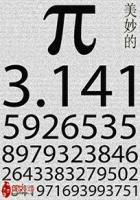《华山女》和《谢自然诗》是姊妹篇。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让我们看看华山女究竟是什么样角色: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着黄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全诗一韵到底,和《谢自然诗》比起来,《华山女》的形象多于议论。其中有的情节,却需要揣摩。
唐代的长安城本来十分热闹,而佛道两教的盛行,和尚、道士的活跃,又使这座帝城到处传来说经之声,撞钟吹螺闹嚷嚷地深入宫廷。诗人先在次句中标出“宫廷”,然后再说民间,隐寓上行下效之意。僧人说法,必以祸福胁诱,下民无知,闻而密接聚会,如同浮萍推排。黄衣道士也想借此炫耀,听道的人却寥若晨星。这一句是写道教势力不及佛教,也是为了逗引下面主角的出场。
有一个来自华山的女道士,为了驱除佛教,于梳妆之后来到道观。她长得颈白颊红,眉毛画得长而黑,其人之妖冶可见。她升座后,不许道观大门敞开,闲人进入。这样,外界便无从知道道观内部的活动了。
不晓得是谁暗中泄露了消息,顿时像响雷一样轰动了全城,把僧寺中听经的人都转移过来,男的乘马,女的坐车,整座道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后来的人已无隙地,一些妇女纷纷解下金玉首饰相赠送。前面原说听黄衣道士讲道的人很少,来了个华山女,卖座率就爆满了。
这消息又被玉皇得知,便由宫监诏传进宫,说是宫中后妃都想见见她的风采。她在宫中住了几天后,玉皇才允许她回去,于是乘龙驾鹤由天上重返人间。玉皇指宫中的皇帝,青冥指深宫。因为事涉至尊,所以故意写得似幻似真,似仙似人。一些豪门中的子弟,平时本来不晓得修道不修道,这时却像热锅上蚂蚁,向华山女百般缠绕,络绎不绝。华山女却处于云窗雾阁之中,把翠幔金屏重重遮蔽,只教人恍恍惚惚,难以窥测。
最后两句,倒真使人感到恍惚:从字面看,是说那些豪门子弟因仙俗悬殊,无法接近华山女,所以白白地枉通消息,空致殷勤,实际是要读者从夹缝里看。如果华山女真是不许那些豪门子弟入幕,则“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两句,何必写得那么神秘诡异?前人已经看出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朱彝尊便说:“女道士乃作柔情语,然风致全在此。”朱熹《韩文考异》说:“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宽容)如此。非也。此正讥其衒姿色,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失,岂真以神仙处之哉?”说得极为警辟。王元启也以“云窗”以下“皆亵慢语”。
唐代女道士的浪漫生活,原很普遍,有的还能作诗,著名的有李冶与鱼玄机,诗中常抒发艳情,鱼玄机就写过“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之诗。韩愈深恶佛道,人又好奇,写入诗篇,自必加上一些虚构和渲染。从文学的眼光看,这首诗写得很出色,既浓艳又飘忽,仿佛地上的洛神,从深宫的帝王到豪门的子弟,都为这个华山女而倾倒,而又以偏锋虚笔加强传奇的色彩。
我们看了全诗,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疑问和遐想:华山女既然是世代奉道,志在驱除异教,那应该将她写得庄严矜持,却偏要写她“白咽红颊长眉青”。升座讲道,应该敞开大门,却偏要紧关。在道观内传道,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诗中却说“不知谁人暗相报”。消息传开后,来的却是人山人海,难道真因为她道行高深?“抽钗脱钏解环佩”,是听众中妇女送的,难道没有男子送的?而且女道士何必受人的金玉首饰?下诏召唤,说是后妃要见华山女的容颜,出宫离去,却须经过玉皇的颔首许可。“仙缘难攀俗缘重”,正见得这种仙缘比俗缘还污浊。“浪凭青鸟通丁宁”,其实早已暗通丁宁了。查慎行评韩诗末二句云:“二句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较含吐蕴藉。”杜甫《丽人行》的末二句为“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这是写杨国忠未到曲江时,别人还能看到虢国夫人,等到杨国忠一到,别人因恐遭国忠的恼怒,就不敢走近虢国夫人。杜诗还是正面写来,韩诗则用欲盖弥彰法,所以说“更较含吐蕴藉”。浦起龙《读杜心解》评《丽人行》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因而发挥了讽刺艺术的最大效果。这首《华山女》也是这样。从头到尾,不见谴责呵斥之词,所以有人要说韩公对华山女有“假借”意,但我们读完全诗,这个华山女是何等样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什么样子,不就历历在目,而有皮里阳秋之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