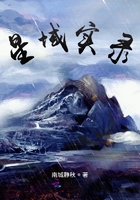荒唐的十几年似乎翻几个脸就过去了,这些脸,有青涩有明媚有妖艳有端庄,等我被声音拉回神时才发现,抱我进车里的不是大哥,司机也不是往常的司机。一个高挑少年一个大眼睛姑娘。
“沈二小姐,我们接您去与魂铺。”
“你好,我是亓景,与魂契簿的现主人,来接你去与魂铺,在那里有你要见的人。”
我觉得奇怪,这个人说的我一概没听过,而且脸开始感到刺痛,我对着后车镜,摸了摸脸,满手鲜血,后视镜中我千疮百孔烂肉中参着蠕虫。我心中大骇,想看得真切,欲把头伸出窗外,少年却不知念了什么咒语定住我接着用手捂住我的眼。
“您先闭眼,不要一直想着自己死的模样,死后状态都是由意念化成的。多想点好看的时候。”
我有预感我已经死了很久,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过程,于是问两人:
“谁要见我。”
“你曾在与魂铺留下契约,要见害你的人。今天是那人转世后的绝命之日,就带你过去见他。”
“我没有转世?”
“你只剩三魂四魄,无法转世。丢失一些记忆也是这个原因,不过你要见的人晚上就会由鬼差送到与魂铺,到时你可以问问。”
车子行在一片混沌中,等停下来时,就看到大黑漆木门,依稀透过的光亮可见门口两尊石像,石像模样凶狠奇怪,石像上方挂着灯,灯下一串玲,顺着玲往后看就是门上匾三大字——与魂铺。
漆黑的大门打开,走出一个红衣公子,这个公子像是从仙侠画本里走出的非仙非魔只能一笔而过不敢深究的美人,好像他所到之处都是人间仙境,眸光一暼却又是场祸国殃民。就在黑暗中深深得看一眼,心中所有都是剩那抹红色的震撼,等我移开眼再看镜中自己时,惊讶镜中已是妙龄时面若桃花的少女,未涂脂粉已经魅人,可惜一双眼睛没有春夏只余秋冬,在红衣公子面前,诚惶诚恐,心中怯弱,告诉自己无法直视。
进了正堂,有魁梧壮汉站立等候,司机过去和他说了几句,壮汉便匆匆离去,再回来时背着刚刚在路途睡着的大眼睛姑娘。壮汉勾着腰,为了小姑娘趴着睡能舒服点,面朝尘土青石。看着他们的一步一步,就让人想起此生最温情的一路。
“大风?”
刚刚还在车上酣睡的小姑娘含糊得嘟囔一声,挠挠头拍拍脸然后晃荡了下腿示意要下来,嘴上小声的抱怨:
“都和容辞说了,到了就喊我起来,晚饭还没吃呢。”
站在地上后,退了两步,对着壮汉作揖,道:
“谢谢大风。”
这几个人看着奇怪,从进来时就看得出这些人对小姑娘的尊敬宠爱,此时小姑娘却毕恭毕敬道谢,完全没有娇纵小姐模样。小姑娘行完礼,名大风的壮汉笑笑点头,然后从不知哪个兜里掏出一盒点心和一只烤鸡,开口:
“小殿下,先垫垫肚子。”
“谢谢。”又是一礼。
有小童端来茶水,姑娘对我一笑,道:“沈二小姐,之前扮作司机和仆人入你梦境只是想接你回与魂铺。我是亓景,刚刚开车的是容辞。看时间那个生魂应该还要过一会才到,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一个魂魄哪有什么感觉,只是好奇小姑娘口中说的回与魂铺,如果是‘回’,那我上次来是什么时候,还有我的记忆里只到哥哥送我去医院,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忆那些鲜血脸上又开始了刺痛,我赶紧收住心绪,明白自己不能往那张脸上想,不然又会变成骇人模样,于是吃了口糕点问小姑娘:
“我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有一百五十年了,你等的那个人在死后六十年进入轮回转世,享年九十,算算差不多是一百五十多年。”
“我是怎么死的?”
“你活了二十七年,到与魂铺时,你用魂魄立契无法转世,剩下的三魂四魄一直呆在与魂契簿中沉睡。”
“我问我是怎么死的?”
话声刚毕,一片红纱飘过,红纱后一双眼睛,等我痴痴拉下那片红纱,惊心动魄,心有如千万绳索拉扯,一来一回的遭受割据惨痛。有人在唤我,声音还带着奶音,一场人生终于收场,松气之际我得幸真切看看那双眼。
“沈二小姐?沈二小姐?”
“我没事,刚刚没问,小姐你是与魂铺的?”
“我是亓景,亓官的亓,高山景行的景,现掌与魂契簿。”
我暗暗舒一口气,明白了刚刚那双眼里不易人察觉的恼怒,是生气我对小姑娘话说太重。
“抱歉,刚刚有点心急。那个人什么时候来?”
回我话的是扮作司机叫容辞的小伙子,他和小姑娘坐在一起吃着烤鸡,嘴上油光泛亮。
“阴差已经去接他,约莫还有半个时辰。”
红衣公子坐在案桌上喝茶,身后没有神佛,脸上不是慈悲相,晃着茶壶都是绝妙风流,目光所及是笑酒笑姑娘。
“沈二小姐,我进你的梦境,有一些事还不太清楚,你姐姐……”
小姑娘给我添了新茶,坐我一旁。
“我姐姐孕时,我阿妈发现了大姐夫在外养情人,把姐姐带回家备孕后,我阿妈和阿爸准备偷偷把姐夫这个情人送走,再给大姐夫施压这事就过去了。名门望族的都怕流言蜚语,能大事化小的都自己私下解决,就一直没和大姐说,等大姐快生产时,大姐情绪突然特别暴躁,而且每天都要喝一种汤。”
“大夫说是因为罂粟,接着阿妈就派了很多人查这个事,其实大致也都有方向,所有侦探最先查的都是大姐夫的情人,很快就把这个情人揪了出来,阿妈当时把她赶出皖北,让人盯了一个月就没再把她当回事,可是大姐夫一直惦记着,看着风波过去了,沈家都不追究了,就开始偷偷去找这个情人。”
“要说权势这东西,沈家追了三代人,我爷爷恨仗势欺人,杀了姑奶奶的丈夫,举家到武汉把姑姑嫁给高官,可惜不论民还是妇,不是人还是不是人。有了点甜头,那情妇当然不甘呆在小村庄里,想回皖北继续做她的富贵梦,于是找了几个仆人混到沈家,开始给我姐姐下药。”
“发现姐姐病症后,阿爸便把姐姐锁在家里。”
我停了话,喝口茶,小姑娘嘴上的油光已经擦掉,看我喝了茶,忙又去端茶瓶给我倒水。容辞咬着鸡腿,含糊问道:
“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有个记者扮作季泽诺的同事来给我送信,说我阿爸用莫须有的罪名把季泽诺送到警察局,我当时心急一时没有戒备让他进了沈家。”
容辞站起身,指指门,道:“来客人了,我先去开门。”
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小姑娘,道:“别扔与魂契簿了。”
小姑娘抱紧怀里的簿子,移到红衣公子身边,对容辞点点头,然后示意他赶紧去开门。
我知道是那个人来了,从红衣公子眼睛里看到的那个人,经过轮回转世过来了,喝下最后一口茶,再添上就是第三泡,味道最好时。回忆起他初见到我时,我已近三十,穿得珠光宝气,张牙舞爪。他以为我是拿着枪视人命如草芥的坏姑娘,所以在我睡着时也提心吊胆的防备我,我如果笑笑他只会觉得我又有坏主意了,就像一个侦探般敬小慎微,而我就是最大嫌疑人。
“亓景?能换个地方让我和他见面吗?”
“那就去院子吧。”
跟在小姑娘身后,走过正堂,又穿过一个走廊来到院子,院子中一棵古树,明月似挂在树梢。
“我好像记起来上次怎么来的了,我跟着鬼差到黄泉口,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这棵树,等到与魂铺时,就听见一阵声音。”
“那时还没有我。”小姑娘沮丧得可爱,皱着小脸看古树。
“一个自称老板的男人把我接进来,问我有什么丢不掉的。”
“这是我们老板,不过我还没见过。”小姑娘嘴瘪得像个小鸭子,夜里突然吹起风,带着草木香,沁人心脾。
“过会,我和他告个别,就去黄泉了,大概魂魄不全不能投生为人,希望就做一棵桃树吧。”看着掌与魂契簿的小姑娘,我总觉得有很多话想讲,可是觉得我这一生也是荒唐,没有什么要说的必要。
“姐姐,你是怎么死的?是季泽诺杀了你吗?”
我有些发笑,想起那个老板的模样,也是有双漂亮到星河失色的眼睛。
“称做老板的男人说他也在等一个人,想必就是你了。我记得我要留在这里时,那个人问我是因为怨恨才不愿意丢掉吗?才不是这样,虽然我死的时候被枪打烂了脸,可是来到这里留在这里,只是因为死的太仓促,我有心愿未了,自己无声无息离开这一世十分遗憾,听说这里可以用魂换愿,那我就在这里等等吧,我没来得及和他告别,花了一辈子心思去讨好的人,我和他怎么能草草结尾。至于你问是谁杀了我,是姐姐啊。”
亓景手中的与魂契簿被风吹开了书页,呼啦呼啦的声响,有一页似受牵引停在空中,仔细看了,居然有东西从纸中渐渐浮出,黑色金属手柄,等书页翻动的声音停止时,东西也全部现在空气中,一把手枪,手柄处还有红色指甲油。
“姐姐,去杀了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