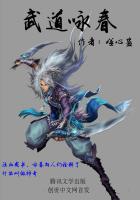柴老夫人在门外参拜太子龙驾已毕,抱着柴君让放声痛哭。柴君让也是趴在母亲怀里,泣不成声。
老家人柴安擦擦眼泪,在旁边劝慰道:“老夫人,母子相见是好事,又哭什么来?太子殿下还在呢,莫要慢待了太子。”
柴老夫人这才慢慢止住悲声,连声称是。来到太子面前深施一礼,道:“殿下,臣妇一时不慎,慢待殿下了,望殿下恕罪。”
太子道:“皇叔母母子相见,正是大喜之事,喜极而泣,自是人之常情,小王又岂会怪罪?”
柴老夫人躬身闪开,道:“殿下,门外不是说话所在,殿下里边请。”
太子说一声:“皇叔母请。”
一行人来到厅堂。太子仔细观看,见这柴府摆设十分简陋,就连使用之人也没几个。柴老夫人先茶后酒,命人招待,有条不紊,一看就知是见过大世面的。不由得在心里暗暗赞叹柴门清正。
不多时,柴老夫人来到太子面前,禀道:“殿下,饭菜准备已毕,请千岁入席。”
太子答应一声,跟着柴老夫人,走到饭桌上首坐定,柴老夫人相陪,柴君让坐在下首,智文长与杨铜也入了席坐定。
太子往桌上一看,见是一碗肉,一碗鱼,一只鸡,一盘豆腐,一碟韭菜,一壶老酒,每人面前一碗粥。碗碟俱是陶器,桌子是粗木打成的,简陋至极。不由得暗暗垂泪。
柴老夫人道:“殿下,皆因官夫生前为官清正,一个月的俸禄是三十二两纹银,也攒不下多少家业。自打官夫去世,幸而留下几亩田产,臣妇靠着那几亩地也能勉强维持温饱。饭菜不可口,望殿下恕罪。”
太子道:“柴家是忠臣,小王知道。皇叔母,明日小王想把你一同带往东京,住在南清宫,狄娘娘也多一位能交心的姊妹,柴皇兄也可忠孝两全。不知皇叔母意下如何?”
柴老夫人慌忙跪倒,柴君让也跪下,柴老夫人呼道:“臣妇领旨谢恩。”
太子道:“皇叔母不必多礼,请起来吃饭吧。这些饭菜可口至极,可口至极,小王爱吃。”说着,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又夹了一块豆腐,放在口中。
柴老夫人这才放心,柴君让把母亲扶起,柴老夫人重新入座,招呼着众人吃菜。
众人吃完了饭,柴老夫人早为太子等人安排了厢房。太子与智、杨二人自去歇息了。
柴老夫人拉着柴君让的手,走到后楼,母子二人秉烛谈心。
柴君让把自己如何下山寻父的,如何独闯灵岩寺的,父亲如何丧命的,又是如何保太子出使辽国的,如何比武招亲的,细细地说了一遍。
柴老夫人又悲又喜,听到柴君让独闯灵岩寺时哭道:“我今日才知你父亲原来是这么死的,官府来家里报丧,说是暴病身亡。”哭了一阵。
听到柴君让说比武招亲,与萧可儿定下了亲事,老夫人转悲为喜,连连说是老天保佑。
柴君让问道:“娘,儿适才在门外听安叔说咱家来了个赵公子,不知是哪个赵公子?”
柴老夫人道:“这位赵公子衣着富贵,一看就知是个大户人家出身。,生得十分俊美,唇红齿白,粉面如雪。自称是你的师弟,却不说名,只说是与你自幼一起长起来的。”
柴君让听了,百思不得其解。
柴老夫人又道:“不过娘看得出来,这位赵公子是女扮男装。你好好想想,是你的哪位师妹也说不定。”
柴君让暗暗考虑:“要说同门师兄妹,只有二师姑辣手春兰蓝玉香有一徒弟,名唤邬素娟,与自己最好。”又转念一想:“不对,不对。邬师妹又怎知道我保太子使辽之事?又怎会女扮男装,假说姓赵?不,绝不是她。”
便问道:“娘,这位赵公子是何时走的?”
柴老夫人道:“昨日刚走,你不说我倒忘了。这位赵公子临走时说你今日就回来,他有要事在身,就不见你了,说是在东京汴梁等你。临走时托我给你带句话,说莫忘了当日南海之情。”
这一句话听在柴君让耳里,不亚于平地炸个响雷,脑海之中如波浪翻腾,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想起当年与赵元英一同玩耍,一同练功;想起她一声一声叫自己“君让哥哥”,想起她采了花,一点一点编成花环,亲手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又想起在济南大街上,二人再次相遇,形同陌路。又想起父亲被葛永义害死,又想起在灵岩寺她命令童董二杰和八大铜人围攻自己……
柴老夫人见儿子的眉头一会儿舒展,一会紧皱,忙叫道:“让儿,让儿。”
“哎,娘”柴君让这才回过神来。
“你是不是知道她是谁了?这个人原来与你交情匪浅,后来渐成路人,甚至是仇人,是吗?”柴老夫人关切地问道。
柴君让看着母亲的眼睛,点了点头。
柴老夫人叹了口气,道:“让儿,别想了,睡吧。”
柴君让答应一声,服侍母亲睡下。自己往床上一躺,心里不住地想:赵元英为何来到柴府?为何帮自己服侍母亲一个月?
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起来,柴君让帮着母亲收拾好衣物,又在外面为母亲套了一辆马车。柴老夫人嘱咐好柴安在家打理田产,一应吃穿,不可难为了自己。众人吃罢早饭,这就上路。
沧州百姓扶老携幼,俱来相送。但见前面马上坐着小霸王杨铜,手拿一对八卦紫金轮,耀武扬威,率一队禁军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的是太子的车辇,岳百恒与智文长一左一右护住太子龙驾。再后面是柴老夫人的马车,柴君让陪在老夫人身旁,母子二人说话。最后面是成对的禁军,旌旗招展,威风凛凛。
大队人马出了沧州,前面是平坦的官道。正往前走,柴君让忽听前方一阵大乱,叫道:“母亲,不好了。必是有人前来行刺,太子有难了。”
柴老夫人道:“我儿不必挂念为娘,速去保太子周全。贼人要杀的是太子!”
柴君让答应一声:“谨遵母命!”跳下马车,施展轻功,来到前面,见是一位蒙面之人正与杨铜打斗,太子由岳百恒护着,毫发无损。柴君让这才放心。
那蒙面之人手使十三节链子鞭,施展开来如梨花骤雨,与杨铜杀在一堆,战在一处,打得难分难解。
柴君让站在智文长旁边,看着前面二人打斗,不由得双眉紧皱,对智文长道:“智师兄,你看那蒙面之人的身法怎如此熟悉?倒像是本门的,莫不是言必行言贤弟到了?”
智文长捋着八字胡须,眯着小眼,也是紧张地看着他二人争斗,听了柴君让之言,道:“哎呀师弟,身法倒像是本门身法,只是与言必行还有些不同。言必行师从言月红,根儿在陶四叔那里。言必行的身法是由他母亲改后的,故此,他的身法里既有本门身法的迅捷,又有月红婶子的灵巧。依愚兄看来,此人就是本门中人,只是怕你我看破,有意遮掩。”
柴君让恍然大悟,连称正是。
杨铜与那蒙面之人大战五十余合,仍是不分胜败。皆因那蒙面之人的链子鞭软长灵巧,长于远战。杨铜的八卦紫金轮厚重有余,灵巧不足,长于近战。故此,杨铜总是近不得那蒙面之人的身。杨铜暗暗着急,可偏偏为兵刃所限,处处受制,只是一味地招架躲闪,难以进招。杨铜也着实是粗中有细,施展开苍山派“移步换景”的轻功,围着那蒙面之人打转,一心要寻他的破绽。
不料那蒙面之人似乎早就知道杨铜每一步停在何处,总是先发制人,长鞭一甩,总是逼得杨铜步法散乱。
杨铜又惊又怒,左手一甩,就要扔出八卦紫金轮砸死那人。
“师弟不可!”柴君让与杨铜相识多年,又岂不知他这一招的厉害?这一轮若是砸实了,便是十个蒙面之人也得立毙轮下。深恐真是自家人,怕伤了那蒙面之人的性命。故此大喊一声,止住了杨铜。
杨铜心里明白,柴师兄不让自己砸死他必有隐情,柴师兄是想抓活的。小霸王打定主意,与那蒙面之人真杀实砍,一心要缠他的兵刃,活捉此人。
那蒙面之人一招“一枝独秀”,朝杨铜前胸点来。杨铜大喜,左手轮护在胸前,右手轮自外向里划过,齿轮正把那根十三节链子软鞭缠住。
杨铜双膀用力,喝道:“给俺过来!”使劲后拽。
那蒙面之人的膂力明显比不上杨铜,眼看得链子鞭把就要脱手,那蒙面之人猛然一张嘴,吐出一物。这样东西透过蒙面黑布,径袭杨铜。
杨铜正在全力夺那蒙面之人的链子鞭,一见暗器到面门了,急忙躲闪,哪里来得及?只听得杨铜“哎呦”一声,一撒手,扔了那对八卦紫金轮,栽倒在地,人事不省。
智文长、柴君让惊呼一声:“师弟!”分别抢出。
欲知杨铜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