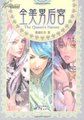苏木坐在窗前酝酿睡眠的时候,是夏天风雨交加的时候。
苏木把一只手伸到窗外,那些过于庞大的雨滴就干净利落地打在上面。一种钝重的金属质感,瞬间就沿着他那繁复而狭小的静脉逆流而上。
那些奇妙得足以让人哑口无言的感觉,逐渐在苏木的身体深处,开始像一列列军队一样聚集起来。
苏木渐渐感到坐立不安,他觉得在自己的体内已经累积了足够大的能量,甚至大得足以让身边的那些细碎的物体,从此得到无以复加的毁灭。苏木这时候感到一丝恐慌,他努力地压抑自己使自己能够安静下来。他似乎想远离一切夹杂着不安静的介质,去接近一种自以为是却可以安静美好的程度。
安静有多久,程度有多深。苏木觉得这句就可以高度概括他所有自定义的内心想法。
一瞬间的模糊,甚至可以造就一世纪的念念不忘。这也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程度吗。苏木认真地摊开那只湿漉漉的手,他看见掌心里的脉络,一段一段地断裂,旋转,直到无奈地模糊成一片,像战争后家园里驻扎的废墟。
苏木没有像往常那样睡过去。这一次风雨交加的时候,他像一头疲惫不堪的兽类,用来回走动去拒绝自我沦陷的危险。
当窗外不远处的一个人举着一把伞,从络绎不绝的雨水里,以及从苏木那执迷不悟的视野里,身影迷离地翩跹而过时,苏木在无意间有意地刻画下了她的马尾辫。至少在那一瞬间,他是如此地像迷恋一场轮回的烟花表演一样,可以轮回地迷恋上一个人的马尾辫。于是他在纸上轻描淡写地叙述起来,他故意把夏天的雨水写成冬天的阳光,英英和小冉的马尾渐次在他眼前流离失所。
谁动了我的马尾辫。
喜欢马尾辫。
喜欢看到扎着马尾辫的女孩,从身边接近翩跹地飘然而过。也或者远远地迎面走来。
反正只是喜欢。
可是现在的马尾辫突然少了。她们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将头发一缕一缕地扭曲掉,也或者一片一片地直直地倾泻下来,然后赋予各种颜色。
花里胡哨。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最终视觉疲劳。
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身上应该具有一种冬天明媚的气息吧。不经意从谁身边走过,谁又不经意闻到了那种遥远的阳光碎裂开来的一地芬芳。
仿佛许多花瓣在同一瞬间的殒落。
那不是谁的水晶鞋,也不会是谁和谁不期而遇的童话。
只是匆匆地瞥上一眼,感觉暖暖的,像把脸小心翼翼地贴在情人的胸口。呼吸和心跳一起纠缠。
以及那些措手不及的爱情,它们会不会和天空和大海和麦田一样,占据了四季落花的歌舞升平。
写完这些苏木走进了雨中。没有打伞,神情坦然,目光与倾泻而下的雨水有着接近垂直的界面。
那个人和她的马尾辫,在绵绵不绝的雨水里,也在苏木焦灼涣散的视野里,渐渐地渐渐地隐约起来。直到某一时刻的开始,苏木毫无征兆地仰起脸,那些透明晶亮的液体,就一股脑儿覆盖到他的整个面部。
苏木顿时感觉到一种铺天盖地的音符在同一瞬间休止,继而是一起默默无闻地跳跃,杂乱无章,毫无头绪。苏木因此而感到格外心烦意乱。走了一段路,他就奔跑了起来。四溅的水花沿着苏木的脚步一节一节地盛开,但很快就各自湮灭了,短暂得不过一转身的时光。
雨停下来的时候,苏木全身已经湿透。雨后的天空有细碎明亮的阳光,透过云朵的罅隙懒洋洋地飘过来。那些阳光意料之中地打在苏木的侧脸,苏木似乎看见了众多的水分子从他的脸庞不亦乐乎地逃离。
对了,逃离,还有不亦乐乎。苏木把头低下来,身上附着的水分蒸发所带走的热量让他微微地感到寒冷。可是抬起头,阳光开始像湖边的野草一样渐渐茁壮,渐渐肆无忌惮。
苏木,在干什么呢。女孩的声音跟随着远远打下来的阳光,一起在苏木的耳际翩跹起来。
回头看,果然是她。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另一半呢。
他呀,他在球场。语气柔和中带着微微嗔怪。
小冉,有爱情天天陪在身边,一定感觉很幸福吧。
幸福。小冉把它轻轻地念了一遍。有时候幸福就在我身边,我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抓,等回过头来,一些东西就看不见了,或者不再是以前熟悉的样子。
这样至少也是一种安于现状的美好。抵达不了的地方,一样可以使我们幸福。
苏木,我知道你想要去表达什么。我们一度这样努力,上天会根据情况,向我们每一个人播散我们想要的一些。
但愿如此,但愿这般不为难。
你呢,苏木,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去找个女朋友。小冉的目光停留在苏木的睫毛上,随着它一跳一跳地忐忑起伏。
其实我也想找一个,可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也许内心深处,始终是习惯自己一个人的。我担心自己带给她的仅仅是不快乐。不快乐,小冉,你知道吗,许多时候身边的人都说我是个不快乐的人。因此,我带给他们的,自然是不快乐。可是我很幸运,他们都并不嫌弃地接纳了我,以及我的那些不快乐。
小冉把目光平移到远方的某处坐标系。苏木随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他眯起眼睛企图调节出一个更为舒适的聚焦点,可是视野里呈现的依然是一片荒芜的底色,苍白,浑浊,甚至不容人靠近半步。
这样拉开距离的拒绝。
苏木和小冉两个人都很安静地走了一段路,只听见各自的脚步踩到积水处发出的微微激越的声响,像大自然深处传来的童声合奏。还是苏木忍不住开口了。
小冉,曾经有一个网上很好的朋友试探着问我,他说他逐渐喜欢上我的文字表达,便质疑我口头表达是否具有同样的本领。其实他的疑问很有道理,当一个人的语言感官去无限靠近文字,而逐渐疏远语言最初衷的本身时,他的任何一种表达便呈现出走向极端的趋势。所以现在我担忧,是否会有我完全失语的那一天。
没有关系的,苏木,有时候不说话或者少说话,都是一种生命初始的本能。那样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余地。至于做朋友,本身便和语言没有太多的关系,互相迁就对方便是。
可是我从来就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说话,不愿意和陌生人交流,口头表达也没有书面表达好。这些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语言,自始至终都更像一个孤独者的梦呓。
苏木,我想起我的一位室友,她的发音很奇怪,总是把F和H反过来去读。比如,吃饭她会说成吃换,回忆的画面她唱成了非议的发面。很多时候自己感觉糟糕的地方,正是别人认为可爱的地方。
小冉抿了抿嘴,一边的嘴角轻微上扬,几乎扬成一个让人难以遗忘的弧度。苏木听见阳光在她嘴角碎裂开来的声响,怎样空灵,怎样寂寞,怎样黯然神伤。也许就在那一瞬间,苏木的眼里装满了太多认真后的无可奈何。
在有些时候,我们注定要一败涂地的,无论我们怎样小心翼翼地努力过,战战兢兢地祈求过。
小冉,对不起,我来晚了。一个有点沉甸却富于磁性的声音,逆着阳光倾泻的方向贯穿而来,苏木裸露的皮肤感觉到了空气微弱的震颤。
回过头去看,没错,应该就是他了,苏木想。
秦南,这是我的朋友苏木。小冉走过去挽起秦南的胳膊,语速飞快却眼神淡定地说道。
你好。秦南把手伸到苏木面前。
你也好。苏木伸出右手迎接了面前的那只手,他在那只手上感受到了一种橡胶的质感,应该是长期接触篮球的缘故。
三个人一起走了一段路,话题从三分篮的姿势扯到南极企鹅的保暖功力。每间隔一段时间,小冉都要从秦南的右手边转悠到他的左手边,然后再从他的左手边到右手边,小冉说这样可以避免手腕关节僵硬得像一块砖头。秦南便在一旁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嗯,我们家的小冉确实比以前懂事多了。
那当然,你以为我只长得好看啊。小冉把头轻微地扬起,一阵风很轻地吹过来,苏木便看到她的马尾辫一晃一晃地逐渐明亮起来,有一瞬间苏木感觉到一阵千丝万缕的晕眩。只是晕眩。
走到一家饭馆的旁边,秦南建议一起进去吃饭。苏木借口自己肚子不饿推脱掉了,然后一个人在路上晃荡起来,近乎无忧无虑的样子,可是看上去像极了失恋不久的无业游民。失恋和失业一起,这个世界如此冷漠地在拒绝着一些人和一些事。
苏木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双脚和双臂机械地相互交错着弯曲,抬起坠下,像巨大的钟摆一样不知疲倦地定格时间的尺度。苏木最后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久,走了多远,反正肯定是很久和很远,因为当他决定要停下来驻足的时候,他看见许许多多陌生的景物和面孔,在自己的视线里很奇怪地集结成一团一团的形状。苏木随即看到那些形状奇特的团状物,闷声不响地逐渐脱离了地面,在气流的作用下,升腾至一个高得足以让人感到绝望的高度。
苏木仰起脸,便亲眼看到它们渐次下坠。苏木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毁灭的力量正在大地上蔓延开来。
那个时候,苏木突然觉得很饿,需要很多食物去满足他的消化系统。于是他走进了不远处的一家清真饭馆,在一个角落的位子上坐了下来。苏木拿着菜谱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每一个菜式都掩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服务员走了过来,轻声细语地说,先生,想好了要点哪些菜吗。
苏木把菜谱递给服务员,几乎是闭上眼睛说,我要一盘牛肉炒饭。
从那家清真饭馆出来的时候,苏木感觉体内有许多水分在同一时间涌了出来,在体表的毛孔处凝结,苏木体会到了那种大汗淋漓的畅快。苏木想,有些人的满足,仅仅止于饥饿时的一碗饭而已。
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怀揣那么多居心叵测的欲望和处心积虑的野心,去流连一场注定要走向湮灭的幻觉。
也许,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幻觉。
晚上的时候,苏木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进入睡眠,他觉得是自己心里在放不下一些事情。苏木想,我是有一些话要对小冉说的,只是以前走得太匆忙,所以来不及去告诉她。这次要认认真真地说给她听,认认真真地在一个人面前天真一回。
苏木打开手机,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按出来。小冉,我想要你做我的红颜知己,我便是你的蓝颜知己。然后,你谈你的恋爱,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帅哥不犯美女。那样当我们老去的时候,老到可以蓦然回首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我的回忆会因一个女孩而渐次绚丽多姿起来。
这些又未尝不是一种美好呢。还有,秦南是个不错的人,记得要互相好好珍惜才对。
按下发送键,然后关机,闭上眼睛开始等待新的一天。明天应该还是今天这样的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吧,苏木想。在睡得晕乎乎的时候,苏木记起有一个人在他梦里绵绵不绝地唱了起来,声音很轻,可是苏木却异常清晰地听到了。
如果有来生,我愿作一缕清风。朗朗清风,无形无物,无休无止,可以随时吹到你身边,吹到天荒地老,天涯海角。吹到我一个人看见自己白发苍苍。
苏木醒来得的时候,就怎么也记不起这是谁唱的歌谣了。也许这不是谁唱的,是苏木白天的时候在书本上无意间看到的,然后无意间就把它铭记在心底,等梦里的人都走光了以后,自己对着自己唱了起来。
像夕阳下对镜梳妆的缥缈。
苏木在那一晚上不知失眠了多长时间。反正他只知道,当他开始闭上眼睛的时候,他隐约地听见了窗外国防生喊操训练时发出的整齐划一的口号。那时候苏木想,我是个不轻易喜欢上一个人的家伙,可是一旦喜欢上就不轻易忘掉那个人,这样便注定了我是个容易受伤的动物。
我的感情线太过清晰单一,这一辈子只能去爱一个人,直到爱到那个人为止。所以在没有爱到那个人之前,所有的爱情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爱情。也许那些只是喜欢,总是与爱情有一墙之隔的。不能逾越,更是不可破墙而入。
爱情是一辈子的事,而喜欢,则是一阵子的事。时间的尺度不同,程度便不一样。
苏木记得在前不久,和班上的一位同学探讨星座的问题。听苏木随便讲了一段射手座和处女座的故事,他便感到疑惑,问,苏木,你对星座很有研究吗。
不研究。我一度这样心高气傲,是不会去相信这类看似很骇人听闻的东西。现在依然心高气傲,却宁愿相信了那些以前不轻易去相信的东西。没有办法,生活有时候就是这般不讲道理。多数时候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有去顺应它,以及改变自己。
改变。也许那么多的不顺利,只是因为我们欠缺改变。
可是有些人,你在他或者她身上用过心思花费过时间,离开的时候会更难过。苏木心里明白,有些事只能作回忆,有些人只配作过客。
这便是相交于心灵,相忘于江湖。
苏木记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当一个人认识到江湖并非如愿美好,从而像退出江湖归隐山林,另一个人便对这个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本身便是江湖的一份子,如何让去退。
一入江湖岁月催,都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事。
爱不到,却又放不掉,因此总是念念不忘。
这样的爱,免不了与欲望起着千丝万缕或者蛛丝马迹的关联。可是在苏木的眼里,有些爱并非是欲望可以随便注解的。他在某一时刻起,只想自己去做个无欲无求的人,努力让自己没有野心和欲望。
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平淡安宁地行走四季,又未尝不是一种众生向往的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