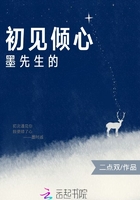我们是愈摇撼愈牢固的树木。
——乔治·赫伯特[64]
桑顿先生没去餐厅告辞就离开了。他有些晚了,所以加快速度向市郊的克兰普顿走去,他担心迟到会显得失礼,让自己的新朋友觉得受到了怠慢。他站在门口,等着狄克逊不紧不慢地来开房门时,教堂里正好响起了七点半的钟声。当狄克逊觉得必须要降低身份去给客人开门时,总是无比缓慢。他被领着走进小客厅,受到了黑尔先生的亲切欢迎。黑尔先生带他上楼,见了太太一面,她苍白的脸色和包着披肩的身子,无言地解释了她为什么没有打起精神迎接他。他走进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发黑,所以玛格丽特正在点灯。在昏暗的房间中央,灯光投射出一道明亮的影像。他们依然保留着乡下的习惯,没有把夜空和窗外的黑暗给挡在外面[65]。不知为什么,这个房间和他刚从那里来的房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之前的那个房间虽然布置得很漂亮,但是很沉闷,除了母亲坐着的地方,没有任何女性留下的痕迹,除了用餐,也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那是一个餐厅,但是母亲乐意待在那里,在这个家里她的想法就是法律。但是这个客厅却不同。它比那里精致两倍,不,是二十倍,但是在舒适程度上还不如那里的四分之一。房间里没有镜子,甚至连一块能反射光线的玻璃也没有,就像溪水映照周围的景色那样。这里没有金碧辉煌的陈设,色调是素雅而柔和的,在有些陈旧的赫尔斯通印花棉布窗帘和椅套的点缀下,显得十分宜人。一张带着罩子的小书桌放在正对门口的窗前,桌面敞开着。另一个窗边立着一个小架子,上面摆着一只高大的白瓷花瓶,瓶口垂着茂盛的常春藤和桦树枝。房间的很多地方都有漂亮的装着针线的篮子。桌子上有一些书,看起来是最近放在上面的,并没有因为装帧精美而被束之高阁。门后摆着另一张桌子,安排好了茶和点心。桌上的桌布是白色的,上面放着椰子饼,还有一篮摆在绿叶上的橘子和通红的苹果。
桑顿先生认为,这些精心而典雅的布置对于这家人来说习以为常,并且和玛格丽特十分和谐。她身着浅色的细布衣裳,上面有淡红的花纹。她似乎没有在听他们的谈话,而是在桌子旁边专心地摆着茶杯,用那双象牙般圆润的手轻巧地布置着茶具。她的胳膊上戴着一只手镯,因为胳膊很细,所以手镯总是掉到手腕上。桑顿先生对她重复地把手镯又推回去的动作十分关注,相比之下都没怎么听她父亲说的话。他看着她有些急躁地把手镯推到手臂上,紧箍住娇嫩的肌肉,然后再看着它慢慢松开又落下,这让他几乎都着了迷。他差一点就叫出声来:“要掉下来了!”他到达的时候,玛格丽特几乎已经安排好了茶点的准备工作,所以他为自己要马上开始喝茶吃点心,没法多看玛格丽特一会儿而感到惋惜。她流露出了一种不得不去为人服务的高傲的神色,将茶杯递给他,但是当他需要续杯的时候,她马上就能注意到。他看到她的父亲用手捏着她的大拇指和小指,把它们当成夹子夹起糖块,他心里也强烈地希望她能够也为自己做同样的事。在这对父女间进行这种无声的哑剧的时候,桑顿先生看到她抬头看着父亲,美丽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其中一半是笑意,一半是疼爱,而他们觉得没人注意到他们的这些小动作。玛格丽特的头依然很疼,这可以由她苍白的脸色和保持的沉默得到证明。但是如果对话中发生了长时间的停顿,她就会开口来打破沉默,从而不让父亲的朋友和家里的访客觉得自己被怠慢了。谈话一直在继续。撤下了茶具之后,玛格丽特拿起针线活儿,来到母亲旁边的一个角落。她觉得自己能独自想事情,而不用担心去找话题来弥补对话中的间隙。
桑顿先生和黑尔先生正在全情投入地聊着上次见面时谈到过的一个话题。当母亲压低声音说了一句题外话时,玛格丽特才重又注意到了眼前发生的事。她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看到了父亲与桑顿先生之间在形象上的不同之处,别去认为这些区别能够代表两者性格的截然相反。父亲是个瘦高个儿,所以当没有人和他作对比时——比如现在,和另一个高大又强壮的人对比——他会显得比实际身高要高一些。父亲的脸上有着温和的皱纹,看起来带着一种波浪一样的起伏,能够表现出一些捉摸不定的情感。他的眼睛很大,又有点弯,看起来有些无神,呈现出一种温柔而特殊的美感。他的眉毛也是弯的,但是隔着大大的眼睑,看起来距离眼睛有些远了。再看桑顿先生,在他的脸上有两道笔直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深陷的、清澈而流露出真挚情感的眼睛。这双眼睛的眼神十分锐利,但并不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过似乎能够看穿所有他正在凝视的东西的本质。他的脸上没有多少皱纹,看起来十分坚毅,像是大理石雕塑出来的纹路分散在嘴角的两侧。从他微启的嘴唇能够看到他有着一口洁白的牙齿。当他难得地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的时候,当他的眼睛发出欢乐的神采的时候,他的脸上会让人觉得突然闪出了阳光,同时让他的整个形象从一个随时准备做任何事、也敢于做任何事的严肃而果断的神态,转变为对那一刻的乐事感到由衷地欣赏的神情。除了孩子之外,很少有人会这样直率地流露出这种表情。玛格丽特很喜欢他这样的微笑。这是她在父亲的这个新朋友身上找到的第一件让她欣赏的方面。而且她意识到,他们的外貌所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截然相反的特性,好像正是他们能够彼此吸引的原因。
她把母亲的针线活儿收拾好了,接着又自己开始了沉思。桑顿先生也把她完全给忽略了,就好像她并不在这个房间里。这时他正集中精神给黑尔先生解释汽锤具有的强大力量,以及如何巧妙地调节力的大小。这让黑尔先生想起《一千零一夜》里描写的那些妖怪的故事[66],一会儿能够化身为充斥天地的巨人,一会儿又能缩小到装在一个小孩子都能拿住的小瓶子里面去。
“能够想象出如何利用这种力量,并且实现这个宏伟的构想,这都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有头脑的人做到的。他的头脑真是厉害,让他能够在创造出一个奇迹的基础上再创造另一个奇迹。我必须得说,如果他死了,在我们之中还会出现很多人,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要迫使——这简直是必须的——所有物质的力量臣服于科学的脚下。”
“你的这番慷慨言辞让我想起了两句古老的诗——‘在英格兰有我的几百名队长,’”他说,“‘全部像他一般出色。’”
玛格丽特听到父亲说出这两句诗的时候,忍不住抬起头来,眼里流露出惊讶和好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从齿轮谈到《切维山狩猎》[67]上去的。
“我没有夸夸其谈,”桑顿先生回答,“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承认我为自己属于这里而非常自豪,因为这个地方虽然贫穷,但是产生了如此伟大的设想。我宁肯在这里辛勤度日,即便是一无所成,也好过在南方的那些你们认为充满贵族气息的地方,受制于陈腐的规矩而沉闷地生活,享受着懒散和无所事事。你们或许会被蜂蜜给粘住[68],再也飞不起来。”
“你说的不对。”玛格丽特说道,她显得有些激动,因为被人这样侮辱她所钟爱的南方,于是要挺身而出为南方辩护。她的脸因为激动而泛起红晕,眼眶中充满了泪水,“你对南方一无所知。这里出现的这些令人惊叹的发明,是商人的投机精神促成的。如果说南方与这里相比缺乏投机和冒险精神,或者说是缺少一些刺激,但是却比这里少了很多痛苦。我在这里的大街上看到很多人都像是因为一些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被折磨垮了,他们不但承受苦难,而且充满仇恨。在我们南方,也有穷人,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在这里看到的那些痛苦不堪的神情。你根本不了解南方,桑顿先生。”她结束她的发言后,决定不再开口,并且为自己说了这么多而觉得十分气恼。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你同样不了解北方呢?”他问,说话的音调异常平和,因为他已经看出来,她的感情真的被自己的话伤害了。她决定继续保持沉默。她是如此地思念那些在遥远的汉普郡的诸多可爱的地方,这种思想让她感到,如果自己现在开口说话,声音都会开始颤抖。
“不管怎么样,桑顿先生,”黑尔太太说,“你必须得承认,和南方的任何一个你能想到的城市相比,米尔顿的烟雾都更浓,也更脏一些。”
“那么我只能不谈环境这方面的事了。”桑顿先生露出了一种狡黠的微笑,“但是议会下令我们把烟雾给处理掉,我们可能必须得听从命令,像乖孩子一样——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但是你不是告诉我,你已经改造了工厂的烟囱,好让烟雾得到处理吗?”黑尔先生问。
“我改装烟囱是在议会做出干涉之前的事。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是能够节约燃煤,让我能够受益。如果这项法令获得了通过,我倒不确定是否还会这么做。不管怎样,无论如何,我都会等到被人告发并且罚款,还要在遵照执行以前把在法律范围内所有能惹出的麻烦统统都惹上一遍再说。但是这些只能通过告发和罚款来维持的法律,会因为这些机器而变得毫无用处。即便在米尔顿有很多烟囱烧掉了这里三分之一的燃煤,然后变成议会禁止的黑烟冒了出来,我也不认为过去的五年里有任何一个烟囱被人举报过。”
“我只知道,干净的棉布窗帘挂在这里用不了一星期就会变脏了。在赫尔斯通的时候,窗帘能够连着用上一个月。即使是过了一个月,也并不显得脏。还有手的问题。玛格丽特,你刚才说今天中午之前你洗过多少次手?是不是有三次?”
“是的,妈妈。”
“你似乎对议会下达的命令,和影响到你们在米尔顿的管理方式的所有法律,都抱着强烈的抵触情绪。”黑尔先生说。
“是的,我非常抵触,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并且我觉得这十分有道理。棉花纺织行业里的所有机器,当然其中不包括那木制的机器,都是新发明出来的,所以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法马上配合好,是很正常的事。七十年前是怎样的情况?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各种原料都聚在了一起。两个受教育程度和身份本来相同的人,因为其中一些人的聪慧和各种机遇,分为了工厂主和工人两种阶层。一些人因为他们天生的机敏和富有远见而崭露头角,他们意识到理查德·阿克赖特[69]爵士发明的简陋机器能够带来多么美好的未来。那个时候,因为新的行业的飞速发展,让早期的工厂主们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势。这种权势不仅体现在能够支配工人,还能够支配买方,也就是全世界的市场。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在不到五十年前,米尔顿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上面说某人(当时仅有的几个棉布印花商之一)会在每天的中午关闭他的货仓,所以想要购买的人得在关门之前到那里去。看啊,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地随意规定售货与停止的时间。而现在,我相信,如果有人愿意半夜来买我的货,我都会从床上爬起来,等着他来订货的。”
玛格丽特撇了撇嘴,但是不知为何,她却没法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而不得不听桑顿先生说下去。
“我举这样的例子只想说明,本世纪初,工厂主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所以他们都被权力迷住了双眼。即使一个人在投机事业上非常成功,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在其他方面也能显示出同样的水平。恰恰相反,在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之后,他的正义感和朴实的作风往往就消失殆尽了。民间流传着一些怪诞的传说,里面说的是这些过去的纺织业巨头的生活是怎样地纵情和骄奢淫逸。这些人对工人们的压榨,也是确有其事的。黑尔先生,你应该听说过那句谚语,‘乞丐如果发财了,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有一些早期的工厂主确实做过很多恶,他们对工人毫不留情。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反作用。工厂和厂主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工人。厂主和工人的力量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现在,我们之间所进行的战斗是非常公正的。我们不乐意服从所谓的仲裁者的判决,更加不会让一个对真相都不是十分了解的人来多管闲事,哪怕这个人被称为议会也不行。”
“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必要被称为战斗吗?”黑尔先生问,我当然明白,既然你用了这个词,就说明在你心里这个词最能代表事情的真相。”
“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说是很正确的。这就好比,处事精明和品行优良,从来都和毫无远见与缺乏知识是相对的,而且一直在和它们战斗。一个工人能够通过努力来获得提升,最后获得工厂主的权力和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中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实际上,只要能约束自己,洁身自好并且恪尽职守,就一定能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虽然不一定是工厂主,也能够成为监工或者会计,成为拥有权力和创造秩序的人。”
“这么说,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话,在你看来,世界上所有平凡的人,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就都是你的敌人啦。”玛格丽特语气冷淡地说道。
“他们是自己的敌人,是的,我就是这样认为。”他飞快地回答道,完全没有因为她的口吻以及说话时流露出的傲慢而生气。但是回答之后,他就非常坦率地意识到,他说的这句话只是对她的问题做出了一个并不明确的回答。而且,无论她怎样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他都有义务把自己的意思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如果要把她说的话和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区分开来,并且显示出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却显得十分困难。他只能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说给他们听,这样能够很好地解释他想表达的意思。但是和陌生人说起这些,是否有些显得过分私人啦?但是,这是能够说明自己的意思的最直接的方法,所以尽管他有些羞怯,脸颊都有些发红了,但是他仍然决定抛开这种羞怯,说道:“我说这些并非凭空捏造。十六年前,我父亲在一个悲惨的境况下离世。我只能辍学,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大人。幸运的是,我的母亲是一个几乎没人能比得上的,坚强而能干的女士。我们搬到了乡下的一个小镇上,因为和米尔顿相比那里的生活更便宜。我在一个布匹店里谋到了份差事,我得说,那里能够学习到很多关于商业的知识。时间一星期接着一星期地过去,我能取得十五先令的收入了。靠这点收入,我需要养活两个人。我母亲为我计划好了,让我从这十五先令中拿出三先令来作为积蓄。这是我以后成功的开端,并且让我懂得了要自我节制。现在,我能够让我的母亲颐养天年,我每天都在心里感谢她在早年对我的培养和训练。所以我觉得,以我过去的经历来说,我没有什么特长,也不是凭着好运气,更没有什么才干,只是因为生活中养成的一些习惯罢了。我非常看不起那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种种享乐,我不会对它们产生哪怕一点儿兴趣。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痛苦,就是黑尔小姐提到的在米尔顿人的脸上看到的痛苦,只是对他们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里获得了不应得的享乐的惩罚。我并不认为那些纵情声色的人值得我厌恶,只是因为他们的卑劣人格而鄙视他们罢了。”
“但是你接受过不错的基础教育。”黑尔先生说,“你对于荷马的作品的兴趣能够让我看出来,你对它并非一点都不熟悉。你过去曾经读过,现在只是再度唤起了对它们的记忆。”
“这倒不假,——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的时候,曾经胡乱读过一些。不瞒您说,我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一个学习古典文学非常出色的学生,不过在那之后,我把拉丁文和希腊文都给忘光了。但是我问问您,这些知识对我必须经历的这些生活有任何用处吗?一点用都没有。完全没有用处。从受教育程度上来说,只要会读会写,那么和我当时的受教育水平都是不相上下的。”
“不,对你的这种说法我并不同意。在这方面,我或多或少有些迂腐。荷马的作品中描写的那些高尚的精神,在你回忆起来时,没有让你的精神感到过振奋吗?”
“一点都没有!”桑顿先生笑着大声说道,“我身边有很多活人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我实在很忙,没法想到一个死人。现在,既然我能够让母亲过上了在她这个年纪应该享受到的生活,适当地回报了她在过去的辛劳,那么我就能回过头来找到以前的那些书,然后好好地阅读一下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职业习惯,我总是认为,我的工作才是全天下最重要的。”黑尔先生回答。
桑顿先生站起来,打算告辞。他先是和黑尔先生和黑尔太太握了握手,接着转向了玛格丽特,打算也和她握一下手。这是米尔顿约定俗成的习惯,但是玛格丽特却不知道。她只是朝桑顿先生鞠躬告别,等她看到了他伸出手,又迅速地缩了回去的时候,她觉得非常抱歉,没有事先察觉到他的用意。但是,桑顿先生对她的抱歉心情一无所知。他直起身子,转身离开了。在从这座房子里出来的时候,他的嘴里喃喃自语道:“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姑娘比她更加傲慢和暴躁的了。她的高傲和无礼,甚至使她美丽的容貌都显得不是那样令人记忆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