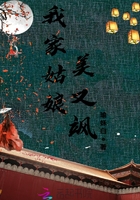撷枝醒来时觉着头痛,日光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外头一阵喧嚣,不绝的脚步声,欢笑声,打闹声,杯盘碗盏的碰撞声让她心头亦跟着焦躁。她迷糊着推门,却见凌翠倚在门口的立柱上,手里悠然打着纨扇,似笑非笑道:“姐姐这是好清闲,这睡了得快一天了吧。昨晚上孟家少爷来找你,都被云乔推了出去呢。”
撷枝一时没反应过来:“孟家少爷?”
“就是那个从刚牢里放出来的孟少爷啊。”
撷枝全不顾她是随口一说还是话里带刺,只想着孟益竟然就这么被放出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连皇帝都下令彻查此事,怎么就轻而易举地给放出来了。可转念一想,这些权贵只手遮天,连草菅人命的事情都能大事化小,何况只是以权谋私,贪婪敛财。她忍不住自嘲,如此煞费苦心,却也不过是往水里不痛不痒地扔了一块碎石头,只微微起了几丝涟漪,便再无波澜。
说话间凤羽已经由喜娘搀扶着走了出来,她手里的丝帕已在手指上绕了好几个圈。云嫣只道她是紧张了,拉上撷枝送凤羽上花轿。
轿子并不算大,可贵的是通身用红木打造,像个缩小的亭子。条条横木交叉相叠,像极了儿时玩的鲁班木。远看还觉得素净,可凑近了却见雕刻的折枝牡丹暗纹浮动在眼前,迎着明亮的日光,颜色只是更深了一分,像是酱紫色,十分古朴典雅。花轿四角扎着硕大的鲜红绣球,底下垂着金灿灿的流苏。迎亲人喊了一声“起轿——”惊得麻雀一片乌压压地飞过。轿子缓缓升起,上下浮动着往前移,埋在红色绸缎里的黄色妆花缎被风吹得翻了出来,一层压住一层,如微风拂过田间,麦浪翻滚,一派喜气祥和。
撷枝却觉得这轿子孤零零的,除了一个迎亲的管家,就只有四个轿夫,莫说仪仗,连唢呐、锣鼓也没有。巷子里静悄悄的,直到那朱红的一点越来越淡,终不可见,云嫣才叹了口气:“孙老板在钱财上这样舍得,可好好的婚礼竟然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真是委屈了凤羽。”
撷枝被说中了心事,亦叹息道:“向来纳妾都是不给走正门,只得从偏门悄悄送进去。也不知孙老板的夫人喝凤羽的妾室茶时,会不会为难凤羽那丫头。”
孟益和周翼之获释之事来得的确出人意料,虽说对这个结果有所准备,却怎么也料不到他们竟然这么快就毫发无损、活蹦乱跳地走出了刑部大牢。崔荻这样好的脾性,都气得暴跳如雷,将书案上的册本卷轴扫了一地。
孙先生道:“贤侄莫急,总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是不是吴王?”陆止萧问。
崔荻道:“吴王何时有了这么大的本事?”
“造些假证,找人顶罪,再加上陛下的偏护,想来竟也不是什么难事。”
孙先生安慰二人:“好在经过此事,太子与周遥彻底结了梁子。周遥多一个敌人,我们就多一个朋友。”
晌午时候,陆止萧带孙先生到医馆看病拿药。他素来走长平街,今日却宁可绕道也要刻意避开。
孙先生似乎看出什么来,问道:“有什么心事连叔父都不肯说吗?”
陆止萧似是而非道:“叔父,如果你做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却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你会怎么办?”
孙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认真思考了片刻才说:“若是能补救,求得他的原谅自然是好,否则……无解。”
陆止萧心中隐隐失落。猛一抬头,脚步忽然迟滞。他疑心自己看错了,那抹浅蓝色这样淡,淡得几乎要融化在淡蓝的天际里,可那分明就是她。
他停在原地,不知应该打声招呼还是应该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犹豫间,她已从他身边经过。他似乎还能闻到她鬓间秋海棠的香气,她离他这样近,却连斜眼也没看他一眼。
“刚刚那位就是柳姑娘吗?”
陆止萧诧异地看着孙先生:“叔父怎么连这都知道?”
“崔宅上下这么多嘴巴,我多少有些耳闻。虽说有一些细节不大清楚,但大体上也能猜到几分。”
陆止萧苦笑道:“崔荻与我是挚友,我不能眼看着他因为一时糊涂断送了前程。”
“止萧,”孙先生意味深长道,“说到底崔荻喜欢谁,想娶谁都是他的私事,你没有立场过问。这样的关心在谁看来都委实过分了些。”他看了陆止萧一眼,又继续道:“何况,你要是真想让那姑娘离开崔荻,以你的聪明才智难道想不出比这样更好的做法?”
陆止萧脸色骤变,急急辩驳。孙先生仍然面带微笑道:“你无需向我解释,若是你没有这样的想法,只当老头子我想错了吧。”
陆止萧彻夜辗转难寐,最终还是决意同柳撷枝谈一谈。他是鼓足了勇气才走到拾芳楼跟前,可远远就看见柳撷枝笑吟吟地送孟益离开。他一霎那觉得血都冲到了头顶,一个箭步冲上去,质问道:“孟益怎么会在这?”
柳撷枝置若罔闻,兀自向前走着。
他又快步挡到她前面:“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可崔荻呢,他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要和他的死对头纠缠不清?”
撷枝冷冷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遥才是崔荻的死对头吧。”
短暂错愕之后,陆止萧呓语一样低声喃喃道:“孟益也不行。”
撷枝漠然看着他,像在看一个普通的陌生人。她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愿说,只等着他,等他给她把路让开。他终究调转头,走开了。
如果他回头就能看到她戚戚地看着他,可他一次也没有回头。
好像回到许多年前,她还不认识这些个人的时候。她刚刚出来弹琵琶,日日都唱得十分卖力。偶尔有客人想轻薄她,可都给拾芳楼里的小厮架了出去。苏妈妈是个左右逢源的人,寻常客人不敢得罪。等大了些,她不再费心在琴棋书画上下功夫,开始学着揣摩别人的心思,学着知分寸懂进退地和客人聊天,学着怎么和周翼之这样不怀好意的纨绔子弟周旋。
如今她只需弹好琵琶,心情好的时候多陪客人聊聊天,逢场作戏,虚情假意,倒也清闲。
孟益偶尔会来找她,她有时也会和孟益逛逛园子,看看风景。孟益虽是个极其没有出息的纨绔子弟,倒也还算是谦和有礼,言语举止间从不敢冒犯。这样的人虽然不可爱,但是也没有什么怀心眼,和其他城府颇深的王公贵胄比起来,和他打交道的倒是容易轻松一些。
“公子最近好像是不高兴的样子?”
孟益道:“别提了,我那个姐夫削减了我大半用度。只怕再过几日,苏妈妈连门都不给我进了。”
撷枝“嗤嗤”一笑,给他递了一块桃酥,道:“哭穷都哭到我这里来了,要不要我接济你一些饭钱。”
孟益连忙摆摆手:“这我多没面子啊。”
“公子也该听殿下和娘娘的话,多花些时间在科考功名上。也不说什么济世安民的话了,好歹太子和娘娘能对你好些,你手上也会宽裕一点。”
撷枝原只是随意说些客套话,却不想孟益一脸感动的看着自己。孟益其实也是十分讨厌别人劝自己这些浑话的,但是这话从柳撷枝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觉得身心惬意。
“这些事儿我也就别想了,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既没有那个心,何必去当那官害人呢。”
撷枝此刻倒觉得孟益算是个拎得清的人,不免调侃道:“公子说得是。”
这日,云嫣正专心致志打着缨络,忽听到外面一阵喧哗。只见孟益抱着撷枝,身边围着一群人,径直走进了怡云阁。地上稀稀疏疏滴了一地的水,蜿蜒如细绳。
“这是怎么了?”
云乔道:“姑娘和孟公子出去划船掉到水里了,现在已经没事了,只是受了极重的风寒。”
“怎么会掉到水里?”
“姑娘的项链掉到了水里,她慌忙去捡,不小心从船上滑了下去。”
云嫣有些疑惑:“什么项链要这么不要命地去捡?”
云乔回答:“就是崔公子送的那条。”
云嫣“啊”了一声,云乔又补充道:“就是那条像骰子一样的项链。”
云嫣似乎想起什么来,连忙道:“快叫李公子来。”
“李公子?”
“对,李公子。”
陆止萧先问了问撷枝的情况,听云乔说她已无大碍,便道:“既然柳姑娘在休息,我就不打扰了。”
云乔并没有在意,又道:“烦劳通传崔公子一声。”
陆止萧道:“崔公子近日公务繁忙,只怕……”
云乔这才恼了,大声道:“姑娘现在高热不退,可手里仍然紧紧攥着那颗玉方石坠子。姑娘为了他送的项链连命都不要了,让他见一面姑娘有这么难吗?”
陆止萧愣了愣,才道:“等晚些崔公子回来了,我一定转告他。”
云乔这才放心,哽咽道:“谢谢李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