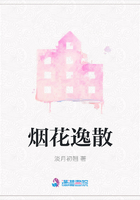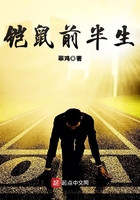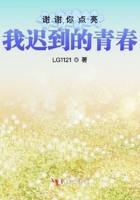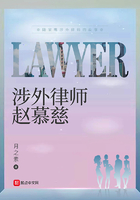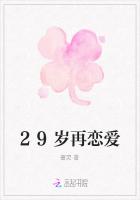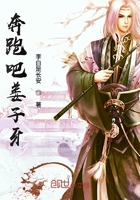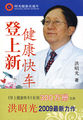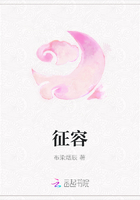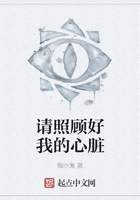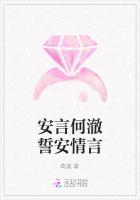安公公让设计的那几件东西被宫里的新任总管李莲英拿走了之后,德风心也就平静了许多。一个是没有误了人家的喜事儿,再一个就是不枉他辛苦一番的设计。要是卖给了别人,总感觉怪怪的,似乎是物非昔人,像是对不起谁似的,这下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多年下来,他自己觉得多了几分惰性,少了几分追求,年年有钱捎回家中,亲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温暖有了保障,这也是他有些懈怠的原因之一。可他也时常告诫自己,提醒自己,越是有这样的想法,越是要努力攀登,艺术是无止境的,做事儿要无愧于心。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提升自己,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
多年的身在他乡,对家人少了许多接触,对老人少尽了孝道,爷爷的去世令他难过许久,一想到他在世时也住上了孙儿挣钱盖起的新房,也有了些许的安慰。
二弟的病痛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这与农村的缺医少药,条件简陋有着切实的关系,这使父母增加了许多精神负担,对此他也颇为芥蒂。
作为一个七尺男儿,常年在外,自然对妻子就更少了不少呵护与恩爱,对子女的教育和关怀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让他安心的是,妻子的通情达理,孝顺父母长辈,教育子女,操持家务,费尽心血。
小立庆天资聪慧,悟性极高,他遗传了父母二人的长处,艺术细胞明显显露,尤其对绘画热情极高,且画什么就像什么,惟妙惟肖。在母亲的指导下,能充分发挥他自己的想象力,德风每年回家时,都能看到立庆的许多画稿,也令他惊讶不已。越是这样,爷爷奶奶就越是宠爱。因为这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希望。儿子靠手中的画笔挣得了这份家业,如今的孙儿也有了他父亲般的能耐,他们怎么能不宠爱呢?且又是长子,长孙。
有一次,爷爷问他,“立庆啊,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像俺爹那样,去京城。”
“去京城又干什么呢?”
“到皇宫里去见皇上,去见太后啊。”
“去见皇上、太后干啥呢?”
“给他们设计好看的灯笼,漂亮的宝瓶!”
“为什么呢?”
“去挣钱啊,我要去挣好多好多钱。”两只小胳膊比划着。
“挣来钱又干什么呢?”
“给爷爷奶奶买点心,给俺奶买红纸儿。”
“好孙子,爷爷奶奶没有白疼你,可给你奶买红纸儿干什么呢?”
“让俺奶剪好多好多的花纸儿,贴满整个房子,让咱家的房子好漂亮好漂亮。”
“真是个好孩子,”奶奶说着把他搂在怀里,深情地在他的稚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那以后可要好好听话,认真做事儿!将来像你爹那样为皇帝做事儿,为家人争光,光耀祖宗。”
“嗯!”似乎是听懂了大人们的话似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立庆渐渐长大,眼下已是十六岁的人了,也算成人了,到了这个年龄,可他游性太重,家人为了能让他沉静下来,便张罗着为他提亲,好让他收收心,成熟起来,能对家庭有个担当。由于家庭条件好,门槛都被踏平了,媒婆一个个的造访,传递着个个女家的信息,家庭的口碑,女孩儿的人品,相貌,脾性等一一仔细打听落实,像过筛子一样为贾家的长子,长孙尽心挑选着未来媳妇。
经过媒妁之言,父母亲定,总算相中了德平陈家寨一个刘姓人家的一位女子,年龄还比立庆大两岁,不过这也是家乡的习惯吧,说什么女大两金银淌。挑选了良辰吉日,凑齐了三头六面,给二个孩子既定了终身,张罗了婚庆大礼。
接到儿子要结婚成家的消息,德风当然不能不回去,这是孩子的终身大事儿,又是他唯一的儿子。再说,天已经凉下来了,又快要过年了,索性等过好了年再返京,这样时间也宽裕,也好与家人多在一起多聚聚,多交流交流。儿子成亲,这家里又多了一口人了,加人添口是喜事儿。也说明人丁兴旺嘛,再过个和和美美的快乐年,岂不乐哉。想到这里,德风来向老掌柜告假,得到允许后,德风做了些必要的准备,便启程回老家来了。
德风回来后,首先关注的是二弟,看着他在门口跑来跑去,如同个孩子,对德风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似乎忘记了许多东西,“德春,过来,到哥哥这儿来!”
“嗯?你叫我吗?”德春一惊。
“对,是我叫你,”德风鼻子一酸,眼泪便含在了眼眶里。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我是你大哥,德风呀,”德风更难过了。
“是吗,我大哥在京城里做事儿,你怎么在这里?”
“大哥回来了,回来看你来了,”德风进一步解释。
“看我干什么,你走吧,别看了,我还要玩儿去呢。”
德风此时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看到德风流了眼泪,德春伸手为他擦泪,“你哭了,你都是大人了,还哭啊,别哭了,我带你去玩儿。”
德风猛地抱住了德春,哭得更伤心了。
“你把我抱疼了,”德春挣扎着。
“是哥不好,德春,跟哥说,你认得我吗?”
德春瞪着眼看着他说,“不认识,你从哪里来?”
“跟我回家吧,哥给你吃糖果。”拉着他的手。
“是甜的吗?”
“嗯,可甜了。”
德风摸了摸口袋,拿出几块儿糖放在德春的手里,“你看。”
“我可以吃了吗?”
“当然,很甜。”
德春坐下来剥开了一块儿放在嘴里说,“嗯,甜,你从哪里买来的?”
“京城,”德风说。
“是我大哥做事儿的那个京城吗?”
德风心里翻腾着,“是。”
“那你见过我大哥吗?”抬头看着他。
“我就是你大哥,德春,我就是德风。”
“又骗人了,我不跟你玩儿了,”抬腿就跑了出去。
看着德春的样子,德风心里难受极了,这么大一个人,一场病生的,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本来到了成家的年龄,可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日子,可现在就如同一个不懂事儿的孩子。还有点儿呆傻,不禁要为他的将来而揪心,心情也更加沉重了。又看到他无忧无虑的另一面,也感到一份欣慰。他活得起码没有心灵的烦恼和负担,只要供他吃喝,穿着干净还是能够做到的。
小弟一家也过得自在,已有了两个儿子,老大立功,活泼可爱,体壮腰圆,将来一定是个种田的好手。老二立墀,有点儿顽皮,瘦小,和哥哥完全相反。见到两个可爱的孩子,德风把他们叫过来,搂在怀里,真是喜爱至极,“功儿,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跟俺爹那样,赶车上地,喂骡子养马。”
“呵,你爹可多了一个好帮手。”
“墀儿,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又问老二。
“俺呀,整天挑上个担子,拿上个拨浪鼓到处串乡,换针换线去。”
“哟,一个做小买卖的,那也得会吆喝才行啊!”
“我会呀,”神气地说。
“那你吆喝两声我听听。”
“你等等,”他跑到屋里拿来一个小拨浪鼓,搬起了一个小板凳儿搭在肩头,右手举起拨浪鼓摇了两下,开口便喊,“哎,拿铺衬烂套子来,换针换线喽——”
“嘿嘿,还像那么回事儿,”德风乐了。
墀儿接着又喊道,“我这儿有针头线脑,顶针儿,发卡,岁数大的,年龄小的,小媳妇儿,大姑娘用的样样齐全,来喽!”有人夸他就更来劲了,“我以后还要把担子挑到京城去,那里的人儿也需要这些东西吗,大爷?”
“需要,哈哈哈,哪里的人都需要,”对孩子说,“别说,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德风又对德和说。
“那波浪子一来,小孩儿们儿就跟着转,早记得滚瓜烂熟了。那天,咱村儿来了一个要饭的磕巴,贾本成那二小子还骂人家了一长串的词儿,他们都记住了,墀儿,给你大爷学学!”
立墀开口就来,“磕巴嘴儿,喝凉水儿,凉水凉,吃冰糖,冰糖冰,吃烧饼,烧饼烧,吃火烧,火烧火,吃蜜果,蜜果蜜,吃大屁。”
“哈哈哈,墀儿,这样的话,可不要学,这都是编排人的。”
“还有编排他们家的人儿的呢。”
“怎么说?”
“地方,地方,走得快当,一步五尺,二步一仗,三步一仗五,四步两仗,五步两仗五,你爹是个二百五。”
“嘿嘿嘿,这又是谁编的?”
“不知道,以后可别乱说去,会惹祸的!”德风严肃地说。
“噢,知道了。大爷,还有一个编排老嫲嫲儿的呢。”
“你学学看。”
“老嫲嫲儿,轧疙瘩,轧不烂,擦菜饭,擦不熟,快梳头,梳不上,快上炕,上不去,噗嗤噗嗤放大屁。”
“哈哈哈,这些小孩儿们儿,真会糟践人。”
对德和说,“我说三弟啊,你这俩儿,一个种地,一个做小买卖,可热闹了。以后不愁吃喝了,可也得好好引导啊。”
“大哥说笑了,小孩儿们知道啥呀,都是一阵儿新鲜,过了这一时,过后还不知怎么样呢?”
“不论怎么样,咱那孩子他有想法儿,不走歪门邪道儿就行,起码是自食其力,比什么都好。”
“这才一点点儿,还早呢。”
“这老人们都说吗,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这大的都快十岁了,可不能小看了。”
“你还真当真了?”
“你们两个可要听爹娘的话,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两人在旁边开始打闹起来。
“大爷跟你们说话呢,听见了没有?”德和呵斥道。
“嗯,听见了,爹!”
“大爷给你们说的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听爹娘的话,”老大说。
“做个有出息的孩子!”老二跟了一句。
“好,真是个好孩子,下回大爷再回来时,看你们学习的怎么样了,我可要检查你们有没有进步哟。”
“嗯!”两人都应道。
大年初一,前徐家有个叫徐长忠的人,带着孙子来到家里拜年。立庆娘赶忙招待,好酒好肉上桌,热情倍至。临走时,立庆娘还装满一篮子馍馍和果子,再加上一块儿大肉送与他,他感激地快让孙子给立庆娘磕头。
送走他们爷孙二人,德风问立庆娘,“他这是……?”
“他们弟兄几个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年年如此,我时常周济他们,我就见不得人家受穷,也是没有办法,那么多人,只有二亩地,收成再不好,那就更难了。过年连个饺子都吃不上,去年他实在没法了,到我们家来,借走了半斗麦子,算是有了过年的饺子了,他还说,他要是还不上,就让他儿子还呢。咱也是救急也救不了穷啊,唉……”
“这世道就是如此,只要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吃个饱饭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德风说。
“他们每年农忙时也来给咱忙忙秋收,人倒都是好人。”
“还是缺乏经营之道啊,光靠天怎么行啊!”德风也摇摇头。
“咱也是能帮就帮点儿呗,人家都上门儿了,这大过年的,总不能把人家赶出去吧?”立庆娘又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咱就当是救人了,积德了。”
“是啊,做了总是有的,人们总会记得你的好的。”
“是啊,你有事儿时,人家自然就会来帮忙的。”
“这叫人心换人心,您做得对!”
“咱只能帮到这儿,其他也无能为力了。”
“你可谓贾家的大善人了。”
“瞧你说的,我这是为谁呀?”
“哈哈哈。”
“我这是为你们铺路呢!”
“还是你想的周全,贾家的大善人!”德风大声地说。
为儿子的婚礼,也为了过个团圆年,德风一直等到正月十五。这是个团圆吉祥幸福的日子,是年后的第一个美好的节日。立庆娘为了这个好日子,与婆婆携手做起了枣泥元宵,让大家尝尝元宵的香甜,体会一下团圆的美好。德风又带着孩子们忙着扎起了象征团圆的灯笼,做个与往年不一样的灯笼。让孩子也看个新鲜,长长见识。德风动手并指导孩子们一起合作扎了一对儿莲花灯,绿色的底座,粉红色的莲瓣灯身,灯口处配以黄色,就似花蕊,夜幕降临,点上蜡烛,通透鲜亮,悬于门口,宛如两只硕大的莲花,显得绚丽多彩,甚是好看。邻里乡亲见了无不称赞,都说,“看看人家,究竟是京城来的,见过大世面的,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式样新颖,大气不凡,漂亮又好看!”
听到别人的称赞,孩子们自豪的劲儿就别提了,小女儿说,“这是俺们和爹爹一起扎的。”
“我还帮忙糊纸了呢,”墀儿也插嘴道。
“你爹的手可真巧,扎出来的灯笼真好看!”邻家小孩儿说。
“俺爹说,他在京城里看到的灯可多了,有好多好多。”
“那叫你爹也给俺们扎一个呗?”
“那可不行,要是你们家也有了,俺们家的灯就没人看了。”
“真小气,不跟你玩儿了。”大家扭头就跑开了。
“吃元宵喽,吃元宵喽,”听到喊声孩子们就都进家去了。
看着花灯,吃着元宵,再看看天上的月亮,在众多小星星的衬托下显得分外明亮,一家人坐在一起,体会着这美好的时刻,享受着这团圆氛围,是那么地和谐美好。
时间过得真快,十五过去,年就算过好了,好多年都没有这么休息了,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既温馨又快乐,很令人回味,可又要远行了,也真的舍不得离开亲人们。
“立庆他奶呀,我明儿就走了,”抬头看看妻子,“你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有没有让我做的事儿了?”
“有着做不完的事儿,需要你的地方多了,你能做吗?”妻子也叹叹苦境,“其实啊,这家里的活儿哪有个完啊,做不了的,有事儿我就叫德和帮帮忙,孩子们也大了,都能帮点儿了,爹娘也能帮着看着点儿,他们岁数也都大了,我现在一个人也都习惯了,谁让我是你的媳妇呢?”
看着这个家,每一个人,德风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儿。尤其在这要分别的时刻,看看为这个家操劳受累又善解人意的妻子,白发苍苍的父母,他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怕被媳妇看见,忙转身拭去。
“爹呀,你就别走了呗,再多陪陪我吗?”小女儿插嘴说。
“不行啊,爹已经在家里快一个月了,京城里还有活儿等着爹去做呢。”
“让别人去做呗。”
“别人可干不了爹的活儿。”
“那怎么办呢?”小女儿没有注意了,“那……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呢?”
“等爹把你们的嫁妆都挣到了就不去了。”
“那我不要嫁妆了。”
“傻闺女,你不要了还有你姐姐呢?”
“那还是要等的,太久了。”
“好闺女,很快就到了。”
“好了,好了,快去跟你姐睡觉去,让你爹也早点儿睡,他明儿还要赶早路呢,”立庆奶催促着孩子。
“嗯,听你奶的话,快去吧!”
小女儿不情愿的去和姐姐睡觉去了,“爹,你可要快一点儿挣呀!”临走时再补充了一句。
“你看看,连孩子也不情愿让你走……”立庆奶一边收拾着铺盖一边说。
“我也知道你的难处,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这么多事儿也一一解决了,我们也都不年轻了……”有些伤感,“看,你都有白头发了。”
“你不也都一样吗?我不容易,你也不容易,一个人在外边儿。”
“我也就是个人管个人,你就劳累了,还要孝敬父母,照顾老人,又要管教孩子,还要操心地里的活儿,你更不容易啊。”
“不管怎么样,家里还有个帮忖的不是?地里的活儿请短工,一些累活,他小叔都干了,也就是还养个鸡,喂个猪,放个羊嘛的。”
“爹娘也老了,这不都需要你照顾吗?”
“这点算什么?谁家不是这样?再说还有老三家的,有人帮忙的,好了,不说了,明儿个你还要赶路呢,”德风媳妇端来一盆热水,“快抹一把脸,再洗个脚,歇着吧。”
上了炕,吹了灯,暖暖的热炕,温馨的被窝,二口子依偎在一起,回味着往日的温情,在不知不觉中甜蜜地进入了梦乡。
正月十六一大早,天还未亮,立庆娘就起来烧水做饭,为远行的丈夫做好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也为早起的父母送上新的一天的问候。
吃了面,向父母打了声招呼,看了看熟睡中的孩子,又望了望儿子新房的门口。“我把立庆叫起来送送你吧?这天儿还没亮呢,叫他跟你做个伴儿,也好说说话儿。”
“算了吧,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这对年轻人,真是的。”
“孩子们刚成了亲,还正是黏糊的时候。”
“立庆这孩子也没个脑子。”
“算了,我走后,家里就全靠你了,你就多费心吧!”
“这还用说吗,孩子们也可以帮帮我了,再说,有了儿媳妇儿,这就多了一个帮手了。老人们也能帮点儿,还有他叔可以帮忙的,你就不要记挂家里的事儿了。你自己在外边儿也照顾好自己,啊?”
“放心吧,我一个大男人什么都好办。倒是你,一个女人家,有事儿就和德和商量着办啊?”
告别了亲人,话别了妻子,就要踏上了回京的路程。刚一出门,德和套好马车已在门上等候了,德风非常吃惊,“德和,你这么早啊?你也不多睡会儿?”
“瞧你说的,你要走了,我送送你还不应该吗?还跟我客气,又不是外人儿,咱们可是一个娘生的。”
“我是说,还这么早,天还没有亮呢。”
“你不是更早吗?上车吧,咱们走!”德和对大哥说。
“德和,你也不早一点儿过来,也好吃点儿东西,你这饿着肚子能行吗?”嫂子说。
“没事儿,大嫂,回来再吃也来得及,不碍事儿的,再说了,这不还早嘛。”
“嫂子,回去吧。”
“回去吧,啊?”德风深情地说。
德和挥起鞭子往空中一甩,“啪”地一声,马车就启动了。
送别了丈夫,立庆娘久久地站在村口,凝视着远方,直到看不见那熟悉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慢地挪动起那沉重的脚步,朝家中走去。一路走,一路喃喃地说,“又要等待那漫长的一年光景了,真的好羡慕别人,一家人日夜相守在一起,虽然吃苦受累,身边儿也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啊,也有个呵护倍之的人啊……可别人未必不羡慕我们,住得宽敞,吃得饱,穿得暖,还有个零钱用。这世上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家啊,丈夫不在近前,可有儿女的陪伴,该知足了,”想到此,她的脚步也轻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