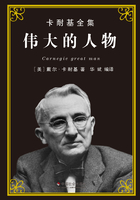任翰墨翘起大拇指。“河南无人可比,老夫望尘莫及!”接着感叹,“余志于翰墨五十余载,第一次大开眼界,天外有天,后生可畏啊!”
周围的文士们也齐声赞颂。有个文人趁机拍知府的马屁:“我府出此奇才,是彰德人杰地灵的风水使然,更是地方长官一贯修文重教之力呵!”
知府脸上立刻放出光彩,“此言不差。地方昌盛,人才为本。本府也是二十年寒窗苦读,才进士及第的,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只是本府财政收入有限,入不敷出,捉襟见肘,难免力不从心。不过再难再穷也不能辍学穷教,凉了士子们的心,洹水书院的事不能再拖,回府立马拨银一千两,里外修葺一新!”
他侃侃而言,在场的士子们早已喜出望外,又是一番称颂。刘更新却有点不耐烦,瞅住个空子忙插嘴道:“知府大人,先不说别的,咱们打的赌还没兑现呢!”
“本府一言九鼎,当场兑现!”知府笑着,叫过身边衙役,把准备给任翰墨的润笔银取出一半交给更新,“这是十两银子,你先收下。你不愧新榜案首,今日出手惊人,堪称俊杰,是我府荣耀。本府要请你和任老先生等彰德名士欢聚一堂,共商振兴文坛大计,然后再备轿送你回林县家乡可好?”
任翰墨一班文人齐声叫好。更新偏着头想了想说:“俺今儿本打算去岳飞庙的,如果那样就要多耽搁一天了。——就怕我爹娘在家等得心焦,不过也不当紧。”逗得大家一阵笑。
更新接过银子,招呼刚才搭脚手架的那个“半脸胡”说:“我答应每人给你们一两银子的,十个人,正好,拿去吧。”“半脸胡”和那帮苦力齐刷刷跪到更新和知府面前,千恩万谢。
说话间人潮又起,大家挤着喊着,争看更新这位天才少年。不知是谁扛来一顶亮轿,众星捧月一般把更新抬了起来,锣鼓唢呐也喧天地响。于是乐队开道,一班人高高地托起亮轿,更新一下子从人群中冒出来,望着黑鸦鸦一片人海,张张大脸都在盯着自己,小更新窘得满面通红,连连向周围朝自己招呼仰望的人们拱手致谢。人们抬着更新绕场一圈,又向城里走去。一直把更新抬到知府衙门。
虚惊
夜已经很深了,刘继基仍无一点睡意,坐在炕沿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弄得屋子里烟雾腾腾。夫人虽然躺在被窝里,也没有睡,呛得一阵阵咳嗽,坐起来嚷:“抽!抽!抽!熏獾哩,想把人呛死!”刘继基放下烟袋,并不答话,看看正在变小的灯头,拿起油壶往高脚皮油灯里添了些油,这才自言自语地说:“半个月了,还不回来?”
从儿子离家那天,他就盘算着,几日应考,几日结束,几日放榜,几日归家。可今天已经超出放榜的日子八天了,仍无消息。几天来,他每天都到村头去等,从早到晚,眼都望穿了,就是不见儿子的影子。对儿子的学识,他不怀疑;考中也没问题,就算落榜,对一个未成年的童生来说也算不得什么。他担心的是儿子心高气盛,放荡不羁,招惹出什么是非来。
这些心事太太心里也明镜儿似的,见丈夫不说话,她像在安慰丈夫又像是在安慰自己似的说:“咱更新虽然不懂事,还有辛先生呢。六十多的人,应考也不是一回两回了,熟门熟路不会有啥闪失。”
“要是一般孩子,那倒不会有啥,更新是安分的么?他会听辛先生的么?”刘继基述说着自己的担心,“当初不该听你这妇道人家的话,让他带那么多钱。”
“孩子出门,多带些钱怎么了?人常说穷家富路嘛。”夫人朝他一撇嘴,“难怪人家叫你铁公鸡哩,对亲生儿子都抠门儿!”
“你懂什么!城里是个花花世界,妓院烟馆什么没有。没听人说,到了那地方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你忘了那一年我去彰德府买牲口……”
“忘不了!”夫人咬牙切齿地说,“一根牲口毛没买回来,却跟一个小妮子上了床,白花花的十两银子让你填了屄窟窿!”
“唉,你是不知道,那小妮子多会缠人。跟皮胶火漆似的贴到身上撕都撕不开……我也后悔死啦!”
“后悔?后悔带的银子少没有欢够不是!怨人家缠粘,你还巴不得呢。过去半年多了还说那小妖精脸蛋子多嫩,身上多香哩!你下头那东西就是那回使坏的……”
见她越说越离谱,刘继基慌忙拦截,“你别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好不好。你想想,三四十岁的人都把握不住,咱更新十三四岁,情窦初开,气血两旺,万一他……”
这么一说,夫人也慌了,“那可怎么办呢?……要不,你明天就进城找找!”
“也许是我多虑了,再等等看吧。”
……
老两口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一宿没睡。天一亮刘继基就出门到村头去了。
那棵抱不住的老柿树,巨人般的日夜站立在村口,像一个忠诚的卫士。秋风已过,满树的柿子由青变黄,间或几个熟透了的,红红的小灯笼一般挑在枝头。树下一条黄土路,似一条粗麻绳,弯曲着延伸远去,使山村和山外世界联系起来。刘继基站在树下顺着“粗麻绳”的方向使劲望着,满眼成熟的庄稼,谷子、玉米、豆子、高粱……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再向前望目光便被山坡不客气地挡了回来。望得眼酸,只好蹲下抽烟。抽几袋烟,再望一阵。望一阵再蹲下抽烟,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树荫罩住了他,又慢慢地向东移去。他心里越发焦灼。不只他心焦,全村人都挂念。更新和辛向举村里两个最有文化的人赴考,是全村的一件大事,谁能不关心呢?刘继基在等,大家也在等。到了后晌,人越发多了起来。大家盼望着、议论着,希望他们盼望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在“粗麻绳”上一下子冒出来。
有人来啦!有人来啦!
不知是谁突然喊了起来。众人的目光便一齐顺着“粗麻绳”搜索过去——极远处一个黑点正在向这里移动。黑点越来越大,不错,是一个人!近了,更近了,可以看出那人还挑着担子——大家失望了,不是他们盼望的人!那人很快到了跟前,是那个老油郎,挑着两只油篓,人没到,浓浓的芝麻油香先到了。
老油郎老熟人,他朝大家笑,大家却没理他,今天对老客户都失去了往日的热情。老油郎也不在乎,只管放下挑子,找块石头坐了,摘下头上的草帽扇着。说道:“我今天不是卖油,是报喜讯送喜油来的,大家不欢迎吗?”
石匠说:“不是不欢迎,是大家心里焦急,没有心思。村里两个文化人去考秀才,快半个月了没个信儿,你说急人不急人!”
老油郎听了一拍大腿,“俺报的就是这个喜讯儿!”
人们听了,似信非信迟疑着围了上来。
“刘更新、辛向举双双中了秀才。刘更新考了第一,取了个案首。知府大人设宴款待,还要用八抬大轿送回家乡呢!”
“真的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刘继基一把攥住老油郎的胳膊,盯着他急切地问。
“这事早已传遍了彰德府,也是俺亲眼目睹!”接着老油郎把前天进城卖油,在南门外看到的刘更新怎样与知府打赌,怎样登城题字,知府如何赞赏,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遍。
讲到刘更新飞笔加点时,老油郎更来劲,一边说一边比划,说得风雨不透。只见他说着拉开架势,顺手抓过老石匠头上的黑毡帽作笔,柿树桩当城墙,一个立马开弓,平空跃起,左手指,右手挥,喊一声“着!”帽子直棱棱脱手飞去,噗的一声撞到两股树枝分叉处,欲落未落,颤颤悠悠,掉不下来。大家如临现场,时而紧张,时而欢笑,望着毡帽颤悠心里也颤悠,仿佛看到了城门上龙飞凤舞的那一“点”,看到了人山人海欢呼雀跃的动人场面,醒过神来一齐哗哗地拍手叫绝。
老石匠刚刚剃过的脑袋闪着青光,抓挠了两下却顾不得去摘树叉上的毡帽,着急地追问:“快说,后来呢?”
接着老油郎讲到众人用亮轿抬着更新游街的事。
“你们没见那场景,真是人山人海,万家空巷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挤着拥着呼着喊着争看刘更新。特别是那些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个个都着了魔一般。这个说:瞧那白生生的脸蛋儿,羊脂玉似的,像这样才貌双全的后生普天下能有几个!那个讲:要是能嫁一个这样子的郎君,这一辈子也不枉当女人了!更有女叹:找这样的郎君,唉,不知道要烧几世高香才有这福气!说着赞着夸着叹着,不转眼地盯着看着,亮轿走到哪里,姑娘媳妇们追到哪里。从南门到北门,再从北门到西门东门,绣鞋挤掉了也不顾捡,脚被石子硌破了也不嫌疼,着了迷中了魔似的直往前挤……”
卖油郎好口才,说鼓书似的,连说带比划,关键处偏斗闷儿摆噱头卖关子。急得听众抓耳挠腮地催促:“快说,后来呢?”
“追着撵着赶着看着,一直追到亮轿把更新抬进了知府衙门。”
“再后来呢?”几个小伙子听得痴了,继续追问。
“再后来清道工打扫街道,捡了一大车绣花鞋!”
哗——!全场人都笑倒了。
听老油郎这么一说,刘继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既然今天儿子一早已动身返乡,这会也该到了,可为什么还不见回来呢?他心急地问老油郎。老油郎说,彰德府到这里七八十里路,坐轿不比骑牲口,最快也在太阳擦山。
正说着“粗麻绳”的那头又现出一个黑点儿,这回准是更新!
人们跷起脚后跟望着。石匠的儿子小石头与几个和更新差不多大的孩子,跑着前去迎接。“黑点儿”动得出奇地快,很快看清楚了——是老南瓜,不是更新。大家又失望了,埋怨老南瓜不该在这条道上、这个时候出现,惹得大伙空欢喜一场。
老南瓜并不知道大家的埋怨,慢性子的人今天一反常态,跌跌撞撞地跑得飞快。只见他红黄的南瓜脸上满是尘土汗道,喘着粗气边跑边喊:“不好啦,不好啦!……快……快去……”气尽力竭,眼看就要跌倒的样子。
大家一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石匠上去扶住他,让他慢慢说。老南瓜定下神来,嘴里拉着风箱说:“东诸翟村董家的一伙人把更新劫走了。劫到村里去啦!……”
这不是要报夺井之仇吗!
大伙一听,也都急了。为了争那口井,董善仁被个孩娃子的刘更新设计输了官司,心里堵了口气,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决不善罢甘休,更新落到他们手里,不是羊入虎口吗?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更新是为了咱全村人得罪董恶霸的,他有了难咱们不能不管!”
“小更新智谋超群,是下川村的宝贝,夜明珠子,就是拿十个二十换一个也要把他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