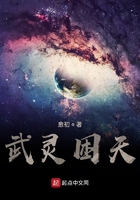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美妙的奇遇。我们相信,爱会发生无极限裂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最早相遇的,是一双手。手让我们脱离黑暗世界,让我们感知冷,感知哭声,感知一个女人垂死般的疼痛。我们被一个流了满床鲜血的女人,抱在怀里。我们还不认识这个人,我们的眼睛还睁不开,我们还说不出气味,但我们熟悉这个人的气息,有海洋的广阔和天空的壮丽,她带来的暖流伴随我们一生,她怦怦的心跳声,是我们一生的鼓点。我们不会忘记这个鼓点,给我们激越,振奋,鼓舞我们跃上战马,鼓舞我们穿越泥淖。这个人将引导我们,认识草木,认识虫鱼,认识色彩和四季,认识我们内心不被认知的部分。手抱着我们,托举着我们,我们的重量与世界的重量相等。我们与乳房相遇。那里有生命的甘泉,是永恒的水井,是月亮的环形山。
棉花包裹着我们。棉花从地里摘下来,一朵一朵地摘,晒干,请来弹棉花师傅,一弓弦一弓弦地弹开,云絮一般蓬松,被一架织布机,咿呀咿呀地拉丝扯线,织成布,被一针一线缝制成棉衣。棉花,是植物中的母亲,纯洁,雪一样白,阳光一样温暖。棉花给予我们另一层皮肤。我们现在就去认识棉,在五月,地垄一条条,远远望去,像一张张空床,栽下棉秧,除草施肥洒水,棉一寸一寸地长,叶从枝节上抽出来,八月开花,紫黄相染的颜色从一个蕊里,哗啦,肆无忌惮撑开,坐桃之后,白霜来了,细晶体的霜,结在棉叶上,像蛀虫一样吞噬叶绿,棉叶发黄发白,出现斑斑的麻点,经脉老死,棉叶渐渐被秋风送走,棉花迎霜而开。我们有了衣裳,有了棉鞋棉帽。棉花使我们免除裸足而行,裸身而立。
我们喝米汤,吃米糊,喝粥,吃饭,我们像春日的柳枝,日日抽枝发叶。这些食物,来自同一种一年生栽培谷物。耕耘,插秧,灌溉,施肥,收割,翻晒,入仓,碾米。我们牢记它,它就是苍生。
摇篮带来了我们的第一支歌谣。我们躺在摇篮里,在秋日的阳光下,摇篮被一只手摇啊摇。母亲轻轻地唱起: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那)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啰,无脸见爹娘/朗哩咯郎哩咯郎咯哩咯郎/没有学问啰,无脸见爹娘……
与早晨相逢,与黄昏相逢。我们相逢,在每一天。
我们认识树木,认识草露。我们认识河流,认识高山。当我们走出自己的门,便有了无数的相逢。我们去远方,坐了几千公里的火车,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峦,我们都是为了相逢。与一个人相逢,与一种生活方式相逢,与陌生的地方相逢。与自己相逢。
对每一次相逢,我们都充满期待和好奇,这是对未来岁月的神往。我们被诱惑着前行,不知道前面是玫瑰园还是陷阱。
192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日,莫斯科大剧院,著名舞蹈家阿赛朵拉·邓肯,由美国专程来此演出。这一天,邓肯与诗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相识,当两人初次紧握双手时,彼此都感到又惊讶又兴奋。爱神来到了他们心中,一见倾心,互相钟情,很快陷入热恋。
叶赛宁当时26岁,而邓肯已经43岁,两人语言不通,叶赛宁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彼此没有语言交谈。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两人如痴如狂的热恋。叶赛宁正式与邓肯同居,并开始了蜜月旅行,先后经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最后到达美国,历时一年多。
因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两人感情出现了裂痕,最后分道扬镳。
1923年秋,叶赛宁和邓肯返回莫斯科不久便开始分居。叶赛宁将邓肯送到高加索疗养,自己则和两个妹妹一起搬到过去的情人别尼斯拉夫斯卡娅那里去住。邓肯于1924年秋离开了苏联。她和叶赛宁的罗曼史彻底结束。别尼斯拉夫斯卡娅是个隐忍的女孩子,内心刚毅,做事果敢,原谅了叶赛宁的移情别恋,再次照顾他的生活。
1925年3月,叶赛宁在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家庭晚会上,认识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列夫娜。彼此一见钟情,疯狂热恋。5月,叶赛宁来到巴顿,给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寄回一封信,提出分手。这是叶赛宁写给她的最后信函。9月,叶赛宁与索菲娅结婚。随着对索菲娅的失望,叶塞宁患了精神抑郁症。12月,叶赛宁一个人离开莫斯科去克里米亚,同自己的两个孩子告别后,再去往列宁格勒。1925年12月28日凌晨,叶赛宁在旅馆自杀,年仅30岁。
邓肯得知叶赛宁自杀的消息后,致信巴黎的报纸:“叶赛宁悲惨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两年后,即1927年,邓肯走在街上,精神恍惚,围巾被卷进汽车轮子,遭受车祸而死。邓肯在自己的自传里曾说,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和叶赛宁在一起的三年,超过了其他快乐时光的总和。
1926年冬,叶赛宁去世一周年,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诗人坟前跪了许久,而后饮弹自尽。她的口袋里留有遗书:“1926年12月3日我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残生……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她还不足30岁。
每一次相逢,于叶赛宁而言,都是美丽的罂粟花——绚丽,妖娆,却让人窒息。万劫不复的心灵灾害在相逢里,人生美好的夙愿也在相逢里。
浪漫的相逢,彼此一见钟情,没有人不向往。法国人更甚,视浪漫的艳遇为生命再现。法国诺昂乡村女孩露西·奥罗尔·杜邦在1832年,以乔治·桑这个男性名字作为笔名,发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一举成名。露西·奥罗尔·杜邦长相并不出众,肥脸,身材略显臃肿,性格强悍。她抽雪茄,骑马打猎,穿高筒马靴,但她内心细腻,情感丰富,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了浪漫情调。27岁时,她与情人私奔,前往巴黎生活。她的一生,有无数的艳遇,一次次地俘获男人,和小说家缪塞、音乐大师肖邦的恋爱,更是交错复杂。在她的诺安镇庄园,日日高朋满座,有诗人缪塞,音乐大师肖邦和弗朗茨·李斯特,以及文学家福楼拜、梅里美、屠格涅夫、小仲马和巴尔扎克,还有画家德拉克洛瓦,拿破仑的小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座上宾中,绝大多数都是艺术天才,也是她的床畔迷恋者。她的每一段情感,都凄婉哀怨,美丽动人。她手中发出的情书,细腻,深情,撩拨心弦。她有一封写给缪塞的情书,堪称经典:
……
爱情是一个庙,凡恋爱的人建筑这个庙作为一个多少值得他崇拜的对象。而庙中美丽的东西,并不完全是神,倒是神坛。你为什么要怕重新来试行这一着呢?无论神像是久已竖起,或即刻会跌成粉碎,然而你总算已经建了一个美丽的庙。你的心灵将住在庙中,内中并且将充满敬神的香烟,而一个像你的心灵一样的心灵必定创造伟大的工作。神也许有变迁,但当你自身存在的时候,这个庙是会存在的。它是一个庄严的避难所,你可以在敬神的香烟中把你的心锻炼得结结实实,这颗心是十分丰富而有力,当神丧失了根基的时候,此心即可重新更换一个神。你以为一种恋爱或两种恋爱足以使一种强健的心灵精疲力竭吗?我也早已相信这一点,但我现在才知道情形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火,它总是要努力燃烧起来,并且通明透亮的。这也许是一个人整个的生命中一种可怕的,庄严的和忍耐的工作。这是一顶有刺的花冠,当一个人的头发开始苍白的时候,这花冠便扬苞吐蕊,现出玫瑰花来了……
爱而不见,相逢便是一种诀别,是隐忍和终生的痛。德国作曲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生于汉堡,逝于维也纳,是维也纳的音乐领袖人物。年少时期,生活非常穷苦,他的音乐启蒙来自他父亲——一位乡村音乐教师。20岁那年,即1853年,他认识了音乐大师罗伯特·舒曼(1810—1856)。勃拉姆斯在舒曼家弹钢琴,在曲子结束时,从琴键抬头的刹那间,看见了34岁的舒曼夫人克拉克·舒曼,他第一眼,便深深地爱上这位端庄美丽的钢琴家、作曲家。三年后,舒曼患严重的精神病去世了,勃拉姆斯为他送葬,随后不辞而别,前往维也纳,再也没有见过克拉克·舒曼。克拉克·舒曼40岁生日当夜,收到勃拉姆斯写的《小夜曲》。《小夜曲》含蓄、古典,像窗外越飘越远的云。克拉克·舒曼次日致信勃拉姆斯:“《小夜曲》就像我正在看着的一朵美丽的花朵中的根根花蕊。”1883年,77岁的克拉克·舒曼与世长辞。勃拉姆斯日夜弹奏她生前喜爱的钢琴曲,伤痛不已,第二年便与世长辞。在与克拉克·舒曼相识的40多年里,勃拉姆斯始终没有向她表露心扉。在维也纳的40多年里,勃拉姆斯给克拉克·舒曼写了无数的情书,但一封也没寄出过。终其一生,勃拉姆斯没爱过其他人,一生未娶。他把自己当作对爱的祭献。
液体中两亿分之一中的生命细胞,与另一个生命细胞相遇、碰撞、结合,是生命诞生的奇遇。人与人的相逢相知相爱,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走过千重山涉过万重水,错肩而过无数的人,在一棵树下,在地铁站口,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在一艘客轮的卧舱里,我们相遇了。我们缱绻绵绵。我们难舍难分,执手相看。世界在我们眼里消失,只剩下一轮明月。我们忘记了来路,也忘记了去路,时间在彼此的眼眸中凝固,幻化出一片汪洋。
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与世界万物相遇的过程。我们认识各类种子,认识道路,认识遥远的地平线,认识黑夜。黑夜把落日抬走,把星辰展露出来,让我们明白,离我们最远的星辰,其实离我们最近,把稀薄的碎光撒在我们额头。我们和无数的人相逢相欢,也忘记无数的人。不能忘记的人,是居住在我们内心神庙里的人,是让我们柔肠百结的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会有意外的相逢。这是命运之神对我们的额外馈赠。我与你相逢。你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我起床时,会想,你起床了吗。我吃饭时,会想,你吃饭了吗。我睡觉时,会想,你睡觉了吗。在空荡荡的午后,我坐在灰暗的窗前,会想,你在想什么。窗外的蜡梅花开了,我想起有一年,从海边归来,种下了它。蜡梅是落叶丛生灌木,不易生长,十几年才会长几厘米粗。不易长的树,不易衰老,生长期长,适合长情的人栽种。
相逢,就是一个怀抱容纳另一个怀抱,一只手牵着另一只手,一张脸贴着另一张脸。相逢是眼里迟迟不滑落的泪水,是掌灯人慢慢从暗中显现出来的面影。相逢一个人,和忘记一个人,同样艰难。某一天,我们走在街上,突然遇见多年前相识的一个人,曾日日夜语,彼此牵挂,后来不在一起了,过了很多年,我们都以为彼此相忘于江湖了,饮马江边,在不经意的街口,再一次遇见,会怎么样呢?美好的相遇会翻腾出苦楚的沉渣。
“我看不厌你的脸,每天都想看。”假如有一天看不见了,在模糊中,还觉得伸手可及,又会是什么呢?或如《一生所爱》所言:
苦海 翻起爱恨
在世间 难逃避命运
相亲 竟不可接近
或我应该 相信是缘分……
相逢过一个人,却再无重逢,心中所盼,又那么急迫,绵绵不绝。在早晨,露珠厚重,在深夜,烛火微弱,如勃拉姆斯般,开始写信,写完了,夹在抽屉底层。信中,写信人会反复提到,一条寂寥的街道,一个大雪之夜,江水汹涌,火车在奔跑,群山隐去,太阳慢慢抵达窗口。写信人的头发会被露水染白,蓝衫会被烛火熏黑。写信成为写信人一生最重要的事。写信人会想起她的咳嗽和耳语,想起她的口腔溃疡和荨麻疹,想起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情境:把虾剥开,喂进她嘴里,她不说话,怔怔地望着自己,暗黄的灯光在她脸上荡漾……
我渴望有这样的相逢,当你从天边匆匆归来,干涩的芦苇发出嫩芽,夕阳久久不沉落,桥外依然是雪的意境。我不知道我是热泪盈眶,还是沉默不语。
我们也会和无数的厄运和不幸相逢。我们相逢过的每一个人,都会和我们作别。大多数的人,没有作别便已消失在茫茫人海。这是我们悲伤的根源。我们终其一生,日日顾念的是什么?内心不能融化的坚冰又是什么?最后,我们与死神相逢。死神阴冷的手,牵着我们,进入一个黑暗的冰窟。我们下沉,在冰洋里漂浮。我们沉默,黑夜无穷无尽,再也没有了相逢的际遇。这是我们相同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