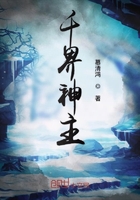道清在勤政殿外跪了良久,李德贵却丝毫没有放她进去的意思。他与夏震一般说辞,奉了皇命,没有办法。道清心中恼恨,又吹了凉风,气血上涌居然晕了过去。她醒来的时候,身在自己寝殿中,赵昀在一旁坐着。她隐约看见赵昀眼中露出一丝担忧,想捉,却没有捉住。皇上已经换上一副冰冷的面孔。
“皇后入宫也不少日子了,旁的没学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倒是学得十足。人人皆知帝后不和,太后训斥朕,大臣劝诫朕,你满意了?”赵昀的声音很响,大概整个大内都有了回声。
“若琴不是刺客,请皇上放了她。”道清想解释,让赵昀难堪非她的本意。哪知越解释,皇上的脸色越难看。
“朕若不捉她,你就不来找朕了是不是?”赵昀这话说得很轻,飘过道清的耳边,好像幻觉一般。“皇上说什么?”她问。
赵昀气不打一处来,说:“朕说你笨,你蠢,脑子里就是一团浆糊!”
道清觉得莫名其妙,皇上今日分外地阴晴不定。若不是为了若琴,她会将他轰出坤宁殿。“臣妾愚钝,人与事是越发看不清了。臣妾只知道,若琴无辜,她不该被捉。”她憋了半天,还是想求情,可话说得有些生硬。
赵昀皱眉叹气了半天,平复了许久,才在她的床沿坐下。他对着她因为方才晕倒还未恢复血气的小脸,无奈道:“你能不能长点心?皇宫大内,她一个弱女子如何做到来去自如?她会害了你的。”
道清有些懵,那明明是一个豁出性命要救自己爱人的女子,她不信:“她只想救人而已。”
赵昀沉默了,他没有办法与她说得太清楚。若琴穿过大内重重禁军入得坤宁殿,若不是有人刻意放水,她怕连丽正门都入不得。而这背后的人不过是想看看若琴会去找谁,她去找的能帮助她和赵竑的人必定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
“不是谁的命都可以救。在这宫里,你只要用心看清朕,只看着朕,就够了。”他转身走了。他不能在坤宁殿待太久,周围都是眼睛和耳朵。这皇宫,比他想象得还要复杂,而他,只想她安好。
道清被禁了足。她只知道后来皇上与史相闹了一场。皇上看中了原先是济王府中的歌姬,要留在身边。可史相说烟花女子不能留是要祸国殃民的。最后好像是史相赢了。他鼓动一帮老臣,直谏皇上,把皇上逼得不行,只得交出那名女子。她不知道的是,赵昀已经尽力在保若琴了。若琴是史弥远在赵竑身边使用过的针,人是美,艺是好,但用过了便不能再用,特别是放在皇上身边。若有一日皇上知道了若琴曾经在赵竑身边扮演的角色,这只针便能长成隔在他与皇上之间的一堵墙。他不可能让若琴留在皇上身边,同时也让皇上明白,现在到底是谁在做主。
赵昀得不偿失,美人没得着,却得了个贪慕美色的花花名声。赵昀倒无所谓这些虚名,只是担心道清又会当了真。他哪里真的看上了若琴,他是为了赵竑。
他忆起登基之后与赵竑的一次见面。他从赵竑眼中看出不甘和愤恨。数日前还是赵昀给赵竑请的安,这次就变了位置。对赵竑来说,如此巨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回不了神也是自然。赵昀将一切尽收眼底,他叫了内侍给赵竑看座,暖了一杯茶给他。赵竑双手接过茶盏,双眼紧盯却是一口也不敢喝。赵昀朝左右挥了挥手,直到看见他们退到殿外,才缓缓开口:“皇兄,朕不害你。”
夺了自己帝位的是他,今日来示好的又是他。赵竑向来对人事毫无防范之心,只是经如此大变,现在是谁人都不相信。他还是恭恭敬敬,拱手作揖,说:“臣愚钝,不敢妄揣圣意,还望皇上直言。”
赵昀突然失笑,说:“皇兄,若你从前就懂得隐忍不发,三缄其口,防范于未然,又怎会落得如此田地?如今你在朕眼中,最值钱不过一条命,你觉得朕会要吗?”
赵竑眼前一片黑暗:“从古到今,太子失势,大抵躲不过一个死字!皇上若要,拿去便是。”
赵昀也不辩驳,说:“等过些时日,朝中人不再紧盯着你,你便上书请辞现任所有官位,朕允你一方土地,让你自去潇洒度日。不知皇兄意下如何?”
赵竑反应了很久,才问了一句:“皇上不杀我?”
赵昀从来不想要赵竑的性命。他坐这个位置也是为了自己能活。“让你一个皇子离乡背井也是无奈之举,保住性命才最重要,不是吗?你可还有什么要求,朕能做到的尽量满足。”赵昀说得真诚,赵竑终于松下一口气。此刻,他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唯有一人。
“我生性寡淡,可遇了若琴才知我也有放不下的人。我明知她在我身边是存了目的,可情这东西我就是不忍挥刀断了它。人心肉长,我就不信若琴毫无知觉。她与我之间只是错了时间。我仍想寻回她,若能有她相伴,此生亦当无憾!”
他们赵氏子孙大约都是情种,若不是放不下道清,他赵昀何苦盘旋于宫廷的漩涡之中?混吃等死也便罢了。他应了下来,说:“朕派人去将她找来吧!”
赵竑那日谢了恩归去,只是谁都没有料到,史弥远居然如此急不可耐,不过几日功夫,便逐他出了京。而赵昀也终是没有保住若琴。
赵昀正觉愧对赵竑之时,与芮又匆匆赶来。他接夏中原密报,赵竑已达湖州,湖州百姓夹道相迎,拥立济王之声不绝于耳。赵昀眉间皱得越发紧,这势头必是有人刻意造出,目的不过是让朝廷再也容他不下。赵昀实在不想连赵竑也保不住。
道清禁足宫中出不去,她不知若琴究竟如何了,消息递不出去也收不进来。有时候她想,索性就活在这个金钟罩里,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大约这日子也能太平地过下去。但这金钟罩罩住的似乎只有她一个人。这日,她清冷的宫中来了访客。贾惠儿从前也会来,不过都是例行问安。她今日也说是来探望问安,不过说出的话却不似来安她的心的。
贾惠儿说:“这坊间的歌舞伎人到底有什么魔力?惹得这世上的男人无不喜爱她们的。前几日,皇上和丞相还为了一个歌姬闹红了脸。皇上亦是男子,受不住歌姬的魅力也是自然。丞相却是严苛了些。若是害怕她红颜祸水,将她遣离了皇上身边就成。可臣妾听说丞相为绝了皇上的念头,将她当众斩了首。皇上可伤心了,连着几日都不见人。估计皇上也是尽顾着伤心了,也便忘了还禁着娘娘这回事儿。娘娘别心急,等哪日臣妾见了皇上,定会再为娘娘求求情的。”
她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好似在讲一个故事。故事里,皇后比不过一个歌姬,甚至还要仰仗嫔妃去为她求取活路。贾惠儿把这个故事说完了,便离开。不过她走的时候面带笑意,因为她的话已经叫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后,面色青白。
贾惠儿走后,道清从内而外皆软作一团,好在秋云在旁将她扶着。她对秋云说:“我原来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有些智慧,看见的,听见的,都能有自己的考量。可在这里,我笨了,瞎了。看到的,听到的,不知哪件是真,哪件是假。秋云,我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