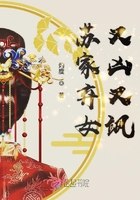“你们放走我妹子,放走我妹子,与她无关的……”聂宁不停呼叫,仍然没人理他,叫到后面渐渐哽咽起来。他懊悔不已,心想如果阿铃没来救自己,也就没有大汉追来,她也就不会跟着落难了。仍见无人回应,他掏出阿铃那把小刀,大力地往笼链劈去,刀链相击,发出‘叮叮’的刺耳声,小刀较软,劈了几十下,仍没见链子有任何损坏。后边一个汉子笑道:“别白费力气了,这笼条和笼链乃纯钢所制,坚硬的很,就算给你上百支刀,也砍不开的”聂宁怒骂:“直娘贼”大汉道:“嘀咕什么?”聂宁大叫道:“我道你着直娘贼,狗厮鸟,撮鸟,腌臜泼皮,你待怎地?”“臭小子,嘴巴还挺臭”说就要拔刀戳去。这时,俞三骑马过来,说道:“大人……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去去去,没你的事”大汉道。
“大人,帮主都不舍得杀这小子,你若是伤了他们,怎么向帮主交代呀”俞三道。
“诶呀,你不卡舌啦,我伤不伤他,你管的着吗?给我一边去”大汉不耐道。
“臭小子,嫌活得太长了”大汉拿起手中的刀在笼子外面虚劈假砍。聂宁知他不敢乱来,只搂着阿铃缩挤另一边,不作声。
那姓辛的听到吵闹声,回头道:“掉江,你干些什么?回前头来”他语气较硬,掉江横了一眼聂宁,便骑回前头去。
聂宁也不敢再叫了,生怕惹怒了他们。阿铃则‘咯咯’笑个不止,聂宁道:“你还笑得出来啊”阿铃道:“你骂起人来,一点不必别人差”聂宁见她终于肯说句话了,如此境况,她竟还能开玩笑,更感对她不起。
铁笼子长七尺,高丈余,置于四轮牛板车上,尾随前面锦衫男人的人马,那人马众多,不下三十,个个配刀带剑,再加七八头牛,犹胜一小支有致的军队。
循着日起日落,聂宁便知他们是往东南而下,这一日经至一县城,城门处人进人出,把门的军卒甚多,当时有好几个军卒检查这列‘军队’,中有一人疑心笼子中为何关有两人,他暗自捏汗。那时,那人问道:“喂,怎么有个笼子,还关着两人?”
姓辛的轻答:“哦,军爷,这是我家老爷的两个仆人,路上想逃走被我们抓了回来,我家老爷心慈,舍不得杀他们,这才买了笼子关着他们,以防他们再次逃走”
那军卒道:“虽是仆人,亦是人,怎可随意杀的”聂宁当时还欣喜了一下,想喊军卒求救。
然接着就见那姓辛的连连应答,左顾右盼两下,扯了腰间钱袋偷偷塞进了那军卒的手中,军卒眉梢一跷,好似惬意。聂宁方知这些人军卒见钱眼开,根本没指望,只好作罢。
‘军队’出了城,一直往东边大道奔去,山坡愈来愈少,地势愈来愈低,白天赶路,夜晚休息,骑了两日马程,锦衫男人把牛马留在一处隐蔽的地方,里面看马喂马人齐备,牛棚马栏的粮草十分充足,设施也很齐全,聂宁暗暗寻思:到底是身何方人物?如此有背景,养马养牛丝毫不计成本,千里转运,还到处设场地喂养的?
他自想不到,也没多琢磨,暗中留意下,只记得那锦衫男人唤那姓辛的大汉为‘五郎’,言行对待无其他手下那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尊敬有加,心想此人于他而言非同一般。其实锦衫男人在夜间休息时,找过一次聂宁,但他仍旧问着那日的问题,聂宁初时恼怒不答,只觉对方无理取闹,事后留心起来,但想一个如山贼头子般的人物,为何不杀自己这个’细作’,而关起来?难道他所问对他很重要?这才想起六年前,于杨文静相遇时,也曾提起‘赖明’这个名字,还道是自己父亲,当时年幼,想不通缘由,如今再次听人道出,暗觉赖明这个人与自己大有关系。而且锦衫男人一定认识赖明,否则他不会提起,心下更加疑惑了,时不时便观察起这个男人,望能探查到什么关联的东西。
留下牛马后,众汉子一路往东而去,铁笼子依置放于木板车上,牵长绳由两人拉着,众人步行而去,不久听到‘沙沙沙’的声音,一眼望去,前方蔚蓝一片,鸥群盘旋,乘风逐浪,聂宁暗赞:人间美景。
走近海滩,见沙岸停了几艘小船,中有两瘦汉,样子似等了许久。众人上了船,划出海五里多之外,便见一个小岛,绿树红花,白云萦绕,宛如仙境。至靠岛深水处停泊,停泊处围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篷梢、封舟、车轮舸数不胜数。那岛上的汉子往铁笼抛下一个大锚,一勾,一提,瞬间升落岛地。聂宁俯瞰一望,蓝水起涌,冲打岛岩。那高岩刀崖离水平面少说也有五丈高,这要是掉下去,绝对没法爬上来了。
拉上了岛,又随两个大汉牵至一大空地上,婢女送来饭菜汤水,一路山吃着中汉子的干粮,也没发现什么身体不适,遂吃了。彼时夜幕降临,海风盈盈,月光明明,树影花影映落地表,慢慢挪移,过了半响,月亮徐徐升起,挂于中央,整片空地照的如白昼一般,耀耀生辉。
聂宁等阿铃睡去,偷偷解了小,遂合眼睡了。
这一觉至天明,忽听闻有人走来,睁眼一看,是那景祀,未走近便叫嚣道:“都快点,都快点……”但见他持着短鞭左右横挥,前边是十几人,衣衫破烂,面容大都清秀,可认出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这十几人走近铁笼,景祀滑动眼珠,笑道:“差点忘了,还有这两小崽子”左手扔出一把钥匙,命后旁的小厮道:“你,去把他们两个带上”小厮道:“是”
聂宁没得反抗,跟于后边。一小厮拿剑指着他后背,他知是防着逃跑,却见那十几个女孩周身并不索链套绳,显然景祀和这小厮都会武功。穿过一丛椰林,好空旷的石地,铺满了作物,黄稻黑谷,瓜果花茶,还晾有药材,好几个仆人不是拿着耙子翻谷,便是摇着筛子挑茬。景祀虚挥鞭子,叫道:“都看着点,谁踩着了,我就送谁一鞭”女孩们自然不敢违背,从旁边的沙地绕过,这时,便见一个皮肤垂松的老婆子走了过来,恭敬道:“景先生可有什么吩咐”景祀道:“嗯,这些个婢女是刚来的,暂且留在仓粮方,你教识她们规矩”“景先生,仓粮方人手虽然缺人手,也不过两三个,婢女一下子来得太多,也不好安排”“多嘴,不见我说了?暂时留在仓粮方,到时候会有人安排的”“是,是”老婆子忙连答。
景祀回转过来,横眉冷眼道:“这位是六婆六司仪,此处乃粮食储备的仓粮方,六婆负责掌理粮方的日常事务,你们好好跟着她做事,做得好的,少不了你们的好处,但谁要是动歪脑筋,我先剁了她双手,让她光着脚干事”女孩们“啊”地惊叫,早吓得冒出了冷汗。景祀瞄了一眼聂宁,走过去从后面一踢他右膝,聂宁“啊”地惊喊,右膝跪倒,景祀道:“我知道你有两条会跑的小腿,哼,这四面环海,你倒是跑给看看”说罢,径直走了出去。阿铃大骂:“呸,不怕我们逃跑还下作了”谁知一巴掌迎去,竟是那六司仪六婆,骂道:“小丫头,多脏的嘴啊”接着又是一巴掌。“住手,不要打我妹妹,要打就打我吧”聂宁道。
他受景祀一脚,对方出尽了力道,只觉膝盖疼痛酸麻,恐怕不是骨折就是断骨了,这海岛四面都是海,没有船是绝计离不开的,眼下唯有顺从敌人,见机行事了。于是劝阿铃道:“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们还得好好活着”“嗯”阿铃点点头。六婆指了指聂宁,道:“小子,咕哝些什”“没什么”聂宁冷道。六婆难得一见有男孩往仓粮处来,又见聂宁生得俊俏美目,心里觉得有趣,见他语气冷淡,然被景祀踢伤,也不免心疼,便不加刁难,安排各人住处,说明了岛上的规矩道理,又分清了各人的活务,各人便各司其职起来。
聂宁膝盖伤得不轻,但也没人理会,六婆安排他去看守晾晒的药材,只需提防鸥鸟燕雀偷吃,倒算个轻松活,坐着木墩,拿着长篱,见鸟走近,赶走即可。午间吃了热粥,小憩,又继续干活。其实只要不动,他的膝盖不会多疼,但晾晒的药材横铺石地,竖放篱团,一条长篱左右触不到,还得瘸走两步,两边防着。他见那新来翻谷子的女孩,每一刻钟就得翻一次,稍微迟了一会儿,或忘了一刻,那六婆便又打又骂的,她年纪上了六十,却虎背熊腰,大手蛮脚的,不落于一个壮年男人。聂宁想到自己膝伤过重,怎么也不敢得罪那婆子,再惹来没好的伤害。
好久,熬到了晚间,吃了送来的稀食,阿铃扶着到了住处,也只是一间简陋的破屋子。男女有别,老婆子把剩下的一间屋子都留给了聂宁住,其余的女孩们则挤在不远处的一屋。阿铃要照顾聂宁,不顾六婆反对,自己跑去聂宁那屋。她摘了许多花草,又撕下了衣块,助聂宁包扎。聂宁想起书上记载疗伤接骨的法子,他摸清了膝盖处的骨头,才清楚是折了下胫骨,忍着疼痛,凭借知觉扭至与髌骨对位,他不深通还骨医术,头次尝试,技术不够精湛,费了好大劲才勉强扭回正位。只是延伤迂久,原该卧床休养,不允许动的,撑持了一天,到底因此加重了伤情,日间时还能勉强移动,这会儿右腿中处已肿成一个大包,他头次扭骨,技术不熟,岛上的草药大都没见过,不知何物,不敢乱用,只嚼了一株白英草敷于肿包,用布块包实潦潦。阿铃见他脸色极白,很是心疼,暗暗抹起泪水。聂宁道:“阿铃姑娘,你知道为什么要把肿块扭至向后突起才可吗?”阿铃不答。聂宁又道:“腿膝胫骨,位于髌骨上下端,上端的髌骨小头与关节相连,内侧有软骨,我折伤了下端胫骨,导致骨头前移,肿块前凸,后扭胫骨往后,对接关节,故而膝盖后关节也肿了起来”阿铃抽泣不说话。聂宁笑道:“你可记住了,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不用我教你啦”阿铃对医理一窍不通,尽管聂宁说得明白,她怎会晓懂?只哽咽道:“我不管别人,我只救你”她声音本就柔婉,这哭起来,更加优柔娇滴,当真让人忍不住的怜爱。
聂宁笑道:“你不帮别人,只帮我,难道还希望我的膝盖再折一次么”阿铃道:“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聂宁道:“好啦,我没事了,你回去睡吧,你究竟是女孩,不要让别人说闲话,不要留在我这了”阿铃对这些礼俗向来不当回事的,硬是不肯去另外一屋,聂宁想若半夜伤口发作,自己呻吟作声,她定会担心,装作生气赶了她回去。果然,半夜三四更时,内里骨头隐隐作痛,肿包碰到生硬的石块,一下就流出了脓水,全是暗红的血液。
第二天,靠着削成的藤拐,一拐一拐地移到木墩处,那六婆怜惜他长了肿包,没有多为难,依着藤拐撑了两日,第四日时,肿包越来越大,流了又长,怎么也起不来身了,早间阿铃去叫,他还不醒,进屋一瞧,浑身滚烫,发起高烧了。六婆怕出人命,知会了景祀,那景祀过来瞧了几眼,撂了一句“让他自生自灭吧”,遂没人再管。阿铃初时还出去干活,后来发觉聂宁开始哆嗦,胡言乱语起来,也不管自身性命,私自跑去照顾聂宁了。
“阿宁哥哥,你感觉怎么样了?”聂宁现无意识,烧的嘴角干裂,整只脸像一层冰般的,又冷又僵,阿铃只道他是疼得失去了温度,一个劲搂着他。
其间,聂宁微微睁开双眼,很快又合拢了去。只觉有一双手牢牢地抱紧自己,轻抚他的额角,是那般温柔体贴,他忍不住地流泪,哭道:“娘,你回来了,我等了你好久啊,你才回来,我们终于跟外公,一家团聚了……”阿铃听得仔细,虽然知道他说的是梦话,却不敢打搅。
这时,门外一人出声道:“快去看看他怎么了”声音柔美轻和。“是”一人提着药箱走了进去。阿铃便见一个貌美女子快步走进,后随的是六婆和众婢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