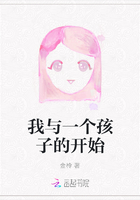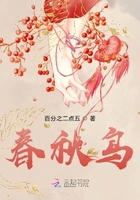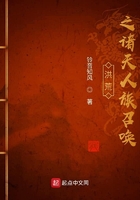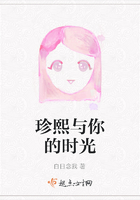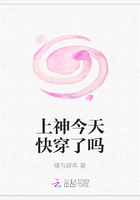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巴金从小目睹了封建大家庭内部腐败堕落、勾心斗角的生活方式,封建专制主义压迫摧残年轻一代的暴戾行径。在他父亲的衙门里,还看到过封建统治者对于平民百姓的迫害,从而触发了对于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反感。另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劳动者的善良品质和悲惨命运,激起了他“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他勇敢地宣称:“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早在那个时候,生活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撒下了作为封建制度、封建家庭的叛逆者的种子。
15岁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广泛传播的各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使巴金在惊奇和兴奋中,受到从未有过的鼓舞和启示。他密切地注视着运动的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以及一些新出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读物。原先从实际生活的感受中滋长起来的怀疑和反感,开始找到了理论上的解释和指引;本来只是个人的思考和摸索,也开始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斗争洪流中。巴金的生活和思想因此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他说:“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五四运动,推动他走上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热情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战斗道路。1923年,他从家庭出走,离开闭塞的四川来到上海、南京求学,一度还想报考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1927年初,赴法国学习,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继续如饥似渴地寻找社会解放的真理。
对巴金说来,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在“五四”前后传播的各种思潮中,最吸引他的是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政论《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鼓吹这种思潮的读物,都曾给过他很大的激动和启发,由此逐步形成巴金青年时代的人生信仰和政治观点,指引他走上生活的道路。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政论。从此开始到20年代末,他一直怀着极大的热诚,翻译编写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思潮。人们那时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几乎有同样的吸引力。到后来才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许多寻求革命真理的先进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这样曲折的路途。现代中国作家中,巴金在这方面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思想跋涉是艰苦的。这种蔑视一切权威和约束的思潮推动巴金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他坚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也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和旧世界决裂的鲜明的、激进的色彩。与此同时,这种思潮又或多或少地妨碍巴金正确理解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一个时期内持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或保留,给他的生活和创作带来某些消极的影响。不过,巴金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中国人民的实际问题,因此他能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自己的理解和行动,即使在最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也能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不仅使他当时有别于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使他经过10多年的思考探索,终于和这种思潮分道扬镳。
巴金最早的创作,是发表在1922年7月~1922年11月《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副刊)和1923年10月《妇女杂志》上的一些新诗和散文。它们传达了“被虐待者的哭声”,闪现出“插着草标儿”的“丧家的小孩”、轿夫、乞丐……的面影,指出世上绝没有主动将财富送给穷人的富豪,“要想美的世界的实现,除非自己创造”。这些带有习作性质的作品,当时和后来都很少为人提及;但是,从现实生活吸取题材,注意尖锐的社会压迫和阶级矛盾,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唤人们起来反抗,将抗争的锋芒直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革命的激情以至于晓畅热烈的文字等,都已显示出巴金以后几十年创作的基本倾向和特色。
他的正式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27年旅法期间。在初到异国的孤独单调的日子里,过去许多经历、见闻在回忆里复活过来,“为了安慰我这颗寂寞的年青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四一二”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准备迎接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推入新的苦难的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被巴金奉为“先生”的凡宰地免受死刑的抗议运动,而美国政府不顾各国舆论的警告,仍然下令将他处死。这些重大变故,都使巴金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懑。为了寄托和发泄这些激情,他又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篇章。到了1928年夏天,经过整理和增删,就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小说写的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从一开始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末尾革命者的头颅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中间穿插着封建家庭破坏青年男女的恋爱,工人因为运送革命传单被杀害等情节,表明这是一个到处都沾满了“猩红的血”的世界。小说以主要的篇幅描写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其实也就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不过,残酷的社会现实、痛苦的个人经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还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使他染上很深的厌世情绪,“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他的行动因而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盲动性质。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企图暗杀戒严司令。结果对方只受了轻伤,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家赞美他的献身精神,同时看到并且写出了这种个人恐怖行动并无多大意义。巴金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的死而哭”,并把杜大心称为“病态的革命家”。杜大心的形象,很可以表明巴金的前期创作中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他对于这种思想的突破。
1929年初,《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情节固然很有吸引力;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兄妹之间展开的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是讴歌还是诅咒,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是逐步改良还是彻底摧毁的争论,全书时而昂奋时而抑郁、骚动不安的基调,以及杜大心自我牺牲的行为等,更在迫切地寻求前途的青年读者中间,激起强烈的反响。正如一位读者所陈述的那样:《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的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号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他们不只是深切地体会了作家总的创作意图,而且准确地感受到了作家情绪上的起伏波动,沉浸在同样的痛苦和欢乐、幻灭和期待之中。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真正的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所以,虽然《灭亡》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思想上也存在着弱点,但却立即成为1929年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这个出乎意料的成功,使巴金第一次发现,文学创作可以成为自己同那些和他一起经受生活煎熬的青年们精神联系的手段。他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的续篇《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在杜大心牺牲的激发下,先后走向革命的故事。小说采用日记的形式。作品渲染了群众的麻木落后,革命者的孤独寂寞——他们只能靠着“信仰”坚持生活和斗争,因而涂抹了一层阴郁的颜色。不过,李冷在就义前想到的,却是“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体的生命上,那么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广延,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可见作家胸怀“大心”,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的命运,瞩目的是经过斗争、牺牲达到的未来。他希望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起更多的后继者,共同起来推翻罪恶的旧世界。虽然这样的信念失之空泛,在艺术上也没有得到充实的表现,却还是具有一定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