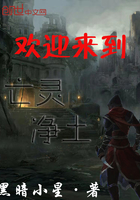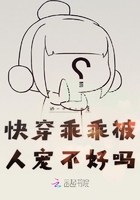17个小时的车程。我在火车上只迷糊睡着了一小会儿,但又很快被吵醒了。醒来后,嘴里又苦又臭。眼睛困得都睁不开。但腰酸背痛的却再也睡不着了。一直挨到早上7点钟。火车才到站了。我拖着行李箱下了车,走过站台旁边时再也没心情去看铁道了。跟着下车的人群走进地下通道来到火车站广场前的出口。看着火车站大楼顶层上温州两个大字。掏出兜里的纸条,上面记着父亲说的话。应该先去汽车南站,做一个发往高楼镇的客车。我出了火车站,往左拐,直走到下一个路口,右边就是汽车南站。买了票,找到那辆车上车。才感觉心里踏实一点,不一会儿车子发动着。出了站,往城外驶去。车开了将近有两个小时。全车的人几乎都睡着了。车上的广播这时也响了起来。先用普通话广播一遍,下一站是高楼。然后用本地方言,又说一遍。我移动到车厢前面的空位。心想方面的司机说。下一站高楼,有人下车。师傅,前面高楼有人下车。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演练着怎么向司机说这句话。可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索性心一横,心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提醒司机到站停车吗?但转念又一想。说不定这一站别人也要下车。在我之前提醒了司机呢,正想着后面有人叫道。师傅高楼停一下哎。司机没吭声,但肯定听见了。我松了口气儿。
车子在一个大桥下停了下来。车厢前方,一个中年女人喊道。高楼到了。我下了车,拿出行李,站在路口等父亲。对面路口一辆电动车旁有个人朝我招手。我没看清他是谁,等他走近了,我才知道是父亲。父亲剃了光头,上身赤裸着,只穿了条大裤衩。脚上拖着双拖鞋。父亲比我印象中黑了一点。也矮了一点。我想起上一次见到父亲时。还是半年前父亲过年回家的时候。父亲帮我把行李放到后座上。就招呼我上车。一路上,我想我应该和父亲说些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就只好沉默着。车子顺着山边的水泥路七拐八拐,在一个小山村的三层楼房前停下来。楼房顶层有一排红色的大字,写着滩脚村民中心。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工地是修建公路的项目。修建的公路正好从滩脚村穿过。项目部的人便把村委会租过来当做办公室。一层有一个大客厅。墙壁正中挂着电视。办完后,不少村里的老人会过来看电视。还有两间员工卧室。二楼是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三楼是个大会议厅。还有两间卧室。是会计和工程老板的卧室。项目部大楼前有不少健身器材,单杠双杠秋千之类的。旁边1栋4层楼房也被项目部租过来当作宿舍,只有一楼有卫生间。
当天晚上,父亲便领着我去项目部斜对面的食堂吃饭。食堂包给了本地一位五六十岁的夫妇。我怯生生地跟在父亲后面。上了台阶进了的那个食堂,低着头不敢看别人。偷瞄到这个房间。这里原本应该是个大客厅,被当作餐厅用了。屋里放着两个大圆桌。周围各放了一圈的塑料椅子。墙边角落里立着一个消毒柜里面放着餐具。旁边还有个小桌子上面放着一口能一次蒸治够几十个人食用的米饭的量的特大号蒸锅,食堂里已经来了不少人。没一会儿,有人陆陆续续的从外面进来。一个中年男人自言自语的喊道,开饭喽。我拿了碗筷,跟在父亲后面盛米饭。吃完饭在父亲旁边坐下。看着这两桌人,两桌菜。最多应该不超过20人。我对于这么一点人就能组建一个修公路的项目,感到不可思议。项目部的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或者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就我一个小孩突兀的坐在他们中间。有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一边夹菜一边问。张涛,这你儿子呀。父亲笑了笑说,是。一他们说到我。我瞬间身上热了起来。不敢再夹菜,只是低头往嘴里扒着米饭。那个男人继续说道,哦,放暑假了,来找你是吧。父亲说,是。紧跟着又说。不读书了。来这边跟我学开车。后面那句话一说出去。我用余光感到在坐的所有人似乎都看向了我。这么小就不读书了?那个男人几乎是叫着把这句话说出来的。嗯,不读了,父亲说道。初中有读完吗?那个男人继续问道。就是初中毕业以后过来的,父亲说。你今年多大哦,那个男人突然问我。十五,我小声说道。那个男人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大口大口的嚼着饭。好狠心哦,张涛,另一个人接着说道。这么小就不读书了,出来挣钱了。操你妈的,我上不上学关你什么事呀,瞎他妈问什么问呀。我又羞又怒,在心里暗骂着。他不愿意读了,有什么办法?进了高中,在里面瞎混,还不如学个技术呢。父亲说道。之后他们都不在说关于我的话题,和自己相熟的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之后他们都不在说关于我的话题,和自己相熟的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过了一会儿,我从桌上下来,把碗筷放进后厨的洗碗槽里。便逃开了那个房间。只所以等过一会儿再走,而不是等他们一结束关于我的话题,我就马上离开。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我是因为他们谈到我而感到害羞,所以逃走了。一走出房门,我长长的呼出口气儿,瞬间就轻松了下来。
来到这里没几天,我就在这完全混熟了。主要是因为滩脚村实在是太小了。还不到200人。山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和一些带着婴儿的妇女,整个山村的一天和另一天过得似乎没有什么两样。来到这后,我发现他们的房屋和我们县城或农村的有很大的区别。这儿的一栋房屋都有五六户人家,房子盖的像是吐司面包一样的长方形。如果单看一户人家房屋的话。就像是又窄又薄的面包片儿。还有他们不会在门前空地围起围墙当做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