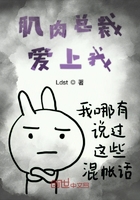部下花了好大力气才帮他把血止住。
竹兰玉昏迷时脑中混沌一片,过了许久才苏醒。他猜想自己应该是在一个寻常人家静养,简单却叫人觉得舒服。
不久,往床边走来一个水蓝色身影,梳着元宝髻。竹兰玉呼吸一紧,心就剧痛起来。他努力镇定下来,用力抬起手摸了摸夹层,玉镯仍在,他又宽心了些。
他半睁着眼,看见女人撩起床帘,对他轻轻说道:“您醒了,我给您去拿点吃的。”
竹兰玉听着这月光般的声音,越发确定眼前这个女子就是曾经那朵解语花。在月白放下床帘抽出手时,竹兰玉用尽力气扣住了她的手腕。
“这么大动作,伤口怕是要裂开了。”月白轻轻动了动手腕说道。
“我不觉得疼,它没裂开。你的建议真好,谢谢。”
竹兰玉忽然想起了什么,立马松开了手,手重重打在床上。月白的手僵了一下,轻轻抽出了帐子。
月白背对着床,说道:“竹先生要快些好起来,这样才不会让妻儿难过啊。”
“恐怕像我这样走在刀尖上的人,还是没有妻儿的好。”竹兰玉无奈一笑道。
“竹先生,能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担心一个人,也是一种幸福。您的妻儿,幸福着呢。”
“不懂。”竹兰玉冷淡了语气,“况且,我没有妻儿。”
“我知道,您好好休息吧。”月白说完,就出去了。
竹兰玉抚着夹层中的锦匣,一遍遍回忆刚才的对话,无力地笑着。伤口有些扯到了,纱布隐隐透着粉色,可他却不觉得这痛感是皮肉之痛。
此刻竹兰玉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无情自私之人,为了成全自己的私心,断了两个人的念想。竹兰玉闭了眼,思量着还是不要把玉镯给她了,怕这镯子成了锁链,叫她心甘情愿囚了自己。
此后,月白再也没有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老妇。
竹兰玉还是忍不住,询问道:“这房子的主人呢?”
“听她爹安排,嫁人去了。说来也奇怪,从来都是不肯的,昨天就答应了。”那老妇絮絮叨叨地说道。
“那个人不好吗?”竹兰玉喃喃道,突然又觉得自己这样做十分不妥当,分明是他无情,现在又来打听这些,着实可笑。
“倒也不是那个人不好,大概是姑娘有了心上人吧。”
他第一次觉得情是这样恼人的,不由己而起,不自觉而深。
竹兰玉养了好久的伤,虽然伤得比大哥二哥都重,却没落下什么病根。他一个人坐在窗边,回忆着小时候,每次父亲出征,母亲和其他太太都是提心吊胆的样子。父亲回来了,才能有片刻舒缓。他很难想象如果父亲死在了战场上,家里的女人们会怎么样,家里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又想起大哥二哥负伤时,大嫂、大太太、三姨娘天天以泪洗面……他好像有点懂得父亲了。他猜着,父亲总是对家里人冷冷的,怕是希望如果哪一天他出了事,妻妾子女们也不用为他过度悲戚。
不过竹元英想错了,怎么可能不悲戚。
不久,竹兰玉的大哥因为腿疾受了感染,去世了。大嫂抱着棺木,身体快弯成一团了,最后撞死在了棺木上,只留下了一个不知死为何物的孩子。
又一年,竹元英对竹兰玉道:“老大不小,该成家了。”
竹兰玉抽着烟,淡漠地说:“像我这样的人,注定死得很吓人。”
“随你吧,或许你会比我好些”竹元英叹气。
“或许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好或不好。”竹兰玉说这话时十分的平静。
竹元英意味深长地看了竹兰玉一眼:“随你吧,只是你大哥的儿子,就交给你了。”
竹兰玉夹着烟,轻轻吐着烟雾。目送竹元英离去的背影,微微眯起眼,他已经很老了。
夜已深,他像往常一样,一边喝酒,一边在月下竹前把玩着羊脂玉镯。
大概在这世上,谁都不似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轻云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