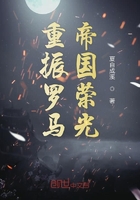李崇文接到的信纸上内容,与沈望给沈掌柜所看告示的内容一样,这告示是永汇钱庄对外放钱的声明告示。
“告示,明日起,本钱庄对外借银!借银者需为苏州府本地人士,且成家立业。借银者需备所需银两倍之质物,质物种类不限。借银者需有保人,亦为有家有业之本地人~”
这个告示被贴出来意味着永汇钱庄真的干起了对外放钱的买卖。
“大家稍安勿躁,且勿被气伤了身,我等并非毫无作为,此事还有可为!”
李崇文率先平静下来,赶紧招呼其他人停止咒骂。
一听李崇文有办法,在座众人终于停止咒骂,端起茶杯牛饮起来,干嚎过后的嗓子终于舒服些。
“儒德有何方法,快快道来!”
乌德才哑着嗓子有些急切的问道。
“那沈老二这般做法无非是以利诱银,再以银取利,一切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与我等想比,他的银本高,银利薄,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汝等以为如何?”
“儒德大才,老朽自愧不如。经此一说,却是如此之理,哈哈哈,看来我等不必自哀啊!”
田勤寿心情大好,既然事情没那么不可挽回,甚至可以说还有优势心中定然高兴。
“可如此这般,我们也要降下银息,那么银利定然不如从前了!”
乌德才唉声叹气,一脸不情愿,觉得降银息如挖取自己心头肉那般痛。
“非常时刻定要行非常之策,若是可惜自己那点银息,但最后大家都得没饭吃,糊涂!”
田勤寿一点也没给乌德才脸面,乌德才也不敢继续多说什么,苦着脸憋在一旁不说话。
田勤寿看似是训斥乌德才,实质却是借着乌德才定调子,屋子里支持乌德才论调的人不会少,现在没说不代表没想法,所以现在借着引子给扼杀在萌芽中。
李崇文趁机端起茶盏喝茶,算是支持田勤寿定的调子,他知道这时候田勤寿出头总要好过自己,而其他人见李、田二人都是这个意思,也就不好多说什么,只能支持。
……
永汇钱庄对外借银,且银息低,深得农民与小商贩欢迎,马上就要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永汇钱庄的政策如同甘霖一般,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存银者与借银者皆众。
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以李家为首的七家钱庄,在永汇钱庄宣布降息不到一天的光景,也顺势宣布降息,并且换钱火耗只取一半。
这么一来,由于七家钱庄借银方便,相比较之下反而七家钱庄生意更盛,相当多的人选择退掉永汇钱庄的借银,转而到七家钱庄借银。
七家钱庄有苦说不出,心中相当郁闷,自己降息借银,可老百姓却都在说沈老二的好话,都说是沈老二逼得七家钱庄降银息,他们心情能好才怪。
在永汇钱庄的后院,沈望的书房里沈掌柜将已经盘好的帐交给沈望,几天下来永汇钱庄存银达三十万两之巨,沈掌柜也将各种细项写清楚交给沈望。
沈望摊开账目和细项大概看了看。
“此事沈掌柜多用些心,我就不大看了,对于这银两用处待我明天回来就有了定数!”
“如此说来,二少爷根本就没想对外借银?”
对于李崇文等人的反击,说实话沈掌柜没料到这帮腐儒做得这么彻底,看来把他们逼急了。
“然也!有人想看我们斗起来,可这也颇合我的心意,有时候一个敌人总要比两个敌人好的多吧。”
沈望两手一摊,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钱庄的那招收学徒与嘉奖之策,你可看了?”
未等沈掌柜回话,七斤从外面敲门,轻声唤道:“二少爷,外面抓住两个鬼鬼祟祟的无赖子,你得要来看看。”
沈望与沈掌柜对视一眼,这事定有蹊跷,否则七斤不会前来通禀的。二人随着七斤来到前面,被抓的两个无赖子已经被五花大绑人在一边。
原来钱庄存银颇多,虽然都放在十分安全的地库中,可为了以防万一,沈望还是在家中唤来几个家丁巡逻。
没想到这巡逻还真有效果,入夜之后两个无赖子鬼鬼祟祟冲着永汇钱庄就过来,正准备泼洒桐油放火,没想到被巡逻家丁当场摁住。
两个无赖子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根本就没等家丁动手,就竹筒倒豆子将事情经过给吐露出来。
按两个无赖子所说,那乌德才对沈望办钱庄气不过,又逼得他们降银息,别无他法,只想出这下三滥的手段,放火焚烧永汇钱庄,所以就将这差事给了他们二人,还保证每人赏十两银子。本来二人想着丑时过后再来放火,可又一想早放完早利索,早点回家睡觉,所以一入夜二人就跑过来放火,未曾想到桐油还没泼就被抓住。
生怕这无赖子信口雌黄将这罪名安在那乌德才身上,沈望将两人分开,分别让他们吃些苦头,逼着他们供出幕后主使。
家丁将两人分开托下去,抡起巴掌就打起耳光,“啪啪”的响声和无赖子的嚎叫声,能传出二里地去。
沈望感觉这样不行,一轮下来两个人嘴巴不肿才怪,那还怎么说话,告诉家丁换个方式。
家丁一寻思打脸不行,那就打屁股罢,二话不说将两个无赖子摁在长条凳上,接着将裤子给扒下来,寻来竹条冲着屁股就抽,这回“啪啪”声和嚎叫声能传出去三里地,引的周围群狗乱吠。
一顿竹条抽下来,两个无赖子摊成一堆烂泥,依然指认乌德才,看这情况二人没说什么假话,对于真假沈望最后也不再关心,因为他想出个恶毒的办法,让这两个无赖子去李崇文家放火。
沈望威逼利诱,先是吓唬二人,最后还保证两人放完火之后将他们送走,两个无赖子忙不迭的答应,反正都是放火,给谁家放还不都是一样?
这一夜注定有人无眠,苏州城东一把大火丑时刚过就熊熊燃起,号称苏州银钱业排行老二的李家钱庄烧的火焰照亮半边天,人声呼号直到天亮才渐渐平息。
第二天一大早用过早餐,沈望带着七斤出门,二人徒步而行,顺着坊市街道直行,路过李家钱庄的时候整个铺子已经烧去半个,另一半也被熏的乌黑,但还伫立着,拌着黑灰的污水流淌满地,看来灭火用了不少水。
一堆看热闹的百姓对着李家钱庄废墟指指点点,有的人在惋惜,有的人在偷着乐。
惋惜的人是没早去李家钱庄借银的人,偷着乐的是已经在李家钱庄借出银钱的人,想着要是这李家钱庄关门不干了,那自己借的银就不用还了。
靠近钱庄废墟里面却是李家的家丁,在驱赶看热闹的人群,还有一些人在收拾着废墟。
沈望就是路过的无关路人,眼神随意向着废墟一瞟,看见李崇文满脸的酱紫色,不知道在跟下人呼号着什么。
二人并未停留,继续前行,转而一路北上就来到城北的郑府。
郑家在江南地区多地从事百货贸易,可以说叫的上名字的东西都能找来交易,沈家的丝布有一部分也交与郑家去贸易。
再往亲近了说,郑家老爷郑元之的母亲与沈望的母亲却是未出五服的表姐妹,沈望称郑元之的母亲为表姨母,而郑元之更是沈望的大表哥。
郑元之如今四十有余,其有一子小沈望一岁,名曰成龙,郑成龙自小与沈望玩在一起。
郑家也是苏州富户,故府邸占地颇广,明显的江南园林风格。在外看却是高墙大院,七尺高墙青瓦铺顶,灰白的墙身足有数百步。
富商宅邸所在位置多是清净之所,小巷不宽可行马车,行人寥寥,沈望二人不多久就到了门前。
高门楼,红门柱,青石狮,琉璃瓦,翘飞檐说不出的气派。正门是赤红木门,漆得又红又亮,上面茆着婴儿拳头大小的铜钉,正门一侧有个侧门,比正门小上一些。
“回转你们郑公子吧,我家老爷断不会见他的,切莫再来了!回去吧,回去吧!”在郑府门前台阶之上,一个富态的花甲老头对着面前一位身着粗布麻衣的年轻人摆着手,不耐烦的驱赶着。
这个老头就是郑府多年来的管家笪翁。
麻衣年轻人黝黑的脸庞,双眼略狭,矮鼻薄唇,面无表情。麻衣下露出的胳膊也是黝黑粗壮,面对富态老头的不耐烦,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可老头没有什么耐心,更不可能再去听了,却是转身回到门内,接着侧门“咣”的一声被关上。
站在侧门前,年轻人迟疑了些许时间,握了握拳头转身下了台阶。
年轻人与沈望主仆二人错身而过,犀利的眼神扫了沈望一下,然后就快步离开。
就在年轻人错身之时,沈望闻到一股淡淡的海腥气,皱了皱眉头,却也未多去想。
踏上郑府门前的台阶,赤红的木门上整齐的排列着铜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亮光。
沈望上前轻轻的叩击侧门的门环,两息间,门后是响起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谁呀?”
接着侧门被拉开一条缝隙,从中间露出一个戴着青色小帽的脑袋,上下大量了一下门外的沈望,接着就是“哎呀”一声,“咣当”一下小门又合拢上了。
盏茶间,赤红大门旁边的偏门“咿呀呀”的再次开启,接着刚才那个富态老头笪翁满脸堆笑的从里面迎了出来。
“二少爷您来怎么不提早打声招呼,好让小老儿备车接您去,您好久没来了老太太还时常说起您呢,赶紧里面请!”笪翁一脸谄媚,不知是上了年纪背有些驼了,还是见到沈望故意弯下来的,抬着手引着沈望向郑府里面走。
沈望年少时与郑成龙在一起玩闹,没少来郑府,那时候二人淘气更没少捉弄眼前这个笪翁,甚至现在笪翁看到沈望都有些发怵。
“笪翁,成龙何时回来,还要与他一起玩呢,嘿嘿。”
笪翁一听,脸上的肉皮就是一哆嗦,郑成龙替父回故乡泉州祭祀,想想也快回转。
“二少爷您就别吓唬小老儿了,成龙少爷近几日就能回转了!”
沈望点点头没再继续说什么。
进了门,向前走不远就是假山小塘,从桥上而过却是一道长廊,穿过长廊就是郑府平常见客的地方。
沈望先是去后堂拜见了老太太,老太太现在一心吃斋念佛,有些日子没见沈望,这次见到又好不高兴,与沈望聊了多半个时辰,有些累了,沈望这才退出来。
从老太太那里出来沈望就拐进了见客厅,这时候见客厅没人,沈望就伸起脖子高声喊道:“哥哥,弟弟来看望你了,多日不见都……”
话音未落,郑元之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向着沈望直摆手,让他不要再喊了。
郑元之拿他这个小表弟也没办法,自己的儿子跟着他胡闹,正经书读的也不怎么样,自己就那一个儿子,有时候想想只能自己独自叹息。
“年纪不小了,还如此胡闹,成龙与你一起不读圣贤书我也不说什么了,现在你竟不打招呼弄出那什么钱庄来,不知沈家姨夫如何同意,定是你又闹了!是不是昨天得大火也是你放的?”郑元之板着脸一边说教一边坐在椅子上,也不去看沈望。
一听到郑元之说这话沈望就知道自己这个大表哥有事,肯定对自己的钱庄有想法,否则怎么会关心自己的事儿?
“这话可不能乱说,现在天干物燥,梅雨迟迟不来,丁点的火星就能烧起来,与我有何干啊!”
沈望往椅子上一坐,翘起二郎腿。
“今天来是给你送点好东西的,要不要?”
“哦?好东西?你能有什么好东西?莫不又是那些奇淫巧技之物?成龙那里都摆了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