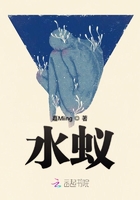俊采妈还在对俊采念叨:“你爸爸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也不等到他,多说几句话?”俊采跟宋铁杉商量好的要单独吃,就忙不迭地说:“他刚才给我交代了,今天他和干爹要很晚,来不及今天说了。这几天他都在,要我改天来,另有其他事情要我办。”
俊采妈这才止住不说,星儿眨巴着惺忪的睡眼,听说俊采要走,可怜兮兮地望着哥哥,想他留下却又开不得口,干妈微微叹口气说:“我去厨房切些卤肉,俊采你们带起吧,晚上吃。”
留不下宋、方二人,过去又没有公交车,干妈就吩咐两个身强力壮些的帮工骑车搭二人回去。
宋铁杉在茶坊内倒还淡定,回去的路上却有些局促不宁了,俊采也觉父亲似有心事却揣摩不清,二人居然一路无话。送他们到了所住楼下,两个帮工就告别原路返去回冠明餐厅了。宋铁杉见俊采还在神思,就后面轻轻踢了他一脚,问到:“想什么呢?我还有瓶尖庄,先去上楼拿了来,晚上我们好好喝喝!”
宋铁杉的住处不仅是省城近郊失地农民的住宅村,同时也是都市边的贫民窟,寄居者大都是体力劳动人,靠力气吃饭的,做为房东的农民也大多在附近建筑工地、厂子里等打工。好些打零工的都喜欢去附近厂子的垃圾堆翻腾,因为经常可以捡到不错的边角废料,打整一下就是门前的垫路、养鸡养鸭子的栅栏等。
尽管附近厂子用电供应非常有保障,这里的供电情况却比农村还不如,家家户户必须备油灯蜡烛照明;没有下水管道,污水恶臭横流;没有垃圾站,所以随处都是垃圾堆;没有公共厕所,所以憋急了的时候也不得不在野地里拉撒;府河就从这片贫民窟穿过,但只是顺水,不顺风,因为这盆地来风是从西向东吹,所以最早规划的工厂等企业都在东边,这就更加剧了这边整体环境的脏乱差。
基本没有什么规划过的街道,已有住宅都是农民们委托包工头甚至自己招募施工队修建的,七零八落错落无致,恰如《跛豪》里的九龙城寨,没来过的人基本都要在里面迷路。
晚饭时间到了,家家户户都开始生火做饭,蜂窝煤、木柴、煤油炉子甚至稻草都有,整个贫民窟立时炊烟袅袅。家家户户都还是如农村一般,全把门敞开了吃饭,超生的妇女们背一个,抱一个,肆无忌惮地当街就扯开衣衫,给怀里的孩子喂奶。男人们则一边抽着光杆子(不带过滤嘴)廉价纸烟,一边相互吆喝着喝烧酒。几杯烧酒一下肚,酒劲儿犯上了脸,如关公一般的红,就口无遮拦地开始大摆荤(黄色)龙门阵,惹得哺乳的女人笑得丰乳乱颤,这更加惹得男人们像闻到了蜜糖的蜂子,越围越多。
附近有很多小摊贩,多是简单快捷的卖麻辣烫、面食抄手、单锅小炒等。两人找定河边一家麻辣烫摊子,看来也是本地农民的房子,打通前门加上院子约有2、30平米的,院子里头左右两边都是用蛇皮编织袋搭起的凉棚,以备下雨时用,一共十来张桌子。
宋铁杉应该是这里的熟客了,直接领着俊采坐到凉棚下窗边的一桌,然后马上大声吆喝:“曲比,拿牛肉来,海椒面碟子两个。”然后转头对俊采说:“这家牛肉做得很滑嫩鲜香,真不比中午你干妈做的那道西施拂牛差!老板娘人材那是两个字——漂亮!酒量好,仗义,待会儿你跟她喝一杯?”
俊采惊异于宋铁杉变化之大,红了脸使劲摇头:“算了算了,认都认不到。”随即有些不解:“我记得,班上你从来没跟女生说过话哒?路上见到认得到的女生,总是要么梭边边要么绕开走。”
“是啊,若光太小,没走出来之前,想的事情和做的方法都不一样。在家里的时候,好像我祖祖辈辈都跟我一样就是这种本分的农村人,那个传说中豪气干云、高朋满座的大伯是个什么生活状态和理想,我根本无法想象!除了努力挣钱抚养母亲、妹儿然后讨婆娘,我就不剩下啥子目标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像我爹一样——活得那么难,死得那么龊(方言:窝囊的意思)…..”顿了一下后,宋铁杉打开那瓶尖庄,“牛肉串好没得?杯子嘢?要开干嘞!”
老板娘端出一大盘用竹签子串好的牛肉走了来了:“来咯来咯!这个小哥哥面生哦,很有型哟,你朋友么?”老板娘的川音有些生硬,但是脆生生的,皮肤白白净净,尤其是鼻子很笔挺从而显得整个脸盘非常耐看,半高个头,年纪可能也就二十出头,盘着小媳妇头,俏脸随时带着笑,亲手打开了蜂窝煤炉子,然后端上着热气腾腾的锅子,将竹签子串好的红艳艳的牛肉放进锅里。
“啊哈,就是,今天人莫得好多人啊,咋哩?”宋铁杉一边扯去酒瓶盖上的封签,一边随口问。
“祝耀山的老板要在中和场再开个厂,来招工,郑矮矮那伙人都想去,就一起打平伙(方言:AA制)请他喝酒,都去了那边。”曲比朝他们来的方向努努嘴说。
“嗯,我晓得,每月应该有400多喏,难不怪郑矮矮老婆今天那么风骚。”宋铁杉想起刚才看到的情景,打着趣说。
那女人白了宋铁杉一眼:“她风骚又不是一天两天咯。我早看出来了,你恨不得跳起去变成她怀头抱起的奶娃子咯!”然后进屋去拿出两个比通常啤酒杯略小的杯子,给他们放在桌上,就又回屋去招呼里头的两桌去了,这种口径的杯子只遂宁常用,看来附近遂宁人开的餐饮的多。
俊采一直憋着,直到老板娘完全进了屋里,才放开大笑起来。
“看不出吧,是个彝族。”宋铁杉略带几分得意地说,“这事儿除了我没人晓得了,你也知道就是咯。她是逃婚出来的,在他们那里,姑舅表兄弟姐妹必定要优先婚配,习惯上是姑母的女儿是舅舅的儿媳,婚嫁前首先要征求舅家纳聘,舅家不纳才能另嫁,而且要把所得聘礼送一份给舅舅家;反之舅家女儿也同样对姑家有上述义务。她有个自幼的青梅竹马,但那家家庭成份有问题,所以他父亲把她许给另外家,她鼓动那个小伙子一起逃了出来。但是那小子在省城不晓得咋个挣钱生活,又怕家里找回来,就丢下她跑回去了。”宋铁杉几乎一口气对俊采说完,眼角却一直扫着老板娘进去的那道门。
俊采看在眼里,暗暗想笑,但装作若无其事:“我爷爷我也从没见过,据说当年是当年走马帮跑云南西藏,但我二爷爷和父亲都不晓得那边少数民族有这些个规矩。你读书的时候可是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功的,你不会是想跟她......这个哟?”俊采把双手大拇指心向内作对比了一个婚配的手势。
宋铁杉脸色稍有红晕,带着几分严肃几分嬉戏说:“我大你两岁,我妈老是这么念叨,你爷爷在这个年纪都已经生了大伯了。只要我想通了,有啥子不可能的?赶紧生两个标致的娃儿出来,说是混血儿既聪明且漂亮,我还真想打算下那!来来,喝酒喝酒。”见老板娘掀开门帘跨步出来,宋铁杉立即岔开话题,把酒倒进啤酒杯,推给俊采一杯,两人碰了下,然后来了一大口。
灼热的酒一下顺着喉咙一直到胃里,激得俊采打了个颤儿,他赶紧拈起一片卤肉放进嘴里。宋铁杉已经抓起烫好的牛肉签子,往俊采面前的碟子里撸。
俊采也毫不客气地挑起来吃,入口果然细嫩滑润,并且味道很鲜,有股奇怪的香料味道,却不像他知道的任何一种。拈起卤肉想起干妈干爹来,俊采问:“今天你进去,干爹说了些咩事?”
宋铁杉没有回答,只是又举起了杯子要俊采喝酒,然后问到:“今天的事儿等会再说。我先问你,我们认到好久了?”
“初二那年嘛,算到今年该是6年咯。”俊采边吃边说。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是10月23号,所以确切说是5年半。那时候如果不是你上前来插话递点子,只怕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坐在这里。”宋铁杉感慨地说,“于今真的我不敢想象那时候怎么就会有那么大的胆子。来,这杯酒我先敬你,没得你和世举、省三儿,我都不晓得当时的我,是不是能摁下心头那口恶气不会去杀人!”
宋铁杉一直低着头,说到这里,他默默顿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很认真的盯着俊采:“我妈的那个病你晓得,基本下不得地,那年刘烧柴到我家,为了藏住那几尺布,她硬是下作得来要给他们跪起!联防的宋拐子跟到刘烧柴的,帮腔说我家里从我爹开始就不是老实人,就是……偷….偷电遭电打死的,结果布还是遭他们连哄带抢地拿走了,说是先寄放在那里,随时补交了粮食就当场退还。”
俊采默默端起酒杯,二人又浮了一大白,宋铁杉揩揩嘴角眼角继续说:“放学回家后我妈已经气哭到卧床了,听到我妹儿一边哭一边学他们的口舌,当时我脑门子就嗡地一下全充了血了,暴跳起来,提起菜刀要去宋拐子家。妹儿吓得抱住我的腿大声哭,我妈听到了,不顾死活地滚下床爬到院子里来拉住我,一边哭一边骂我爹,怪他死得早,怪她自己命苦,养大了的儿没人管没人教,要去杀人,早晚都是劳改犯的命,她还不如早随我爹去了,只是不晓得我妹儿要好造孽。听得这话,看到死死拉住我提刀那只手的宋铁梅,我一下就没了力气,瘫坐到地下了,那个万念俱灰啊,不晓得自己活着还有啥子意思!”
说到此处,宋铁杉已经梗咽鼻塞说不下去了。缓了会儿,他背转身揩了把鼻涕甩了,随即转过来举起杯子:“第二天,我和举娃子一起,用骨头把宋拐子家的狗引到后面的万人坑那边竹林头,然后用提前备好的活扣索索把那畜生拉上树吊死藏好咯,然后半夜去抛出来扛到宋拐子家,吊到他家门口的桑树上。”
“下来没过几天,就是10月23那天的事情了咯,”宋铁杉蓦地见曲比坐在门口竹凳上,正在清理吃过的竹签子,一双妙目有意无意地抬起来瞟向他,似在听他们说话。
“我这才算解那口气,要是当时按不下来,我,我真打算砍了宋拐子再去砍刘烧柴,真要是那样,那…..那很可能我这辈子到那天就全都完咯。”宋铁杉一口把杯中酒干了,砰地把杯子顿在桌上,旋即抓起酒瓶倒满。
“这第二杯我还是敬你,方俊采。”宋铁杉又端起杯来,狠狠地喝了一大口,接着说:“自那次祠堂的事儿之后,你就是我的生死兄弟,我就没有什么不能对你说的,也从来没想过你会看不起我、笑话我。”
俊采点点头,默默地举起酒杯,将残酒一饮而尽,没有插话打岔。
宋铁杉抓过俊采的杯子,也给他倒满,慨叹道:“你和省三一起告诉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又高兴又沮丧。我没有读书出来,不是读不进去,而是家里让我分心太多。坐在学堂里,心都是发慌的,家里好久快要断米了,晚上猪草还没有打好,柴又不够烧了…...这些我都要自己想办法啊!还不能让我妈和妹儿晓得。夏天里想到哪里掏南瓜,秋天想到哪里挖红苕、胡萝卜,全都上课时候做白日梦。认到以后,要不是你经常把米驮到学校后匀给我些(当时乡镇中学都是学生自己带米去学校换饭票),我可能就真的只有听了祝耀山的话跟了他去操。”
“我来省城后的事情很少跟你说,不是因为怕你看不起我,而是每每会想起来,我自己都羞愧难当,说不出口。没钱的时候,我住过九眼桥底下,和几个叫花子一起,幸好我随身带起学生证,亮给他们看,是他们给东西我吃。再难不过讨口,但我始终开不了口去要钱要饭,还被他们笑话;半夜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就爬起来去翻垃圾筒找吃的,开始经常吃来拉肚子,后来适应些后才好些了;有次翻垃圾桶的时候被一个撬杆头头儿看到了,拉起我旁边摊摊上给了我买了碗豆花饭吃,然后就带我去他们在三瓦窑的窝子。起先要我放风,发现没对,我就趁找机会偷偷溜走了。”宋铁杉确实有些羞愧难当了,几乎是一口气说完的,说的时候都不太敢抬眼看俊采。
俊采仍旧默然端起酒杯:“来,喝。”然后一口喝了小半杯。
宋铁杉见状,也一口灌下小半杯,喝得太急呛得急促咳嗽:“还有次,我进了临江派出所,是因为在劳动市场那里跟人谈活路谈价格,有个小子边边上立起听,很不耐烦嘴巴还嚼,说牛王庙外头那边是他们的地盘,我是瓜的,犯贱,那么低的价儿都要去干,我亮了下陀子要他闭嘴,于是就打了起来,那娃儿被我打得还不得手,一路来的个小叫花儿告诉我这娃儿是遂宁帮的,后来听说他们放下话来要废了我。干了没几天,那个玻纤瓦的小老板听说我惹了他们,也不敢用我,结了工钱要我走。”
“是祸躲不过,没好久去找活路做,又和遂宁帮的几个在劳务市场碰到了,我被七八个人提着杠杠和大拇指粗的麻索索追着打,开始还是半躲闪半说理,后来挨了几下有点重,头都遭打破出血了,晓得狗日的要下重手了,那是真的以为自己要被打死在那里,就纯粹是逃命一样飞起跑,撞人被撞,我都没得感觉了,只要看到有人空空跳过去就钻。没料到被逼到河坎坎边上,没得路可走,我就索性横下心翻过坎坎跳进河里,这才算逃过一命。可是等派出所过来拉我上岸,又遭那几个追打我的娃儿诬为撬杆,旁观的人不敢发话,我一人有口难辩,直接就被派出所拿下,学生证遭水浸了看不清楚,又没得认识人来领,就被铐在他们派出所院子里的树上,过了整整一个晚上,蚊子咬得我浑身是疙瘩,我都以为肯定要坐牢了,结果第二天下午,有人来保我出去,你猜猜是谁?”说到此处,宋铁杉方眉头稍有舒展。
“祝耀山!”俊采想了想说。
“你就是很有这些鬼聪明。”宋铁杉抚掌赞道,“就是他哥子!我当时在省城也不认得其他人了。头天他也在劳务市场找人拉砖,我跟人打架被追来跳河的那当儿,他挤在后头看热闹,后来听得我骂人的口音,踮起脚尖才看到满脸是血的我,跟着盯了好半天才确定。当天他就去派出所,但是人家要单位开介绍信来取人,他又想办法去开证明取我出来。”说到这里,两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杯,干了剩下半杯。
两人都有些微醺了,手脚都不像起先那么利索了,曲比很细心,上来给他们分别到了一杯热茶:“不要喝那么快,多喝些热茶,酒劲儿上来就缓的多咯。”然后却拿过酒瓶,一一给他们斟上一小半儿。
俊采见状,赶紧招呼曲比倒开水,自己起身上厕所。回来后看看天色渐渐晚了,就提到一直憋着想问的事情:“这是第三杯了,总该说说我干爹给你说了什么啦。”
“我没提要求。”宋铁杉直直地盯着俊采,一字一句地说到,“我进去的时候,屋内有五个人:陈二叔和大师兄,铝业公司老板和那两个便装军人。陈二叔要我坐下,我就规规矩矩地坐下。只听得陈二叔问我:‘这是我们若光的娃儿啊,你父亲是哪一个?’我仍旧规规矩矩地回答:‘陈二叔,我叫宋铁杉,宋江的宋,打铁的铁,水杉的杉,我父亲早就已经过世了,名字也不值一提。’招呼我进去的那个大师兄附耳到陈二叔跟前说了几句什么,陈二叔眉头就皱起来了。”
俊采微微动了下嘴唇,但还是忍住没有打断来问,宋铁杉仿同视而不见地继续说下去:“‘那你想做啥子?将来。’陈二叔沉吟半晌后问我。我说:‘要像陈二叔一样,受人尊重!’陈二叔愣了一下,转头向那两个军人:‘舟山啊,像你的口气那?这事儿怎么办才好?你说说看,方六子家里弟妹是明白人,她家里那边的人呐。’年长些军官说:‘身板儿不错,能吃苦,脑子也好使,只是好铁不打钉,他未必就能走你的路子。’然后很小心地看另外个军人的脸色,另外个却不动声色,只是掐灭了香烟,点点头却并不接过话来说。”
“陈二叔苦笑了下慢慢地自嘲:像陈二叔一样受人尊重,嘿嘿!陈二叔为了受人尊重,拿下多少吃力不讨好,之后还要帮别人把屁股揩干净的事情?!莫法,谁让陈二叔来坐了这位置呢。”
“我想都没想就接着答道:我拿得出力,也讨得来苦!”
“陈二叔给其他几人发了烟点燃后,转向大师兄:你看那,顺开?那大师兄一直垂拱而立,此刻方抬起头来答到:‘师傅,您亲手带出来的只有我一个,治川已经跟着方二叔咯,铭晓考了警察,那是因为您经常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所以尊重都是是靠各人去争取,没得啥子是给他端到面前的。’陈二叔点点头后就说:那前面就你来安排吧。”
“大师兄要我后天去马鞍路126号二楼去找他。整个过程,就是,就这样。”宋铁杉双手撑在桌面上,使劲儿活动膀子,双手扭在一起,骨节咔咔作响,一副很轻松的样子,“而且我想好了,去当兵!”
“当兵?!”俊采更感迷惑了。
“嗯哪,尊重不是一天失去的,也就不是一天可以捡回的。”宋铁杉拨弄着筷子,“其实我老早就是想好了的,现在能每月即便挣一千,又能怎么样?能给我妈更好的医病条件,能给我妹儿更好的读书条件,这些是很重要!但是相比宋德龄和陈二叔,我更愿意成为陈二叔那样的人:因为钱能买来荣誉证书,却买不到尊重,就像祝耀山的口头禅,有钱使得鬼推磨,得势唤来磨转鬼!宋家人受了他好的不少,但一直不以宋德龄这支为荣。为了洗刷去我父亲的窝囊名声,不管要多少年,我认了!我就要让磨子来把那些龟儿子些的态度弄转了来!”说罢宋铁杉举起酒杯,和俊采碰杯,两人同时仰头干了。
这杯酒下肚后,俊采有些不行了,赶紧端起热茶水来喝,才压下要翻涌起来的酒劲儿。曲比忙给他们端来炒饭和泡菜,两人几口就刨完,宋铁杉抢着去结帐,却半天没出来,俊采正纳闷呢,曲比出来,要他搭个手,把宋铁杉扶上床醒下酒。原来宋铁杉进去就吐了,随后倒地怎么都起不来,曲比拉不动更扛不起他,只好前面来找俊采。
俊采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宋铁杉扶起来,准备往帘外走,曲比却说:“往里头去!”却见俊采不解,她慌不择口悄悄说:“他在这里住过的。”俊采一下愣住了,手里拎的酒瓶子也掉落在地,曲比自知口误,忙碎步赶前打起帘子,却不敢再回头看他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