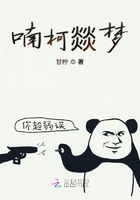才走到5楼,就听到眼镜家歌舞升平的。拐上楼一看,眼镜住处的门大敞开着,难得见到眼镜这么high,看来这小毓是挺外向的性格。
我拉了拉T恤,第一次见面可不能给人家留下太差的印象。一进门,眼镜正裸着上半身在沙发上“葛优躺”。
“人呢?”我小声地问。
“谁?”眼镜满脸问号地看着我。
“你女朋友没来?”
“没啊,谁说她要来。”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脱了T恤往沙发上一靠,真没劲,还以为多大事呢。
“那你找我干嘛?”“你眼角怎么弄得?”我俩神同步了。
“我找你,是正事,我准备跟张老板请十天假。”
“十天?你哪儿来那么多假。”
“不怕,张老板会批的。他巴不得我再多休十多天。”
“纨绔子弟就是不一样。你请那么多天干嘛?”这待遇天差地别,心里想不酸都难。
“我要去趟内蒙古。”眼镜一脸花痴笑地看着我。
“恋爱的酸臭气,情侣游?”其实不用他回答,看那春心荡漾的表情就一清二楚了,嫉妒真是使人丑陋。
“不是,我一个人。”眼镜那心虚地小眼睛瞅了我一下,又迅速移开了。
“骗鬼呢。”
“不信算了,你眼睛怎么回事?”
“张老板摔东西摔的。”
“什么?!这都可以,投诉他啊,这也太过分了。”眼镜一听,气得噌的一下坐得笔直。
“唉,说来话长,那天心情不好,合同搞错了,赔了几万块。”
“那也不行,原则问题,再怎么样也不能打人。”
“我问你个事。”
“你说。”
“小岩打胎的事情,你知道吗?”
眼镜脸刷的一下通红,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你……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
“春节前不久吧。”
“哦……”眼镜想起了什么的样子,半天没说一句话。
因为大门打开着,南北对流,穿堂风阵阵,这么热的天气也凉快不少。阳台外,天色渐渐暗沉下来,又要下雨了。风一阵比一阵大,“嘭”的一声,铁门被狠狠地关上了。
眼镜看看我,一副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的样子,多半想骂我是个王八蛋,但碍于兄弟情面狠不下心开口。
“不是说请我喝啤酒,吹空调的吗?”
“哦哦,对对,来来来,吹空调。冰箱里有好东西,我去热一下。”
说着从冰箱里端出一个饭店装酸菜鱼的大铁盆里,满盆的湖南香辣蟹,这玩意儿做好吃了真是能上天。
“我爸一开湖南饭店的朋友亲自炒的,味道一绝。”说着掀开了盖在铁盆上的保鲜膜,鲜香的味道立马溢出来,闻得人直咽口水。
这开火一热就更不得了,香气逼人,辣椒的香,蟹的鲜裹挟在一起,什么坏心情都一扫而光。
我和眼镜就着啤酒,大口大口吃着香辣蟹,这日子忽然也就赛神仙了。这世界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我一边嗦着嘴里的蟹,一边都眼镜说:“我下周也要请假,回趟四川。”
“回去看你妈?”
“也是,也不是,顺带回去找小岩。”
眼镜忽然放下了手中蟹:“找她干嘛?”
“没,就想找到她,看看也好。”我装作很淡定地说。
“别找了,何必呢,日子总得向前过。”眼镜担忧地看着我,好像我见了小岩就要死缠烂打一样。
“我就是想看看她,没别的意思。”
“那你要是没找到她呢……”眼镜唯唯诺诺的,让人有点看不明白了。
“我知道她家在哪儿,怎么可能找不到。”
“别闹了,我认真地,你都跟人家分手了,再去打扰别人父母更说不过去。”
“我知道分寸,吃蟹啊,这么好吃,这大厨手艺不得了不得了。”
眼镜叹了口气,没再劝我,大口吃起蟹来。
吃完那一整盆螃蟹,我俩胀得站着都累,又继续在沙发上葛优躺。趁着有空,我正好把回家的往返票买了。
感觉这趟回家应该能见到小岩,仅剩的1张卧铺票都给我抢到了,冥冥中上天就在指引着我回家啊。买好票,整个人心里就像卸下了一个重负一样,轻松愉悦多了。情不自禁幻想起回家之后的美好生活。
早上起来,先去大院口张嬢嬢开的抄手店里吃碗红油抄手,然后骑个自行车在老县城里转悠一圈,中午约几个高中同学,去河边吃个苍蝇馆子,下午找个串串店吃冷锅串串。
这四川人的一天,不是吃,就是在找吃的路上,要不就是在去麻将馆的路上。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真的能见到小岩,那只要她开口,我一定留下来。什么理想抱负,我统统不需要。我只想和她在一起,过几天舒服的小日子。我发誓,只要她开口。
我和眼镜胀得交相辉映地打饱嗝,你方唱罢我登场,眼镜这个恶俗之人,还边打嗝边放屁,没过多久,整个房间的空气都浑浊了。
两个人又喝了好几瓶酒,空调的冷风舒服得人飘飘然,渐渐地人就迷迷糊糊打起盹儿来了。
朦胧中,我看见有人开门进来了,我有力无气地推了推眼镜,他睡得像头猪一样,口水挂的老长,都要掉到衣领子上了。
进来的人,将鞋子脱下轻轻放在鞋架上,然后朝客厅走来。是一个头发长长的女生,空气中又是那股桃子的香气,我心满意足地深呼吸了一口,想把这气味吸进肺里,保存起来。
女生俯下身,仔细看着睡着的眼镜,用纸巾帮他擦掉嘴角的口水,然后微微笑着,亲了亲他的额头。
我得意地眯起眼镜笑了,终于看到小毓了,说不定早就见过了,好眼熟的样子。再睁开眼的时候,女生正水灵灵地望着我,这张脸不是那个便利店的水蜜桃女孩吗?她将食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一个嘘的动作,然后轻轻地吻了我一下。
我惊得抽搐了一下,手一弹,“啪”打在了眼镜脸上。眼镜猛地醒了过来,睁大眼睛,愁眉苦脸地看着我:“怎么了?”
我睡意还没完全清醒,摆了摆手,“没,没……你接着睡……接着睡。”
房间里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鞋架上除了两个臭男人的运动鞋什么女人的东西也没有。
我长吁了一口气,起身走向阳台。窗外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水塘里的水被雨滴杂得坑坑洼洼,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大家都跑回家躲雨了。
一把样子有些奇怪的大黑伞快速地移动着,隐约能看到下面是母女两个人,妈妈牵着孩子艰难地行走着。忽然,打伞的人将雨伞移过了头顶,那穿着一身黑衣服的母亲眼神幽怨地看向了站在阳台的我,那眼神像支力箭,看得人心惊肉跳。小女孩依旧疾步走着,她的双手抱着一个高高的瓶子。
伞又迅速地移回了头顶上,拐过那棵大榕树,她们消失在了转角的路口。
“生哥,生哥!”
我一回头,看见眼镜正赤裸着上半身站在我面前,“醒醒!你刚才起来了?”
“好像是。”可我现在明明半躺在沙发上,“怎么了?”
“门咋打开了?”
我扭头一看,大门大敞开着,对门的猫眼大得格外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