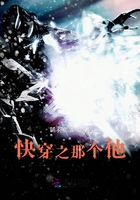上午,送别了王成模糊的背影后,终于斩断了第一节课的浑浑噩噩。
“林瀚,”陈旭手里抓着几小包松露巧克力,停顿了几秒,又往胳膊肘下舔了一本生物书,正从后门口朝这边走来,“换位置。”
姬雅拿手顺了顺右耳旁的头发,抬头看着陈旭,像在等待一抔温热。
“啊?”林瀚扭曲着五官,费力拉开身后的窗户,睡意依旧还是侵蚀进了他下巴附近的校服上衣领子里。
没等林瀚眯成缝的眼睛缓过劲儿来,陈旭已经走到我身后了。
“下节生物课,和我换一下位置,”陈旭把书和巧克力都放在林瀚桌子上,借着搓手哈气的功夫很快将姬雅装进了余光里。
林瀚刻意压低声音,向陈旭挑了两下眉,“哦,懂,”林瀚其实知道陈旭为啥要和他换位置,但还是忍不住想要逗逗他,“那,那个巧克力给我呗。”
风羞于表达自己的执着,只好强忍疼痛,一遍一遍吹打着后门。姬雅的瞳孔被冻得放大了,嘴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丢掉的那块缺角一直像个幸福的遗憾。
陈旭也毫不客气地回应林瀚的打趣,用脚尖勾了下林瀚伸到走廊里的腿,从牙槽缝里掉出几个字,“给别人的,你敢要吗。”
林瀚朝陈旭翻了个白眼,从桌兜里抽出自己早已卷了边的生物书。
“小香菇,我去门口吹会儿风,冷静冷静,你去不去?”
我正趴在交叉叠放着的胳膊上补觉,刚开始只感觉到寒气前后夹击,后来又隐隐约约听见貌似是林瀚的声音,低低的,哑哑的,于是就懒得睁开眼睛了。
“嗯?好冷,不去。”
垫在林陌脑袋下边的左肘弯突然被从窗户外头闯进来的风猛地撞了一下。
连同楼道里的风也把初晨的凄冷哼成了一首歌,迫切地挤进后门,把这段曲调分享给别人。
林瀚用缩在校服上衣袖口里的手把后门关上,才清净了一些,仿佛刚好揪住了它谄笑的证据。
“嗯?又过来了。”
林瀚拿起夹在姜鹏宇生物书里的金版《男生女生》,“是啊,没办法,我太善良了,喜欢成人之美。”
姜鹏宇无处安放的脑袋继续停泊在DNA的螺旋结构里。
“‘雾隐兽面’,哇,这个标题写的……”
“新一期的,借你看一节课。”
“瞅瞅,那小气样儿,”林瀚嘴上叫唤着嫌弃,手却诚实地翻开目录,都是一系列我看了就会选择避而不见的题目,什么《恶蛟迷踪》、《般若之面》、《对话录之复仇》之类的。
置身于物理课后的十分钟是难逃梦魇的,过期了的气氛依旧还在冻结,甚至连过分热络的冷空气都无法拯救。
“给,巧克力,”陈旭把那几包松露巧克力直接放在姬雅还未停笔的日记本上,墨蓝色的几行小诗截止在可可的香醇里,不曾下注的尾声是美的。
姬雅没有放下笔,假装随意地拿起其中一包,小心嗅了嗅,甜甜的。
陈旭把凳子往左边拉了拉,有几分热度在他俩之间一帧一帧地踌躇后戛然而止,“昨天晚上从我妹那儿偷的。”
“你这当哥哥的,怎么那么坏呢,”姬雅把滑落过耳旁的头发缠绕在食指上,来回转动,从嘴角边开始向上勾画出一道彩色来,映射出的是陈旭的笑颜。
十几岁的心绪总是无关乎谋个好结局,仿佛简单到只有大方地接受和真诚地对待。
现在讲台上站着的这位是我们的生物老师郝突然。你没听错,她就叫郝突然,是个五十岁出头的中年女性。利索的短发,可能比林陌的要稍长点儿,不戴眼镜,视力超级好。上课喜欢点名,喜欢挑人回答问题,所以林瀚他们从来不把生物课列入打篮球的行程里。这其实还算好,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对名字结构是ABB式的人格外照顾,所以,我,经常被百发百中。
我担心又被郝突然突然点名,赶紧给林陌偷偷扔了个小纸条,想让他离我近点儿,好帮我坐镇。
“林陌,坐过来。”
林陌把纸条展开在《数报》上,点在眼角的泪痣随后也向外有了位移,“怎么了?”
“呃,风,风大,你坐这边帮我挡着点儿呗。”
“哦。”
一定是天空的味道,才这样好闻。
纸条上红色的“好”字似乎已转成了语音待在我耳边良久。
林陌的一弯浅笑让我时常在郝突然的课上很放心。
“看大家这么没状态,这节课就先不说书上的内容了。”
郝突然突然扭头,转向我们,两只手上下来回交替地搓动着粉笔末。
灰白色如泣如诉,一定是在倾吐着不幸的降生。
——吼……
——耶……
“给大家讲解一下昨天的生物周练题吧。”
我猜想,郝突然应该是喜欢这样的突然的,兴许是她就喜欢做刺激的事,而且实现不了就会如坐针毡的那种。
于果把身子向后倾了大概有四十五度,得意得向我炫耀他的名字不是三个字的,更不是ABB式的,“哇,不愧是‘好突然’,顾浅浅,你说是吧。”
“是是是,真是的,”我抬起胳膊肘恶狠狠地在于果后背上杵了一下,使劲儿抛给他一个眼神儿,“本姑娘时刻准备着。”
“干啥呢,不要这么说浅浅,”于果的大红色球鞋被印上了两轮熟悉的标记。
“哼,帮理不帮亲。”
于果的凳子被他强制往回撕扯,卡在凳脚的橡胶套在地板上呻吟了几句,擦抹过的动静烙在人心上直痒痒。
“对啊,你说气不气人。”
“气人。”
“你气什么,你是猪,好不好。”
“切。”
果子挨着叶子,会自动淘洗掉大部分不和谐的外界因子,任晴空,凭风雨。
也许习惯了此消彼长,所以才总是无法直达你的心里吧。
——还没咋动呢。
——我天,不会又要挑人吧。
——呸呸呸,乌鸦嘴。
“我先挑一个同学,给大家讲讲昨天这份题中的第,第六道选择题吧,就C选项,这项是正确选项,”高二一班这个不大的空间活活被埋在一片唏嘘声中。郝突然继续道,“也是最简单的一个知识点,核糖体在mRNA上的移动。”
郝突然仔细盯着讲桌上贴着的座次表,用凤仙花染过的粉红色指甲在那张繁密的A4纸上不停摸索。
滚滚油墨香依偎着褪尽的花涩,或许注定衔不到什么好彩头。
“顾,浅,浅。”
这三个字像几块烧红发热的炭火,有些难以入耳。
哎,总是这样,怕什么,来什么,越不愿意的,就越容易发生。
我抿紧嘴唇,看了眼林陌,慌地站了起来。
“来,你来给大家讲讲,站这儿来,离话筒近,”郝突然看见我扭扭捏捏地立在那儿,还一直把无辜扮到脸上,开始招呼着让我上讲台去讲。
——妈呀,这是谁给调的节奏?我可不想上去搞笑……
我紧张得一下脱了神儿,但还是照样不误地接收了叶梓忆发出的信号,“浅浅,加油,你可以的。”
我一路拖沓着步子。
时间凝住了,尘砾迷失了轨迹。
不语的静,还是逃不了被摧毁的下场。
“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老师,我,我不会。”
不得不说,天花板上悬挂着的话筒收音效果确实不错。加速的心跳,颤抖的语调也被完整收录其中。
我的一切掩饰都成了妄为。
“不会?”
“嗯。”
“不要说不会,在我的课堂上没有这两个字。”
郝突然凶巴巴的,势如猛虎。
——可我就是不会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且,言论自由万岁!
我不敢看讲台下面,只好把视线死死聚拢在那张薄薄的周练试卷上。要是再给我加点儿热度,恐怕我就能把它烫出几个口子了。
好像教室的每个地方都在低声细语,众说纷纭。
从林陌没有丝毫波澜的表情里缓缓逃蹿出一个“傻”字来。
“一个点都说不出来?”
“嗯。”
“下去吧,”郝突然这才把交叠叉在胸前的两只胳膊会心地安放在别处,这是要迎接属于自己的show time的模样。她摩拳擦掌,清了清嗓子,语气还很清奇,“看来还有好多人不会呀,那我给大家好好说说这个知识点,虽然它比较简单,但也不能忽视,这次讲了我可不会再重复下一次了啊。”
我灰溜溜地坐回自己的位置,此刻郝突然欲拒还迎的话音和气势让我不免对她有些厌恶。
林陌把手里的红笔转了个圈,指着我生物周练卷子上的第六道选择题,“我之前不是给你讲过吗?”
“我知道那三个错误的选项为什么错,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对的为什么对呀,”我把生物周练试卷从林陌的笔下挪开,在第六道选择题的题号前画了个哭脸,“谁让她偏挑我那个正确选项的。”
林陌拍了拍留在我左肩上的一层粉笔灰,嘴角再次凹陷下去一盏光晕,“呃,好像,说的也没啥问题。”
“那你在上头站了三分钟,感觉怎么样?”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匍匐在桌子上,脸蛋正中央时鼓时瘪的一团肉抵着笔头上的樱桃小丸子橡胶玩偶。沐浴在林陌薄荷味的浅笑和声线里,仿佛当时的自己揽下了八方的暖阳。
“真傻,”就料到林陌又会这样说,入耳的嗓音是从远处寄来的一颗糖,化进风里。
郝突然突然开始扫视靠窗户的这一列。
层层浅粉色覆盖着零散的棕色,在炽烤着。
姬雅给陈旭放下一句小小的话,卡在耳后的头发排成一席浓墨,“喂,不要一直笑啦,被老师看到了。”
陈旭忙着收回一直在线的笑容,敞开的进度条不敢再向前了。
“诶,同学,你,”全班的焦点都以郝突然的声音为引火线往陈旭的方向凝聚,“对,就是你,上来。”
姬雅的轮廓最终还是无法存在于陈旭眼框里,在眼角徘徊,逗留了少许空格,然后离开。
陈旭把刚从嘴里松开的校服上衣领子捋平,端起一米八的气场,站在郝突然跟前。
“老师,我……”
“叫什么名字。”
“陈旭。”
“好,陈旭,是吧,”郝突然竟然没有一点要责怪陈旭的意思,“我可以借一下你的校服吗?”
“嗯,嗯,可以。”
那些不适的浅粉色被择取了芳华,是远去的伊始。
陈旭正准备拉开校服拉链,就被郝突然突然拽住了,他两叶粗厚的眉毛同他校服上衣的拉链一齐紧锁住了,“老师,诶……”
虽然不知道郝突然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但头一次见有老师这样讲课,所以她接下来的种种举动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
真像一部视觉小说。
“大家看,核糖体在mRNA上移动,就像陈旭同学校服上的拉头夹持着两侧链牙,借助拉襻滑行一样,能让两侧的链牙相互啮合,然……”
郝突然手里的拉头突然脱开了,陈旭无奈地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窗户边的姬雅。
“听说咱们吴董事长对学校的投资挺多的呀,”郝突然把拉头放在右手手掌中央,用大拇指摩挲着,就差来台显微镜,最后发现新大陆了,“怎么校服的质量这么差呢。”
“老师,我……”
“啊?你要发言?”
“呃,我,我经常咬领口这块儿,所以就……”
哄闹再次被打开阀门,没有预兆。
高中时代很多已经翻篇了的故事,当初有感慨的,有留恋的,后来都被忽略了。
可爱的老师,“直言不讳”的我们,从“针锋相对”到互相感动,彼此理解。
忽晴忽雨,沿途固然不止开出痛楚的花。
我们都是无名的分子,最后游走进破碎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