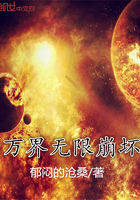同一时刻,阿特拉斯城郊的一间民房,月晦。
昏暗的灯光投在斑驳的墙上,那盏老旧的烛台被摆在木桌的中央,除此之外的家具只有一张积满灰尘的床,前几天的雨水顺着屋顶的洞流淌下来,老旧的床脚长出了霉斑。
屋子里到处都是灰尘,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烛火忽明忽灭,摇曳不定。
这是一间很久无人居住过的民房,屋子的原主人据说得了疫病死了,亲戚们分走了他的财产,只留下一间空空的破屋,据说是因为主人病死在这里的缘故而无人问津。
角落里的一扇木板被掀开,那里面是一条漆黑的甬道,通往这间屋子的地下室,很难想象在这样一间破旧的小屋里有着如此宽敞的地下室。
原主人修建它的作用已经不得而知,这里如今是另一些人的聚集地。
那是个瘦削的男人,皮肤深褐,肩上挎着一只棕色的皮箱。数十根玻璃试管就这样安静地放在箱子里的木架上,木架的旁边是一只黄铜针筒。
他推开地下室的门,如同机械般无机质的目光一瞬间汇集到了他的身上。借着微弱的烛光,无数张木然的面孔从黑暗中显现出来,有身强力壮的男人,也有穿着围裙的农妇,还有年轻的学徒工以及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的相同点在于,每一个人都如同人偶般僵立在原地,没有动作,也没有一丝表情,脸上苍白得如同传说中的僵尸,空洞的眼神直愣愣地望着前方推门而入的瘦削男人。
“神明在上,这些木偶……看着还真是瘆人啊。”
他喃喃地说着,熟练地解开皮箱的锁扣,取出针筒,将铜制的针头刺入一只“木偶”的腰椎,将抽出的脊髓液注入那些密封的试管中。
和正常人不同,这些“木偶”的脊髓液呈现淡黄色的浑浊,如同伤口上流出的脓液。被抽取脊髓液的木偶们没有一丝反应,他们的腰椎处布满了大小不一的针孔,绝大多数人的腰椎上都出现了紫黑色的肿块。
在医学尚未成熟的时代里,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提取脊髓液很容易造成感染和出血。然而这些木偶却毫无知觉,他们无疑是活着的,却又如同死去了一样,就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吃掉了他们的灵魂,只剩下一具孤零零的躯壳。
做完了这一切的瘦削男人扣上皮箱,走到一只木偶的身旁。那是个年轻的姑娘,稚嫩的脸上带着几粒俏皮的雀斑,栗色的头发从帽檐里露出来,自然地形成一个小卷。
“可惜我对尸体没有什么兴趣啊,不然我倒是可以尝试一下你的味道。”他低沉地笑笑,轻轻抚摸着少女的脸颊,就像是在抚摸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良久,他将手从少女的脸上移开。淬毒的匕首从袖中滑出,从少女的喉咙一直贯入大脑。他移了移身子,避免喷涌的血液沾到他的大衣上,然后拔出匕首,走向下一个“木偶”。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木偶做出反应,没有痛苦的叫喊,也没有任何恐惧和挣扎,那些眼神空洞的人仿佛就像真正的木偶一样,一个接一个倒在血泊中。
在所有的木偶都确认死亡之后,男人从地下室的角落里搬出了一只木桶,用匕首撬开木塞,将里面的火油倒在尸体上。黑色的火油和血液混合在一起,随后被一粒火星点燃。
那个瘦削的男人背着皮箱穿过甬道,然后走出了这间破旧的民房。屋外的风依旧呼呼地刮着,他走入前方的小巷,身后是吞吐的火舌和浓烟,死去的木偶们依旧用空洞的眼神注视着前方,在宪兵队到来之前,这里就会彻底化成灰烬。
远处的塔楼上传来七下钟声,街上的行人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不远处瘦削的男人走出巷子,原本挎在肩上的皮箱已经不见了。
所有后续处理已经完成,按照计划,他会在半个小时之后乘上通往卡美洛的最后一班列车,回到他们的“安全屋”。根据上面的消息,帝国上层的某些人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位于阿特拉斯的“苗床”就是这样暴露的。
而作为“苗床”和那些木偶的看护人,他每在这里多呆一秒,面临的危险就多一分。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周围的行人渐渐减少,原本嘈杂的声音也渐渐平息了下来,而那个瘦削男人就像是毫无觉察一般继续行进。皮靴的硬底踏在砖石地面上,急促的脚步声清晰可闻。
他忽然停住了脚步,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脑海里轰然炸响。刚才塔楼的钟声敲响七下,在阿特拉斯,晚上七点仅仅只是夜市的开始,他所处的本应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街道。可是环顾四周,整条街上空空荡荡,只剩他一个人茫然无措地停在原地。
这是……幻象!
莫名的预兆从心底里突然升起。瘦削男人猛然后退,但还是晚了一步。数十道薄如蝉翼的“刃”从四面八方突然浮现。血花从瘦削男人的身上飞溅,一部分“刃”被他避开贯入地面上坚硬的青石,斩出的缝隙足有一指深。
周围的景物如同破碎的镜面般剥落,原本的街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两个戴着白色手套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其中一个的手中连接着很清晰的魔力线,之前的幻境就是他的杰作。
血液沿着额上的伤口流过瘦削男人的脸颊,他微微侧过头,在他的身后以及两侧房屋的屋顶上,戴着白色手套的人现出身形。
帝国宫廷魔法师团,又称“白手套”。
“居然出动了五个‘白手套’的法师,你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啊。”他喃喃地说道。
撕裂般的疼痛从身体各处传来,那些轻薄的魔力之刃如同幽灵般来去无踪,瘦削男人甚至看不到它们的形状,尽管最后关头本能的反应让他没有受到致命伤,但血液的不断流失正在带走他的体力。所有逃跑的路径已经被白手套堵死,站在幻术师身边的白手套一步步向他走来,军靴踏在砖石地板上,如同催命的音符。
无数条魔力的“线”从那个白手套法师的身上向外延伸,在线条的尽头,那个浑身是血的瘦削男人抬起了头,抽出藏在后背皮鞘中的那柄斩马刀。血红色的纹路如同蚯蚓般爬满了他的全身,术式的刻印从他体内凝聚。他再次站了起来,猛然蹬地,如同在飞驰的奔马上高高跃起,挥刀下劈。
白色的“花瓣”在那一瞬绽开。
这一次他终于看清了,那是如同蝉翼般的薄刃。高度凝聚的蝉刃如同白色的莲花,在瘦削男人的身前绽开,看上去是那样的柔弱而轻盈,却轻而易举地撕碎了他身上比铁甲还要坚韧的防护。那柄跟了他一生,曾经在草原上痛饮鲜血的斩马刀,也在触及他的敌人之前无力地落下,如同被折断翅膀的鸟雀。
瘦削的男人一动不动地倒在血泊当中,手脚无力地软垂着。那名白手套的法师皱了皱眉,走上前探了探他的心跳,然后掰开他紧闭的嘴,看见了一枚破损的毒囊。
白手套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想杀死他。两次的“刃”都没有瞄准他的要害,最后的攻击仅仅是削断了他四肢的肌肉。在他抽出斩马刀的那一刻,知道无法幸免的男人就咬破了嘴里的毒囊。
“宁愿自尽也不愿被我们抓住吗?帝都居然混进了这样一群疯子。”他叹了口气:“通知奥利维拉少校,目标人物已经死亡。”
“是。”
——————————
临近莱茵河的街道的另一条小巷里,肩上挎着棕色皮箱的魁梧旅人顿了顿,然后再次加快脚步。
巴图感受到了那个瘦削男人的死亡。作为继承同种魔法的同胞,在一定距离内,他们可以互相感知对方的存在,就在几分钟前,当他将同胞拼上性命藏在巷子里的皮箱取出时,他还能感受到那个气息的跳动。
而现在,那个气息已经永久的沉默了。
他不禁有些悲哀。当他们从北方的草原来到这座南境人的城市之后,同胞们的数量就在一个个减少。尽管他们之间很少有交流,但血管里都流着同样的血脉。正是这份来自同族的血脉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异国的领土上为了同样的目标不断奋战。
他将右手搭在胸口,行了一个古老的礼节。
巴图忽然放缓了脚步,不远处披着黑色风衣的男人靠在墙边,在这个四下无人的小巷里抽着纸烟,并没有对这个路过的行人看上一眼。就在巴图和他擦身而过的瞬间,那个男人突然说道:
“嗨,朋友,你的箱子能让我看看吗?”
巴图下意识地握住了身后的刀柄,那个靠在墙角抽烟的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小刀,反射着冷光的小刀在那人的指间上下翻飞。
巴图皱了皱眉。这种类似街头抢劫的事情并不少见,黑街里到处都是持着小刀,用打量猎物的眼神盯着过往行人的混混。那种将小刀放在手里转的技巧巴图再熟悉不过,真正习惯用刀的人从来不会这样炫技,只有街头混混才会拿这种低劣的技术唬人。
一道血红色的光芒从他的指尖射向对方,巴图冷冷地说道:“下次找茬之前记得擦亮眼睛,今天我还有事,就饶你一次。”
巴图头也不回地朝巷子深处走去,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只要一露出自己的魔法,对方就会吓得跪地求饶,他没功夫和这种人多耗。
“哟,又见面了。”
他猛然抬起头,那个穿黑色风衣,靠在墙边抽烟的男人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身前。他的眼神死死地盯着那个黑风衣的男人,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可对方却依旧漫不经心地笑着,不紧不慢地朝他走来。
莫名的寒冷蔓延了他的全身。他不再犹豫,拔出身后的斩马刀,用力劈向那个男人。刀刃进入了风衣男人的身体,可却没有血液溢出,倒像是斩进了一团空气。紧接着,风衣男人的身体瞬间坍塌,如同影子般融进了周围的黑暗。
“这是……古流的影魔法,你到底是什么人!”巴图咆哮道。
没有人回答,周围是一片寂静,除了不远处水声潺潺的莱茵河。
他咬了咬牙,提着手中的长刀,猛地撞向旁边的墙壁。
————————————
“你怎么了?”陈子扬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有点头晕。”萧逝揉了揉自己的眉心。他和陈子扬正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两个人沿着莱茵河的西岸抄近道。西岸并不是主要街道,没有设立魔导路灯,视线不佳的街上没几个行人,和东岸的人声鼎沸相比起来略显凄凉。
他们并不打算回宿舍。今晚陈子扬答应了要陪萧逝练习实战,两个人沿着莱茵河的下游朝西校区的大竞技场走去。陈子扬皱了皱眉:
“不舒服的话,今天晚上就先回去吧,时间还长,以后有的是机会练习。”
萧逝只是摇了摇头:“不要紧,一点点头晕而已。”
耳畔嗡嗡的鸣声开始有了消退的迹象。不论是耳鸣还是头晕,都从十多分钟前突然出现。或许是某种错觉,萧逝总觉得那股一直徘徊在耳畔的鸣声是某种生物的鸣叫,仿佛无数在火焰中炙烤的小虫朝他们的母亲发出痛苦的悲鸣。
他不知道的是,在某间民宅的地下室里,数十具“木偶”正静静地看着自己被火焰吞噬,无数白色的虫从他们的身体里钻出,然后被热浪在很短的时间里烧成一团看不出形状的焦糊。
耳鸣声在不久之后彻底消失,头晕也忽然间消失不见。但萧逝并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某种如同雷鸣般的声音从他身侧的街巷里突然炸响。
“什么声音?”陈子扬被吓了一跳。
“不知道。”萧逝同样一脸茫然。
然而下一秒那份茫然就变成了惊悚,一只布满血红色纹路的手从萧逝身旁的墙壁里探了出来,紧接着是整个身体,那堵外墙轰然倒塌,露出了房屋内惊恐地缩在角落的女主人。
萧逝被震得跌坐在地上,他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能够用肉身撞塌一堵墙壁的人。过度的震惊以至于他忘记了思考,只能直愣愣地看着那个魁梧的身影撞破墙壁,朝不远处的莱茵河飞奔而去。
“跑了这么久,你也该停下了吧。”
身穿风衣的男人从倒塌的墙壁旁缓缓走出,手中仍然握着那柄普通的小刀。
下一瞬间,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萧逝看见,在那一刻,那个如同巨象般发怒狂奔的魁梧身影停在了原地。
穿着风衣的男人仿佛和周围的影子化为一体,如同烟云般飘忽不定的影子拂过那个魁梧的身影。手中不过一尺长的刀刃也仿佛成为了影子,萧逝甚至看不到那个握刀的人,只有血花从那个魁梧身影上飞溅。
萧逝从未见过这样的刀术,动若奔雷,却静谧得如同春风拂过水面,快到萧逝的视力根本无法捕捉,仅仅在一个呼吸的时间,一切就已经结束。那个魁梧的身影倒在血泊中,生死不知,穿着风衣的男人负手立在他身前,手中的小刀没有沾染一丝血迹。
“十二影杀……你是……白手套的守墓人!”那个魁梧的男人用最后的力气惊恐地嘶吼:“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被称为守墓人的男子只是笑笑:“你是北辽的‘血武士’吧,没想到经历了十五年前的那场北伐之后,血魔法的传承居然还没有断绝。”
白手套的法师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奥利维拉径直走到守墓人的身边,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北辽武士问道:“不留下来审问吗?”
“不需要,血武士是不会开口的,你审了也是白搭。”守墓人回过头瞥了一眼差点卷入这场战斗中的两个少年。陈子扬将萧逝拉起来,后者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那是学院的制服吗?”守墓人问道。
“是,要审问一下他们吗?”
“不用了,两个恰好路过的学生而已,让他们离开吧。”他挥了挥手。这里的动静引起了不少行人的注意,宪兵们也陆陆续续赶来,在人群聚集起来之前守墓人就离开了这里,留下奥利维拉和一群白手套法师善后。
停在路边的黑色马车里,那只由两个血武士护送的皮箱静静地放在座椅上。守墓人从中拿出一支试管,里面是淡黄色的脊髓液。
他幽幽地叹了口气,剧烈的火焰从箱子内部冒出,将里面的东西焚烧殆尽。
“稍微敲打一下,那些家伙应该也会收敛一点了吧。”